 一、小动物们
一、小动物们
鸟兽们自由地生活着,未必比被人豢养着更快乐。据调查鸟类生活的专门家说,鸟啼绝不是为使人爱听,更不是以歌唱自娱,而是占据猎取食物的地盘的示威;鸟类的生活是非常地艰苦。兽类的互相蚕食是更显然的。这样,看见笼中的鸟,或柙中的虎,而替它们伤心,实在可以不必。可是,也似乎不必替它们高兴;被人养着,也未尽舒服。生命仿佛是老在魔鬼与荒海的夹缝儿,怎样也不好。
我很爱小动物们。我的“爱”只是我自己觉得如此;到底对被爱的有什么好处,不敢说。它们是这样受我的恩养好呢,还是自由地活着好呢?也不敢说。把养小动物们看成一种事实,我才敢说些关于它们的话。下面的述说,那么,只是为述说而述说。
先说鸽子。我的幼时,家中很贫。说出“贫”来,为是声明我并养不起鸽子;鸽子是种费钱的活玩意儿。可是,我的两位姐丈都喜欢玩鸽子,所以我知道其中的一点儿故典。我没事儿就到两家去看鸽,也不短随着姐丈们到鸽市去玩;他们都比我大着二十多岁。我的经验既是这样来的,而且是幼时的事,恐怕说得不能很完全了;有好多鸽子名已想不起来了。
鸽的名样很多。以颜色说,大概应以灰、白、黑、紫为基本色儿。可是全灰全白全黑全紫的并不值钱。全灰的是楼鸽,院中撒些米就会来一群;物是以缺者为贵,楼鸽太普罗。有一种比楼鸽小,灰色也浅一些的,才是真正的“灰”;但也并不很贵重。全白的,大概就叫“白”吧,我记不清了。全黑的叫黑儿,全紫的叫紫箭,也叫猪血。
猪血们因为羽色单调,所以不值钱,这就容易想到值钱的必是杂色的。杂色的种类多极了,就我所知道的——并且为清楚起见——可以分作下列的四大类:点子、乌、环、玉翅。点子是白身腔,只在头上有手指肚大的一块黑,或紫;尾是随着头上那个点儿,黑或紫。这叫作黑点子和紫点子。乌与点子相近,不过是头上的黑或紫延长到肩与胸部。这叫黑乌或紫乌。这种又有黑翅的或紫翅的,名铁翅乌或铜翅乌——这比单是乌又贵重一些。还有一种,只有黑头或紫头,而尾是白的,叫作黑乌头或紫乌头;比乌的价钱要贱一些。刚才说过了,乌的头部的黑或紫毛是后齐肩,前及胸的。假若黑或紫毛只是由头顶到肩部,而前面仍是白的,这便叫作老虎帽,因为很像廿年前通行的风帽;这种确是非常地好看,因而价值也就很高。在民国初年,兴了一阵子蓝乌和蓝乌头,头尾如乌,而是灰蓝色儿的。这种并不好看,出了一阵子风头也就拉倒了。
环,简单得很:全白而项上有一黑圈者叫墨环;反之,全黑而项上有白圈者是玉环。此外有紫环,全白而项上有一紫环。“环”这种鸽似乎永远不大高贵。大概可以这么说,白尾的鸽是不易与黑尾或紫尾的相抗,因为白尾的飞起来不大美。
玉翅是白翅边的。全灰而有两白翅是灰玉翅;还有黑玉翅、紫玉翅。所谓白翅,有个讲究:翅上的白翎是左七右八。能够这样,飞起来才正好,白边儿不过宽,也不过窄。能生成就这样的,自然很少,所以鸽贩常常作假,硬插上一两根,或拔去些,是常有的事。这类中又有变种:玉翅而有白尾的,比如一只黑鸽而有左七右八的白翅翎,同时又是白尾,便叫作三块玉。灰的、紫的,也能这样。要是连头也是白的呢便叫作四块玉了。四块玉是较比有些价值的。
在这四大类之外,还有许多杂色的鸽。如鹤袖,如麻背,都有些价值,可不怎么十分名贵。在北平,差不多是以上述的四大类为主。新种随时有,也能时兴一阵,可都不如这四类重要与长远。
就这四大类说,紫的老比别的颜色高贵。紫色儿不容易长到好处,太深了就遭猪血之诮,太浅了又黄不唧的寒酸。况且还容易长“花了”呢,特别是在尾巴上,翎的末端往往露出白来,像一块癣似的,把个尾巴就毁了。
紫以下便是黑,其次为灰。可是灰色如只是一点,如灰头、灰环,便又可贵了。
这些鸽中,以点子和乌为“古典的”。它们的价值似乎永远不变,虽然普通,可是老是鸽群之主。这么说吧,飞起四十只鸽,其中有过半的点子和乌,而杂以别种,便好看。反之,则不好看。要是这四十只都是点子,或都是乌,或点子与乌,便能有顶好的阵容。你几乎不能飞四十只环或玉翅。想想看吧:点子是全身雪白,而有个黑或紫的尾,飞起来像一群玲珑的白鸥;及至一翻身呢,那黑或紫的尾给这轻洁的白衣一个色彩深厚的裙儿,既轻妙而又厚重。假若是太阳在西边,而东方有些黑云,那就太美了:白翅在黑云下自然分外地白了;一斜身儿呢,黑尾或紫尾——最好是紫尾——迎着阳光闪起一些金光来!点子如是,乌也如是。白尾巴的,无论长得多么体面,飞起来没这种美妙,要不怎么不大值钱呢。铁翅乌或铜翅乌飞起来特别地好看,像一朵花,当中一块白,前后左右都镶着黑或紫,它使人觉得安闲舒适。可是铜翅乌几乎永远不飞,飞不起,贱的也得几十块钱一对儿吧。玩鸽子是满天飞洋钱的事儿,洋钱飞起却是不如在手里牢靠的。
可是,鸽子的讲究儿不专在飞,正如女子出头露脸不专仗着能跑五十米。它得长得俊。先说头吧,平头或峰头(峰读如凤;也许就是凤,而不是峰),便决定了身价的高低。所谓峰头或凤头的,是在头上有一撮立着的毛;平头是光葫芦。自然凤头的是更美,也更贵。峰——或凤——不许有杂毛,黑便全黑,紫便全紫,搀着白的便不够派儿。它得大,而且要像个荷包似的向里包着。鸽贩常把峰的杂毛剔去,而且把不像荷包的收拾得像荷包。这样收拾好的峰,就怕鸽子洗澡,因为那好看的头饰是用胶粘的。
头最怕鸡头,没有脑勺儿,愣头磕脑的不好看。头须像算盘子儿,圆乎乎的,丰满。这样的头,再加上个好峰,便是标准美了。
眼,得先说眼皮。红眼皮的如害着眼病,当然不美。所以要强的鸽子得长白眼皮。宽宽的白眼皮,使眼睛显着大而有神。眼珠也有讲究,豆眼、隔棱眼,都是要不得的。可惜我离开鸽子们已念多年,形容不上来豆眼等是什么样子了;有机会到北平去住几天,我还能把它们想起来,到鸽市去两趟就行了。
嘴也很要紧。无论长得多么体面的鸽,来个长嘴,就算完了事。要不怎么,有的鸽虽然很缺少,而总不能名贵呢;因为这种根本没有短嘴的。鸽得有短嘴!厚厚实实的,小墩子嘴,才好看。
头部以外,就得论羽毛如何了。羽毛的深浅,色的支配,都有一定的。老虎帽的帽长到何处,虎头的黑或紫毛应到胸部的何处,都不能随便。出一个好鸽与出一个美人都是历史的光荣。
身的大小,随鸽而异。羽色单调一些的,像紫箭等,自然是越大越蠢,所以以短小玲珑为贵。像点子与乌什么的,个子大一点也不碍事。不过,嘴儿短,长得娇秀,自然不会发展得很粗大了,所以美丽的鸽往往是小个儿。
大个子的,长嘴儿的,可也有用处。大个子的身强力壮翅子硬,能飞,能尾上戴鸽铃,所以它们是空中的主力军。别的鸽子好看,可供地上玩赏;这些老粗儿们是飞起来才见本事,故而也还被人爱。长翅儿也有用,孵小鸽子是它们的事:它们的嘴长,“喷”得好——小鸽不会自己吃东西,得由老鸽嘴对嘴地“喷”。再说呢,喷的时候,老的胸部羽毛便糙了;谁也不肯这么牺牲好鸽。好鸽下的蛋,总被人拿来交与丑鸽去孵,丑鸽本来不值钱,身上糙旧一点也没关系。要做鸽就得美呀,不然便很苦了。
有的丑鸽,仿佛知道自己的相貌不扬,便长点特别的本事以与美鸽竞争。有力气戴大鸽铃便是一例。可是有力气还不怎样新奇,所以有的能在空中翻跟头。会翻跟头的鸽在与朋友们一块飞起的时候,能飞着飞着便离群而翻几个跟头,然后再飞上去加入鸽群,然后又独自翻下来。这很好看,假若它是白色的,就好像由蓝空中落下一团雪来似的。这种鸽的身体很小,面貌可不见得美。它有个标志,即在项上有一小撮毛儿,倒长着。这一撮倒毛儿好像老在那儿说:“你瞧,我会翻跟头!”这种鸽还有个特点,脚上有毛儿,像诸葛亮的羽扇似的。一走,便扑喳扑喳的,很有神气。不会翻跟头的可也有时候长着毛脚。这类鸽多半是全灰全白或全黑的。羽毛不佳,可是有本事呢。
为养毛脚鸽,须盖灰顶的房,不要瓦。因为瓦的棱儿往往伤了毛脚而流出血来。
 二、小动物们(鸽)续
二、小动物们(鸽)续
养鸽正如养鱼养鸟,要受许多的辛苦。“不苦不乐”,算是说对了。不过,养鱼养鸟较比养鸽还和平一些;养鸽是斗气的事儿。是,养鸟也有时候怄气,可鸟儿究竟是在笼子里,跟别的鸟没有直接地接触。鸽子是满天飞的。张家的也飞,李家的也飞,飞到一处而裹乱了是必不可免的。这就得打架。因此,玩别的小玩意用不着法律,养鸽便得有。这些法律虽不是国家颁布的,可是在玩鸽的人们中间得遵守着。比如说吧,我开始养鸽子,我就得和四邻的“鸽家”们开谈判。交情好的呢,可以规定:彼此谁也不要谁的鸽;假若我的鸽被友家裹了去,他还给我送回来;我对他也这样。这就免去许多战争。假若两家说不来呢,那就对不起了,谁得着是谁的,战争可就无可避免了。有这样的敌人,养鸽等于斗气。你不飞,我也不飞;你的飞起来,我的也马上飞起去,跟你“撞”!“撞”很过瘾,两个鸽阵混成一团,合而复分,分而复合;一会儿我“拉过”你的来,一会儿你又“拉过”我的去,如看拔河一样起劲。谁要是能“得过”一只来,落在自己的房上,便设法用粮食引诱下来,算作自己的战胜品。可是,俘虏是在房上,时时可以飞去;我可就下了毒手,用弩打下来,假若俘虏不受引诱而要逃走。打可得有个分寸,手法要好,讲究恰好打在——用泥弹——鸽的肩头上。肩头受伤,没有性命的危险,可是失了飞翔的能力。于是滚下房来,我用网接住;将养几天,便能好过来。手法笨的,弹中胸部,便一命呜呼;或是弹子虚发,把鸽惊走,是谓泄气。
“撞”实过瘾,可也别扭,我没法训练新鸽与小鸽了。新鸽与小鸽必须有相当的训练才认识自己的家,与见阵不迷头。那么,我每放起鸽去,敌人也必调动人马,那我简直没有训练新军的机会;大胆放出生手,准保叫人家给拉了去。于是,我得早早地起,敛旗息鼓地,一声不出地去操练新军。敌人也会早起呀,这才真叫怄气!得设法说和了,要不然简直得出人命了。
哼,说和却不容易。比如我只有三十只能征惯战的鸽,而敌人有八十只,他才不和我开和平会议呢。没办法,干脆搬家吧。对这样的敌人,万幸我得过他一只来,我必定拿到鸽市去卖;不为钱,为是羞辱他。他也准知道我必到鸽市去,而托鸽贩或旁人把那只买回去,他自己没脸来和我过话。
即使没这种战争,养鸽也非养气之道;鸽时时使你心跳。这么说吧,我有点事要出门,刚走到巷口,见天上有只鸽,飞得两翅已疲,或是惊惶不定,显系飞迷了头;我不能漏这个空,马上飞跑回家,放起我的鸽来裹住这只宝贝。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其实得到手中,也许是只最老丑的糟货,可是多少是个幸头,不能轻易放过。养鸽的人是“满天飞洋钱,两脚踩狗屎”,因为老仰首走路也。
训练幼鸽也是很难放心的事,特别是经自己的手孵出来的。头几次飞,简直没把握,有时候眼看着你自己家中孵出的幼鸽,飞到别家去,其伤心不亚于丢失了儿女。
最难堪的是闹“鸦虎子”。“鸦虎子”是一种小鹰,秋冬之际来驻北平,专欺侮鸽子。在这个时节,养鸽的把鸽铃都撤下来,以免鸦虎闻声而来,在放鸽以前,要登高一望,看空中有无此物。及至鸽已飞起,而神气不对,忽高忽低,不正经着飞,便应马上“垫”起一只,使大家落下,以免危险;大概远处有了那个东西。不幸而鸦虎已到,那只有跺脚,而无办法。鸦虎子捉鸽的方法是把鸽群“托”到顶高,高得几乎像燕子那么小了,它才绕上去,单捉一只。它不忙,在鸽群下打旋,鸽们只好往高处飞了。越飞越高,越飞越乏;然后鸦虎猛地往高处一钻,鸽已失魂,紧跟着它往下一“砸”,群鸽屁滚尿流,一直地往下掉。可是鸦虎比它们快。于是空中落下一些羽毛,它捉住一只,找清静地方去享受。其余的幸得逃命,不择地而落,不定都落到哪里去呢!幸而有几只碰运气落在家中的房上,亦只顾喘息,如呆如痴,非常地可怜。这个,从始至终,养鸽的是目不敢瞬地看着;只是看着,一点办法没有!鸦虎已走,养鸽的还得等着,等着失落的鸽们回来。一会儿飞回来一只,又待一会儿又回来一只。可是等来等去,未必都能回来,因惊破了胆的鸽是很容易被别家得去的。检点残军,自叹晦气,堂堂七尺之躯会干不过个小小的鸦虎子!
普通的飞法是每天飞三次,每飞一次叫作“一翅儿”。三次的支配大概是每日的早晚中三时,这随天气的冷暖而变动。夏日太热,早晚为宜,午间即不放鸽;冬日自然以午间为宜,因为暖和些。夏天的鸽阵最好看,高处较凉一些,鸽喜高飞;而且没有鸦虎什么的,鸽飞得也稳;鸦虎大概是到别处去避暑了。每要飞一翅儿,是以长竿——竿头拴些碎布或鸡毛——一挥,鸽即飞起。飞起的都是熟鸽,不怕与别家的“撞”,其中最强者,尾系鸽铃,为全军奏乐。飞起来,先擦着房,而后渐次高升,以家中为中心来回地旋转。鸽不在多少,飞起来讲究尾彩配合得好,“盘儿”——即鸽阵——要密,彼此的距离短而旋转得一致。这样有盘儿有精神,悦目。盘儿大而松懈,东一个西一个地乱飞,则招人讥诮。当盘儿飞到相当的时间,则当把生鸽或幼鸽掷于房上,盘儿见此,则往下飞。如欲训练生鸽或幼鸽,即当盘儿下落之际续入,随盘儿飞转几圈,就一齐落于房上,以免丢失。以一鸽或二鸽掷于房上,招盘儿下来,叫作“垫”。
老鸽不限于随盘儿飞,有时被主人携到十数里之外去放,仍能飞回来,有时候卖出去,过一两月还能找到了老家。
养鸽的人家,房脊上摆琉璃瓦两三块,一黄二绿,或二绿一黄,以作标志。鸽们记得这个颜色与摆法,即不往生地方落。
新鸽买来,用线拢住翅儿,以防飞走。过几天,把翅儿松开些,使能打扑噜而不能高飞,掷之房上,使它认识环境。再过几天,看鸽性是强烈还是温柔而决定松绑的早晚。老鸽绑的日久,幼鸽绑的期短。松绑以后,就可以试着训练了。
鸽食很简单,通常都用高粱。到换毛的时候或极冷的时候才加些料豆儿。每天喂鸽最好有一定的次数。
住处也不须怎么讲究,普通的是用苇扎成个栅子,栅里再砌起窝来,每一窝放一草筐,够一对鸽住的。最要紧的是干燥和安全。窝门不结实,或砌得不好,黄鼠狼就会半夜来偷鸽吃。窝干燥清洁,鸽不易得病;如得起病来,传染得很快,那可了不得。
该说鸽市。
对于鸽的食水,我没详说,因为在重要的点上大家虽差不多,可是每人都有自己的手法,不能完全相同;既是玩嘛,个人总设法证明自己的方法最好。谈到鸽市,规矩可就是普通的了,示奇立异是行不通的。
在我幼时,天天有鸽市,我记得好像是这样:逢一五是在护国寺的后身,二六是在北新桥,三是土地庙,四是花市,七八是西城车儿胡同,九十是泽福寺外。每逢一五,是否在护国寺后身,我不敢说准了;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
鸽贩是每天必上市的。他们大约可分三种:第一种是阔手,只简单地拿着一个鸽笼,专买卖中上等的鸽子。第二种,挑着好几个笼,好歹不论,有利就买就卖。第三种是专买破鸽,雏鸽与鸽蛋——送到饭庄当菜用。我最不喜欢这第三种,鸽子一到他们手里就算无望了。顶可怜是雏鸽,羽毛还没长全,可是已能叫人看出是不成材料的货,便入了死笼。雏鸽哆嗦着,被别的鸽压在笼底上,极细弱地叫着!再过几点钟便成了盘中的菜了。
此外,还有一种暗中做买卖而不叫别人知道的,这好像是票友使黑杵,虽已拿钱而不明言。这种人可不甚多。
养鸽的人到市上去,若是卖鸽,便也是提笼。若是去买鸽,既不知准能买到与否,自然不必拿着笼去。只去卖一二只鸽,或是买到一二只,既未提笼,就用手绢捆着鸽。
买鸽的时候,不见得准买一对。家中有只雄的,没有伴儿,便去买只雌的;或者相反。因此,卖鸽的总说“公儿欢,母儿消”。所谓“欢”者,就是公鸽正想择配,见着雌的便咕咕地叫着追求。所谓“消”者,是雌鸽正想出嫁,有公鸽向它求爱,它就点头接受。买到欢公或消母,拿到家中即能马上结婚,不必费事。欢与消可以——若是有笼——当面试验。可是,市上的鸽未必雄的都欢,雌的都消。况且有时两雄或两雌放在一处而充作一对儿卖,这可就得看买主的眼睛了。你本想去买一只欢公,而市上没有;可是有一只,虽不欢,但是合你的意。那么,也就得买这一只;现在不欢,过几天也许就欢起来。你怎么知道那是个公的呢?为买公鸽而去,却买了只母的回来,岂不窝囊得慌!市上是不甚讲道德的,没眼睛的就要受骗。
看鸽是这样的:把鸽拿在左手中,拢着鸽的翅与腿,用右手去托一托鸽的胸。鸽在此时,如瞪眼,即是公;眨眼的,即是母。头大的是公,头小的是母。除辨别公母,鸽在手中也能觉出挺拔与否。真正的行家,拿起鸽来,还能看出鸽的血统正不正来,有的鸽,外表很好,而来路不正,将来下蛋孵窝,未必还能出好鸽。这个,我可不大深知;我没有多少经验。
看完了头部,要用手捋一捋鸽翅,看翅活动与否,有力没有与是否有伤——有的鸽是被弩弹打过而翅子僵硬不灵的。对于峰,尾,都要吹一吹,细看看;恐怕是假做的。都看好了,才讲价钱。半日之中,鸽受罪不少,所以真正好鸽,如鸽市上去卖,便放在笼内,只准看,不准动手。这显着硬气,可是鸽子的身份得真高;假如弄只破鸽而这么办,必会被人当笑话说。还有呢,好鸽保养得好,身上有一层白霜,像葡萄霜儿那样好看,经手一摸,便把霜儿蹭了去;所以不许动手。可是好鸽上市,即使不许人动,在笼中究竟要受损失,尾巴是最易磨坏的。所以要出手好鸽,往往把买主请到家中来看,根本不到市上去。因此,市上实在见不着什么值钱的鸽子。
关于鸽,我想起这么些儿来,离详尽还远得很呢,就是这一点,恐怕还有说错了的地方;二十多年前的事是不易老记得很清楚的。
现在,粮食贵,有闲的人也少了,恐怕就还有养鸽的也不似先前那样讲究了,可是,这也没什么可惜。我只是为述说而述说,倒不提倡什么国鸟、国鸽的。
 三、养花
三、养花
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工夫去研究和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子里,一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只好上房去玩,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
花虽然多,但没有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要死是件难过的事。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
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喜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喜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个乐趣,摸住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啊!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啊!多得些知识,一定不是坏事。
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它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了,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
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赶到昙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味道——昙花总在夜里开放。花分根了,一棵分为几棵,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友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欢喜。
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今年夏天就有这么一回。三百株菊秧还在地上(没到移入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菊秧被砸死者约三十多种,一百多棵。全家几天都没有笑容。
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既须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四、小麻雀
四、小麻雀
雨后,院里来了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里跳,有时飞一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它这么飞了两三次,我看出来: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地长,似乎要脱落下来。我试着往前凑,它跳一跳,可是又停住,看着我,小黑豆眼带出点要亲近我又不完全信任的神气。我想到了:这是个熟鸟,也许是自幼便养在笼中的。所以它不十分怕人。可是它的左翅也许是被养着它的或别个孩子给扯坏,所以它爱人,又不完全信任。想到这个,我忽然地很难过。一个飞禽失去翅膀是多么可怜。这个小鸟离了人恐怕不会活,可是人又那么狠心,伤了它的翎羽。它被人毁坏了,而还想依靠人,多么可怜!它的眼带出进退为难的神情,虽然只是那么个小而不美的小鸟,它的举动与表情可露出极大的委屈与为难。它是要保全它那点生命,而不晓得如何是好。对它自己与人都没有信心,而又愿找到些倚靠。它跳一跳,停一停,看着我,又不敢过来。我想拿几个饭粒诱它前来,又不敢离开,我怕小猫来扑它。可是小猫并没在院里,我很快地跑进厨房,抓来了几个饭粒。及至我回来,小鸟已不见了。我向外院跑去,小猫在影壁前的花盆旁蹲着呢。我忙去驱逐它,它只一扑,把小鸟擒住!被人养惯的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与爪在猫嘴旁耷拉着,和死去差不多。
瞧着小鸟,猫一头跑进厨房,又一头跑到西屋。我不敢紧迫,怕它更咬紧了可又不能不追。虽然看不见小鸟的头部,我还没忘了那个眼神。那个预知生命危险的眼神。那个眼神与我的好心中间隔着一只小白猫。来回跑了几次,我不追了。追上也没用了,我想,小鸟至少已半死了。猫又进了厨房,我愣了一会儿,赶紧地又追了去;那两个黑豆眼仿佛在我心内睁着呢。
进了厨房,猫在一条铁筒——冬天升火通烟用的,春天拆下来便放在厨房的墙角——旁蹲着呢。小鸟已不见了。铁筒的下端未完全扣在地上,开着一个不小的缝儿,小猫用脚往里探。我的希望回来了,小鸟没死。小猫本来才四个来月大,还没捉住过老鼠,或者还不会杀生,只是叼着小鸟玩一玩。正在这么想,小鸟,忽然出来了,猫倒像吓了一跳,往后躲了躲。小鸟的样子,我一眼便看清了,登时使我要闭上了眼。小鸟几乎是蹲着,胸离地很近,像人害肚痛蹲在地上那样。它身上并没血。身子可似乎是蜷在一块,非常地短。头低着,小嘴指着地。那两个黑眼珠!非常地黑,非常地大,不看什么,就那么顶黑顶大地愣着。它只有那么一点活气,都在眼里,像是等着猫再扑它,它没力量反抗或逃避;又像是等着猫赦免了它,或是来个救星。生与死都在这俩眼里,而并不是清醒的。它是糊涂了,昏迷了;不然为什么由铁筒中出来呢?可是,虽然昏迷,到底有那么一点说不清的,生命根源的,希望。这个希望使它注视着地上,等着,等着生或死。它怕得非常地忠诚,完全把自己交给了一线的希望,一点也不动。像把生命要从两眼中流出,它不叫也不动。
小猫没再扑它,只试着用小脚碰它。它随着击碰倾侧,头不动,眼不动,还呆呆地注视着地上。但求它能活着,它就决不反抗。可是并非全无勇气,它是在猫的面前不动!我轻轻地过去,把猫抓住。将猫放在门外,小鸟还没动。我双手把它捧起来。它确是没受了多大的伤,虽然胸上落了点毛。它看了我一眼!
我没主意:把它放了吧,它准是死;养着它吧,家中没有笼子。我捧着它好像世上一切生命都在我的掌中似的,我不知怎样好。小鸟不动,蜷着身,两眼还那么黑,等着!愣了好久,我把它捧到卧室里,放在桌子上,看着它,它又愣了半天,忽然头向左右歪了歪,用它的黑眼睁了一下;又不动了,可是身子长出来一些,还低头看着,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五、猫
五、猫
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赶到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走出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呀,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及至它听到点老鼠的响动啊,它又多么尽职,闭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拉倒!
它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儿伸出来要求给抓痒,或是在你写稿子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地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力避单调。在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它的高兴。它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它一声也不出,连半个小梅花也不肯印在稿纸上!它倔强得很!
是,猫的确是倔强。看吧,大马戏团里什么狮子、老虎、大象、狗熊,甚至于笨驴,都能表演一些玩意儿,可是谁见过耍猫呢?(昨天才听说:苏联的某马戏团里确有耍猫的,我当然还没亲眼见过。)
这种小动物确是古怪。不管你多么善待它,它也不肯跟着你上街去逛逛。它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是它又那么勇猛,不要说见着小虫和老鼠,就是遇上蛇也敢斗一斗。它的嘴往往被蜂儿或蝎子蛰得肿起来。
赶到猫儿们一讲起恋爱来,那就闹得一条街的人们都不能安睡。它们的叫声是那么尖锐刺耳,使人觉得世界上若是没有猫啊,一定会更平静一些。
可是,及至女猫生下两三个棉花团似的小猫啊,你又不恨它了。它是那么尽责地看护儿女,连上房兜兜风也不肯去了。
郎猫可不那么负责,它丝毫不关心儿女。它或睡大觉,或上屋去乱叫,有机会就和邻居们打一架,身上的毛儿滚成了毡,满脸横七竖八都是伤痕,看起来实在不大体面。好在它没有照镜子的习惯,依然昂首阔步,大喊大叫,它匆忙地吃两口东西,就又去挑战开打。有时候,它两天两夜不回家,可是当你以为它可能已经远走高飞了,它却瘸着腿大败而归,直入厨房要东西吃。
过了满月的小猫们真是可爱,腿脚还不甚稳,可是已经学会淘气。妈妈的尾巴,一根鸡毛,都是它们的好玩具,耍上没结没完。一玩起来,它们不知要摔多少跟头,但是跌倒即马上起来,再跑再跌。它们的头撞在门上,桌腿上和彼此的头上。撞疼了也不哭。
它们的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辟新的游戏场所。它们到院子里来了。院中的花草可遭了殃。它们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你不肯责打它们,它们是那么生气勃勃,天真可爱呀。可是,你也爱花。这个矛盾就不易处理。
现在,还有新的问题呢:老鼠已差不多都被消灭了,猫还有什么用处呢?而且,猫既吃不着老鼠,就会想办法去偷捉鸡雏或小鸭什么的开开斋。这难道不是问题吗?
在我的朋友里颇有些位爱猫的。不知他们注意到这些问题没有?记得二十年前在重庆住着的时候,那里的猫很珍贵,须花钱去买。在当时,那里的老鼠是那么猖狂,小猫反倒须放在笼子里养着,以免被老鼠吃掉。据说,目前在重庆已很不容易见到老鼠。那么,那里的猫呢?是不是已经不放在笼子里,还是根本不养猫了呢?这须打听一下,以备参考。
也记得三十年前,在一艘法国轮船上,我吃过一次猫肉。事前,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肉,因为不识法文,看不懂菜单。猫肉并不难吃,虽不甚香美,可也没什么怪味道。是不是该把猫都送往法国轮船上去呢?我很难做出决定。
猫的地位的确降低了,而且发生了些小问题。可是,我并不为猫的命运多担什么心思。想想看吧,要不是灭鼠运动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消除了巨害,猫的威风怎会减少了呢?两相比较,灭鼠比爱猫更重要得多,不是吗?我想,世界上总会有那么一天,一切都机械化了,不是连驴马也会有点问题吗?可是,谁能因担忧驴马没有事做而放弃了机械化呢?
 六、在乡下
六、在乡下
虽然刚住了几天,我已经感到乡间的确可喜。在这生活困难的时候,谁也恐怕不能不一开口就谈到钱;在乡下住,第一个好处是可以省下几文。头发长了,需跑出十里八里去理;脚稍微一懒,就许延迟一个星期;头发长了些,可是袋儿里也沉重了些。洗澡,更谈不到。到极热的时候,可以下河;天不够热的时候,皮肤外有一层可以搓卷着玩的泥,也显着暖和而有趣。这就又省了一笔支出。没有卖鲜果,糖食和点心的;这不但省了钱,而且自然地矫正了吃零食的坏习惯。衣服须自己洗,皮鞋须自己擦。路须自己走——没有洋车。就是有,也不能在田埂里走。
除了省钱,还另有好多的精神胜利:评剧、川剧全听不到了,但是可以自己唱。在大黄角树下,随意喊吧,除了多管闲事的狗向你叫几声而外,不会有人来叫“倒好”的。话剧更看不到,可是自己可以写两本呀,有的是功夫!
书是不易得到的,但是偶然找来一本,绝不会像在城里时那样掀一掀就了事。在乡下,心里用不着惦记与朋友们定的约会,眼睛用不着时时看表,于是,拿到一本书的时节,就可以愿意怎么读便怎么读;愿意把这几行读两遍,便读两遍;三遍就三遍;看哪一行不大顺眼,便可以跟它辩论一番!这样,书仿佛就与人成了可以谈心的朋友,而不是书架上的摆设了。
院中有犬吠声,鸡鸭叫声,孩子哭声;院外有蛙声,鸟声,叱牛声,农人相呼声。但这些声音并不教你心中慌乱。到了夜间,便什么声音也没有;即使蛙还在唱,可是它们会把你唱入梦境里去。这几天,杜鹃特别地多,直到深夜还不住地啼唤;老想问问它们,三更半夜地唤些什么?这不是厌烦,而是有点相怜之意。
正在插秧的时候下了大雨,每个农人都面带喜色,却一点不慌,还是那么慢条斯理的,像有成竹在胸的样子。
晚上,油灯欠亮,蚊虫很多;所以早早地就躲到帐子里去。早睡,所以就也早起。睡得定,睡得好,脸上就增加了一点肉——很不放心,说不一定还会变成胖子呢!
 七、读书
七、读书
若是学者才准念书,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那么,我可要多嘴了。
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可是我爱念书。
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我有决定念什么的全权;自幼儿我就会逃学,愣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对,《三字经》便可以代表一类——这类书,据我看,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后去念,反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这类书可真不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犯无期徒刑罪的太多;要不然便是太少——我自己就常想杀些写这类书的人。我可是还没杀过一个,一来是因为——我才明白过来——写这样书的人敢情有好些已经死了,比如写《尚书》的那位李二哥。二来是因为现在还有些人专爱念这类书,我不便得罪人太多了。顶好,我看是不管别人;我不爱念的就不动好了。好在,我爸爸没希望我成个学者。
第二类书也与咱无缘:书上满是公式,没有一个“然而”和“所以”。据说,这类书里藏着打开宇宙秘密的小金钥匙。我倒久想明白点真理,如地是圆的之类;可是这种书别扭,它老瞪着我。书不老老实实地当本书,瞪人干吗呀?我不能受这个气!有一回,一位朋友给我一本《相对论原理》,他说:明白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我下了决心去念这本宝贝书。读了两个“配纸”,我遇上了一个公式。我跟它“相对”了两点多钟!往后边一看,公式还多了去啦!我知道和它们“相对”下去,它们也许不在乎,我还活着不呢?
可是我对这类书,老有点敬意。这类书和第一类有些不同,我看得出。第一类书不是没法懂,而是懂了以后使我更糊涂。以我现在的理解力——比上我七岁的时候,我现在满可以做圣人了——我能明白“人之初,性本善”。明白完了,紧跟着就糊涂了;昨儿个晚上,我还挨了小女儿——玫瑰唇的小天使——一个嘴巴。我知道这个小天使性本不善,她才两岁。第二类书根本就看不懂,可是人家的纸上没印着一句废话;懂不懂的,人家不闹玄虚,它瞪我,或者我是该瞪。我的心这么一软,便把它好好放在书架上;好打好散,别太伤了和气。
这要说到第三类书了。其实这不该算一类;就这么算吧,顺嘴。这类书是这样的:名气挺大,念过的人总不肯说它坏,没念过的人老怪害羞地说将要念。譬如说《元曲》,太炎“先生”的文章,罗马的悲剧,辛克莱的小说,《大公报》——不知是哪儿出版的一本书——都算在这类里,这些书我也都拿起来过,随手便又放下了。这里还就属那本《大公报》有点劲。我不害羞,永远不说将要念。好些书的广告与威风是很大的,我只能承认那些广告做得不错,谁管它威风不威风呢。
“类”还多着呢,不便再说;有上面的三项也就足所证明我怎样地不高明了。该说读的方法。
怎样读书,在这里,是个自决的问题;我说我的,没勉强谁跟我学。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着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
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应该记住自己。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书是怎么来着?”我永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管你这一套!
读得快,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不合我的意,我就练习跳远。书要是不服气的话,来跳我呀!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先看最后的几页,省事。
第三,读完一本书,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一告诉就糟:“嘿,你读《啼笑因缘》?”要大家都不读《啼笑因缘》,人家写它干吗呢?一批评就糟:“尊家这点意见?”我不惹气。读完一本书再打通儿架,不上算。我有我的爱与不爱,存在我自己心里。我爱念什么就念,有什么心得我自己知道,这是种享受,虽然显得自私一点。
再说呢,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工夫去细细分析它,所以根本便不能批评。“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这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去管;有一段教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因此,设若我真去批评,大概是高明不了。
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儿子是自己的好”,我还不晓得,因为自己还没有过儿子。有个小女儿,女儿能不能代表儿子,就不得而知。“老婆是别人的好”,我也不敢加以拥护,特别是在家里。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自己的,一提都头疼!自己的书和自己的运气,好像永远是一对儿累赘。
第五,哼,算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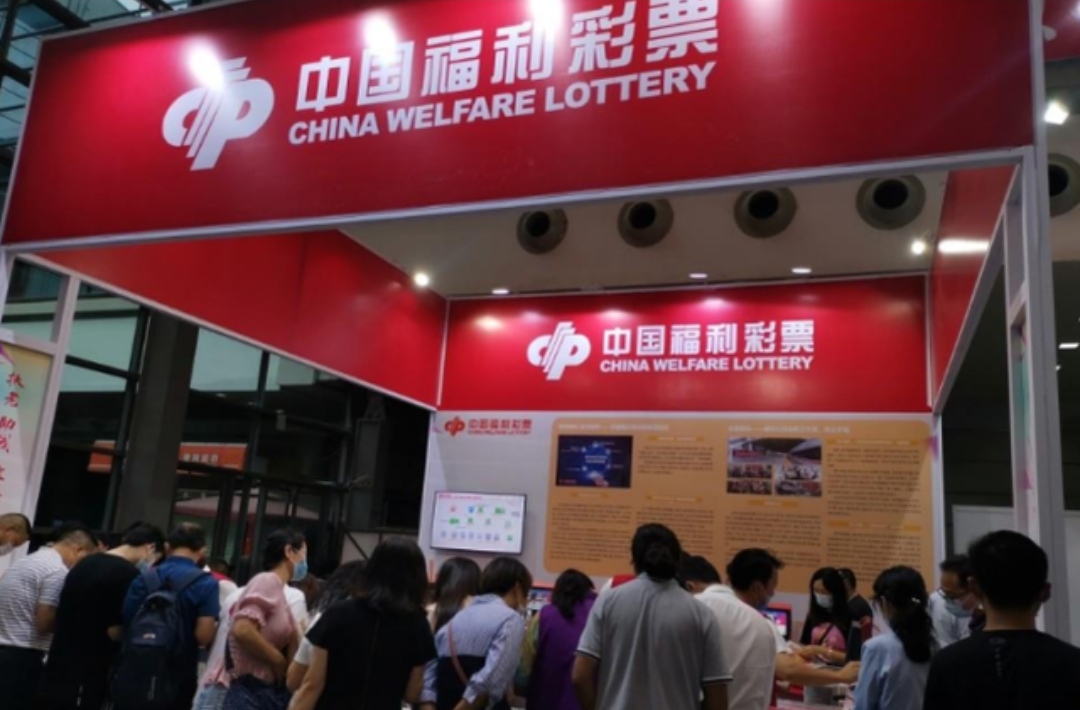 八、买彩票
八、买彩票
在我们那村里,抓会赌彩是自古有之。航空奖券,自然地,大受欢迎。头彩五十万,听听!二姐发起集股合作,首先拿出大洋二角。我自己先算了一卦,上吉,于是拿了四角。和二姐计算了好大半天,原来还短着九元四才够买一张的。我和她分头去宣传,五十万,五十万,五十个人分,每人还落一万,二角钱弄一万!举村若狂,连狗都听熟了“五十万”,凡是说“五十万”的,哪怕是生人,也立刻摇尾而不上前一口把腿咬住。闹了整一个星期;十元算是凑齐;我是最大的股员。三姥姥才拿了五分,和四姨五姨共同凑了一股;她们还立了一本账簿。
上哪里去买呢?还得算卦。二姐不信任我的诸葛金钱课,花了五大枚请王瞎子占了一个马前神课……利东北。城里有四家代售处;利成记在城之东北;决议,到利成记去买。可是,利成是四家买卖中最小的一号,只卖卷烟煤油,万一把十元拐去,或是卖假券呢!又送了王瞎子五大枚,从新另占。西北也行,他说;不但是行,他细掐过手指,还比东北好呢!西北是恒祥记,大买卖,二姐出阁时的缎子红被还是那儿买的呢。
谁去买?又是一个问题。按说我是头号股员,我应当跑一趟。可是我是属牛的,今年是鸡年,总得找属鸡的。还得是男性,女性丧气。只有李家小三是鸡年生的,平日那些属鸡的好像都变了,找不着一个。小三自己去太不放心啊,于是决定另派二员金命的男人妥为保护。挑了吉日,三位进城买票。
票买来了,谁拿着呢?我们村里的合作事业有个特点,谁也不信任谁。经过三天三夜的讨论,还是交给了三姥姥,年高虽不见得必有德,可是到底手脚不利落,不至私自逃跑。
直到开彩那天,大家谁也没睡好觉。以我自己说,得了头彩——还能不是我们得吗?!——就分两万,这两万怎么花?买处小房,好,房的地点,样式,怎么布置,想了半夜。不,不买房子,还是做买卖好,于是铺子的地点、形式、种类,怎么赚钱,赚了钱以后怎样发展,又是半夜。天上的星星,河边的水泡,都看着像洋钱。清晨的鸡鸣,夜半的虫声,都说着“五十万”。偶尔睡着,手按在胸上,梦见一堆现洋压在身上,连气也出不得!特意买了一副骨牌,为是随时打卦。打了坏卦,不算,另打;于是打的都是好卦,财是发准了。
开奖了。报上登出前五彩,没有我们背熟了的那一号。房子、铺子……随着汗全走了。等六彩七彩吧,头五奖没有,难道还不中个小六彩?又算了一卦,上吉;六彩是五百,弄几块做件夏布大衫也不坏。于是,一边等着六彩七彩的揭露,一边重读前五彩的号数,替得奖的人们想着怎么花用的方法,未免有些羡妒,所以想着想着便想到得奖人的乐极生悲,也许被钱烧死了;自己没得也好;自然自己得奖也不见得就烧死。无论怎么说,心中有点发堵。
六彩七彩也登出来了,还是没咱们的事,这才想起对尾子,连尾子都和我们开玩笑,我们的是个“三”,大奖的偏偏是个“二”,没办法!
二姐和我是发起人呀!三姥姥向我们俩要索她的五分。没法不赔她。赔了她,别人的二角也无意虚掷。二姐这两天生病,她就是有这个本事,心里一想就会生病。剩下我自己打发大家的二角。打发完了,二姐的病也好了,我呢,昨天夜里睡得很清甜。
 九、西红柿
九、西红柿
所谓番茄炒虾仁的番茄,在北平原叫作西红柿,在山东各处则名为洋柿子,或红柿子。想当年我还梳小辫,系红头绳的时候,西红柿还没有番茄这点威风。它的价值,在那不文明的时代,不过与“赤包儿”相等,给小孩子们拿着玩玩而已。大家做“娶姑娘扮姐姐”玩耍的时节,要在小板凳上摆起几个红胖发亮的西红柿,当作喜筵,实在漂亮。可是,它的价值只是这么点,而且连这一点还不十分稳定,至于在大小饭铺里,它是完全没有份儿的。这种东西,特别是在叶子上,有些不得人心的臭味——按北平的话说,这叫作“青气味儿”。所谓“青气味儿”,就是草木发出来的那种不好闻的味道,如楮树叶儿和一些青草,都是有此气味的。可怜的西红柿,果实是那么鲜丽,而被这个味儿给累住,像个有狐臭的美人。不要说是吃,就是当“花儿”看,它也是没有“凉水茄”“番椒”等那种可以与美人蕉、翠雀儿等草花同在街上售卖的资格。小孩儿拿它玩耍,仿佛也是出于不得已;这种玩意儿好玩不好吃,不像落花生或枣子那样可以“吃玩两便”。其实呢,西红柿的味道并不像它的叶子那么臭恶,而且不比臭豆腐难吃,可是那股青气味儿到底要了它的命。除了这点味道,恐怕它的失败在于它那点四不像的劲儿:拿它当果子看待,它甜不如果,脆不如瓜;拿它当菜吃,煮熟之后屁味没有,稀松一堆,没点“嚼头”;它最宜生吃,可是那股味儿,不果不瓜不菜,亦可以休矣!
西红柿转运是在近些年,“番茄”居然上了菜单,由英法大菜馆而渐渐侵入中国饭铺,连山东馆子也要报一报“番茄虾银(仁)儿”!文化的侵略哟,门牙也挡不住呀!可是细一看呢,饭馆里的番茄这个与那个,大概都是加上了点番茄汁儿,粉红怪可看,且不难吃;至于整个的鲜番茄,还没多少人肯大嘴地啃。肯生吞它的,或者还得算留过洋的人们和他们的儿女,到底他们的洋味地道些。近来西医宣传西红柿里含有维他命A至W,可是必须生吃,这倒有点别扭。不过呢,国人是注意延年益寿,滋阴补肾的东西,或者这点青气味儿也不难于习惯下来的;假如国医再给证明一下:番茄加鹿茸可以壮阳种子,我想它的前途正自未可限量咧。
 十、落花生
十、落花生
我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口袋里装上四个铜板的落花生,一边走一边吃,我开始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假若有人问我:“你要是做了皇上,你怎么享受呢?”简直地不必思索,我就答得出:“派四个大臣拿着两块钱的铜子,爱买多少花生吃就买多少!”
什么东西都有个幸与不幸。不知道为什么瓜子比花生的名气大。你说,凭良心说,瓜子有什么吃头?它夹你的舌头,塞你的牙,激起你的怒气——因为一咬就碎;就是幸而没碎,也不过是那么小小的一片,不解饿,没味道,劳民伤财,布尔乔亚!你看落花生:大大方方的,浅白麻子,细腰,曲线美。这还只是看外貌。弄开看:一胎儿两个或者三个粉红的胖小子。脱去粉红的衫儿,象牙色的豆瓣一对对地抱着,上边儿还结着吻。那个光滑,那个水灵,那个香喷喷的,碰到牙上那个干松酥软!白嘴吃也好,就酒喝也好,放在舌上当槟榔含着也好。写文章的时候,三四个花生可以代替一支香烟,而且有益无损。
种类还多呢:大花生,小花生,大花生米,小花生米,糖饯的,炒的,煮的,炸的,各有各的风味,而都好吃。下雨阴天,煮上些小花生,放点盐;来四两玫瑰露;够作好几首诗的。瓜子可给诗的灵感?冬夜,早早地躺在被窝里,看着《水浒》,枕旁放着些花生米;花生米的香味,在舌上,在鼻尖;被窝里的暖气,武松打虎……这便是天国!冬天在路上,刮着冷风,或下着雪,袋里有些花生使你心中有了主儿;掏出一个来,剥了,慌忙往口中送,闭着嘴嚼,风或雪立刻不那么厉害了。况且,一个二十岁以上的人肯神仙似的,无忧无虑地,随随便便地,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吃花生,这个人将来要是做了宰相或度支部尚书,他是不会有官僚气与贪财的。他若是做了皇上,必是朴俭温和直爽天真的一位皇上,没错。
吃瓜子的照例不在街上走着吃,所以我不给他保这个险。
至于家中要是有小孩儿,花生简直比什么也重要。不但可以吃,而且能拿它们玩。夹在耳唇上当环子,几个小姑娘就能办很大的一回喜事。小男孩若找不着玻璃球儿,花生也可以当弹儿。玩法还多着呢。玩了之后,剥开再吃,也还不脏。两个大子儿的花生可以玩半天;给他们些瓜子试试。
论样子,论味道,栗子其实满有势派儿。可是它没有落花生那点家常的“自己”劲儿。栗子跟人没有交情,仿佛是。核桃也不行,榛子就更显着疏远。落花生在哪里都有人缘,自天子以至庶人都跟它是朋友;这不容易。
在英国,花生叫作“猴豆”——Monkey nuts。人们到动物园去才带上一包,去喂猴子。花生在这个国里真不算很光荣,可是我亲眼看见去喂猴子的人——小孩就更不用提了——偷偷地也往自己口中送这猴豆。花生和苹果好像一样地有点魔力,假如你知道苹果的典故;我这儿确是用着典故。
美国吃花生的不限于猴子。我记得有位美国姑娘,在到中国来的时候,把几只皮箱的空处都填满了花生,大概凑起来总够十来斤吧,怕是到中国吃不着这种宝物。美国姑娘都这样重看花生,可见它确是有价值;按照哥伦比亚的哲学博士的辩证法看,这当然没有误儿。
花生大概还跟婚礼有点关系,一时我可想不起来是怎么个办法了;不是新娘子在轿里吃花生,不是;反正是什么什么春吧——你可晓得这个典故?其实花轿里真放上一包花生米,新娘子未必不一边落泪一边嚼着。
 十一、吃莲花的
十一、吃莲花的
少见则多怪,真叫人愁得慌!谁能都知都懂?就拿相对论讲吧:到底怎样相对?是像哼哈二将那么相对,还是像情人要互吻时那么面面相对?我始终弄不清!况且,还要“论”呢。一向不晓得哼哈二将会作论;至于情人互吻而必须作论,难道情人也得“会考”?
这且不提:拿些小事说“眼生”就要恶意地发笑,“眼熟”的事儿是对的,至少也比“眼生”的文明些。中国人用湿毛巾擦脸,英美人用干的;中国人放伞头朝上,西洋鬼子放伞头朝下;于是据洋鬼子看,他们文明,我们是头朝下活着。少见多怪,“怪”完了还自是自高一下,愁人得慌!
这且不提。听说广东人吃狗。每逢有广东朋友来,我总把黄子藏到后院去。可是据我所知道的广东朋友们,还没有一位向我要求过:“来,拿黄子开开斋!”没有。可是,黄子还是在后院保险。
这且不提。虽然我不“大”懂相对论——不是一点也不懂,说不定它还就许是像哼哈二将那样的对立——可是我天性爱花草。盆花数十种,分对列于庭中,大概我不见得一定比爱因司坦[1]低下着多少。不,或者我比他还高着些。他会相对——和他的夫人相对而坐,也许是——而且会论——和他的夫人论些家长里短什么的。我呢,会种花。我与他各有一出家手戏,谁也不高,谁也不低。他要是不服气的话,他骂我,我也会骂他。相对论,我得承认他的优越;相对骂,不定谁行呢!这样,我与他本是“肩膀齐为弟兄”,他不用吹,我用不着谦卑。可是,我的盆花是成对摆列着的,兰对兰,菊对菊,盆盆相对,只欠着一个“论”;那么,我比他强点!
这且不提——就使我真比爱因司坦强,也是心里的劲,不便大吹大擂地宣传,我不是好吹的人;何必再提?今年我种了两盆白莲。盆是由北平搜寻来的,里外包着绿苔,至少有五六十岁。泥是由黄河拉来的。水用趵突泉的。只是藕差点事,吃剩下来的菜藕。好盆好泥好水敢情有妙用,菜藕也不好意思了,长吧,开花吧,不然太对不起人!居然,拔了梗,放了叶,而且开了花。一盆里七八朵,白的!只有两朵,瓣尖上有点红,我细细地用檀香粉给涂了涂,于是全白。作诗吧,除了作诗还有什么办法?专说“亭亭玉立”这四个字就被我用了七十五次,请想我作了多少首诗吧!
这且不提。好几天了,天天门口卖菜的带着几把儿白莲。最初,我心里很难过。好好的莲花和茄子冬瓜放在一块,真!继而一想,若有所悟。啊,济南名士多,不能自己“种”莲,还不“买”些用古瓶清水养起来,放在书斋?是的,一定是这样。
这且不提。友人约游大明湖,“去买点莲花来!”他说。“何必去买,我的两盆还不可观?”我有点不痛快,心里说:“我自种的难道比不上湖里的?真!”况且,天这么热,游湖更受罪,不如在家里,煮点毛豆角,喝点莲花白,作两首诗,以自种白莲为题,岂不雅妙?友人看着那两盆花,点了点头。我心里不用提多么痛快了;友人也很雅哟!除了作新诗向来不肯用这“哟”,可是此刻非用不可了!我忙着吩咐家中煮毛豆角,看看能买到鲜核桃不。然后到书房去找我的诗稿。友人静立花前,欣赏着哟!
这且不提。及至我从书房回来一看,盆中的花全在友人手里握着呢,只剩下两朵快要开败的还在原地未动。我似乎忽然中了暑,天旋地转,说不出话。友人可是很高兴。他说:“这几朵也对付了,不必到湖中买去了。其实门口卖菜的也有,不过没有湖上的新鲜便宜。你这些不很嫩了,还能对付。”他一边说着,一边奔了厨房。“老田,”他叫着我的总管事兼厨子,“把这用好香油炸炸。外边的老瓣不要,炸里边那嫩的。”老田是我由北平请来的,和我一样不懂济南的典故,他以为香油炸莲瓣是什么偏方呢。“这治什么病,烫伤?”他问。友人笑了。“治烫伤?吃!美极了!没看见菜挑子上一把一把儿地卖吗?”
这且不提。还提什么呢,诗稿全烧了,所以不能附录在这里。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