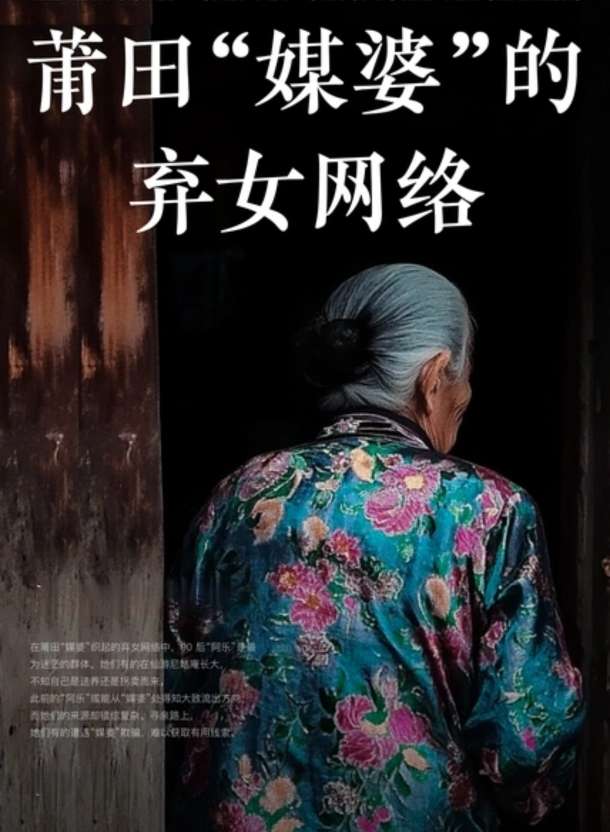
180后红梅知道自己的“阿乐”身份,已是上世纪90年代。尽管年少,她依旧知道这个身份意味着自己的生命里经历了什么。
近30年过去了,她还记得六七岁时眼见的那一幕。
“‘阿乐’来咯……”女人吆喝的同时,放下扁担,竹筐落地,声音闷沉,地上尘土扬起。
一群孩子迅速围过去,女人掀起盖得严实的布,两个交错摆放的女婴露出身子,一个的头紧挨着另一个的脚。
买“阿乐”的大人摇摇头。女人又掀开一层,还是两个女婴,再下一层又是两个。有的脐带没断,有的穿着单薄,裸露的皮肤上爬满大片痱子。
那些围观买“阿乐”的女孩们,多数也是“阿乐”。时光倒退几年,这也是她们曾经的遭遇。
2从上世纪60年代到新世纪初,数万弃女就这样流入莆田及周边的仙游、泉州地区的农民、盐民、渔民家里,多养作童养媳。她们最初来自福建长乐,因此都被叫做“阿乐”。
那个被红梅等“阿乐”围着的女人,在当地被称作“媒婆”,多数是早年从莆田嫁到长乐乡村的女人。正是她们上下翻动的手,翻转了竹筐里那些女婴一生的命运。
红梅1985年左右生,成长在福建莆田灵川镇。她90后的邻居阿妹,就是那时阿叔花了四五百元买下的。“媒婆”们当时经手的女婴,范围从一百多公里外的福建长乐,拓展到闽侯、连江、宁德等福建地区乃至浙江、江西、海南等外省地区。她们共享着同一个名字“阿乐”,也共同遥想着同一个故乡长乐,因为大多数“阿乐”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来。
3她们在异乡飘摇,长大成人,一个接一个找回长乐;而当年送出女儿的长乐父母,也开始寻亲。“媒婆”,成了她们共同的目标。
从这根纽带反馈回来的信息,往往令寻亲者失望甚至绝望——“媒婆”像莆田做其他游贩生意的人一样,一手转一手,把孩子从长乐运到莆田,规模成潮,网络复杂。
这张越拉越大的网里,早年流动着各地家贫养不起的女儿,后来又汇流了因政策问题被弃的女婴,以及后来从全国各地被拐卖的幼女。有往长乐寻亲的“阿乐”,后来在浙江温州、福建宁德,甚至贵州和云南找到了亲生父母。
梅花镇的女儿
4“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9岁那年,小学生红梅这样哭着回家大声问养父母。
那天,村里来了长乐人,挨家挨户寻“阿乐”,要找早年送出的女儿。邻居老人逗红梅,“你爸你妈来找你了”。红梅生了疑,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养女,自己两个70后姑姑也是,不过从来没人当面喊过红梅“阿乐”。
小女孩的疑问最终被家人证实——养父母不能生育,1985年正月二十七,亲戚在长乐汽车站的“媒婆”那里,花四百元钱买回了她。不止红梅,她妹妹也是买回来的。
5“媒婆”称,红梅来自从长乐梅花镇。“媒婆”是莆田涵江人,早年嫁到临海的渔镇梅花镇,后来专门从那里抱孩子。养父母接过女婴,取名“红梅”,名字里包含着她的家乡。
长大后,红梅去梅花镇寻亲。镇上的老人告诉红梅,这里两个“媒婆”,都是早年从莆田嫁过来的,矮矮瘦瘦的那个去世了,胖胖高高的白秋芳,不知去向。
红梅走遍梅花镇每个村庄,打听每户送出女儿的人家,来来回回十年,还是找不到自己的家。她原以为,找到“媒婆”,就可以顺藤摸到亲生父母。许多二三十年前就开始寻亲的人也同样困惑——不是在电视上发个广告,在报纸上刊一纸启事,亲人就可以看到吗?
6找到长乐潭头镇的吴白荷后,红梅才模糊知道了答案。从莆田嫁来的吴白荷以前是“批发头子”,潭头镇和周边乡镇的弃女,多数由“媒婆”搜罗来卖给吴白荷。不少在莆田卖孩子的“媒婆”,从莆田跋涉坐车去吴白荷家,“批发”了孩子,再运到莆田。
红梅找到吴白荷,给了她几千块钱求信息。得到的回答是,经她手上送走的孩子成千上万。2013年前后,吴白荷去世,如今已经无法求证她到底经手了多少孩子。那些辗转过来想找到线索的“阿乐”,会被她的儿女们告知:抱孩子的事是母亲做的,我们不知道更多的信息。
7更何况,从这里送出的女儿太多了。人口超过71万的沿海城市长乐,近三十年间流向莆田的女婴,按寻亲者估算,规模逾两万。
“长乐每个乡镇都有莆田来的女人。”孙小萍比其他寻亲的“阿乐”更早发现了这点。新世纪初,她便走遍长乐十八个乡镇的每一个村庄,寻访每一个“媒婆”,至今还没找到亲人。
一位长乐民俗专家分析,民间将抱走孩子的女人称为“媒婆”,是取“媒介”的意思,当时乡间将信息灵通的介绍人都称为“媒人”或“媒婆”,他们流通包括民间借贷、婚嫁、抱养等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