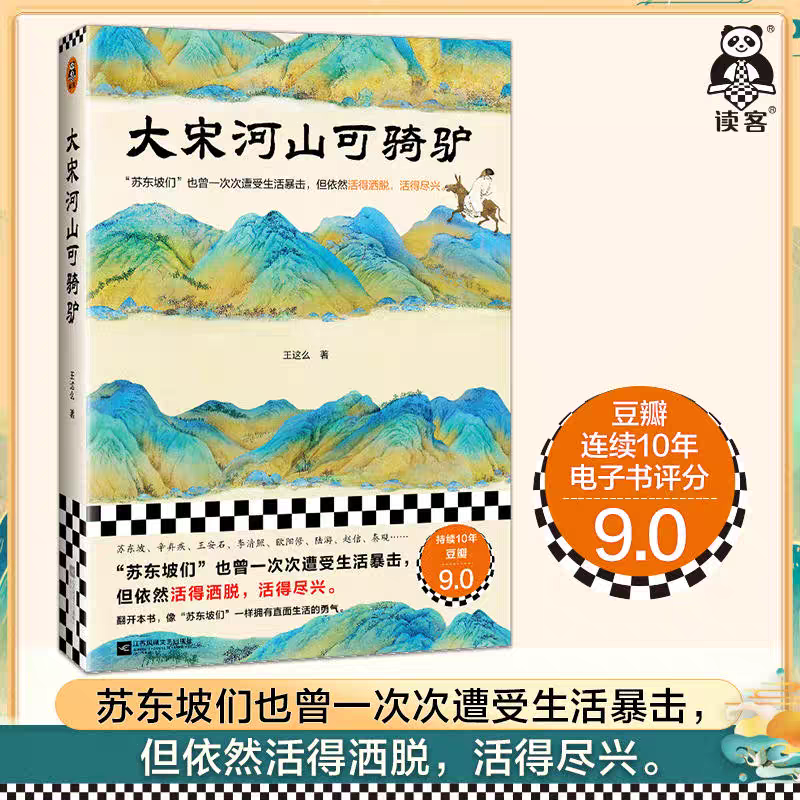
在缺马的朝代找一匹老马
1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陆游的悲痛,是整个南宋有志之士的悲痛。后人论及,往往会痛恨主和派的投降主义,归咎于天子昏庸。然而,如果没有这些阻碍,南宋真的就能成功地“还我河山”?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也不妨在既成的事实中,寻找一些必然与偶然交错的症结。
大家都知道,军事力量一直是两宋王朝的致命弱点,经济、文化都已发展到高峰,却受制于外族的武力威胁,跟强汉盛唐没法比。但也要了解,北宋之建国,本来就先天不足:它承接了五代十国的乱摊子,名义上统一,实际上是分裂成了几个并立的民族政权。北宋所能真正掌控的范围,仅在传统的中原地带。起点既不高,生存环境又不佳——正逢辽、西夏等的游牧民族向定居过渡、建立王朝的上升时期。
2比起盘旋于境外的草原铁蹄,靠兵变起家的赵家天子,深知对于皇帝宝座的安稳,内乱比外敌更直接、更可怕,所以皇朝的立国之本,就是抓紧兵权,重文抑武,守内虚外,建立高度发达的文官政治体系,将武将地位一再压低。然而在文人政治生存环境空前宽松、文采风流鼎盛的同时,武将素质却每况愈下,终至于,战事起时,举国无可用之将才。
将才凋零,相匹配的,自然是兵不堪用。高度中央集权的用兵制度,兵将分离,文官带兵,减少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却也“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无法训练出高素质、高效率的部队。于是采取人海战术,以数量来弥补质量不足。
3军备是宋朝财政消耗的重头,北宋前期,每年的军费开支即已超过财政支付能力。朝廷不得不鼓励军队经商,结果官兵武艺更加废弛,只好再扩充军队。最高峰时全国军队人数达一百二十万,受天子直辖的禁军就占了八十万,都用于拱卫京师,弹压地方,一旦有战事,根本不受将帅调派。南宋时岳飞之所以战绩辉煌,就是靠亲手建立、训练的“岳家军”。成绩出来,朝廷的猜忌也跟着来了。
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时候,大宋王朝的职业军人们,走走私,经经商,合资开个茶楼酒店,小日子快活得很,却苦了国家,每年向辽、西夏交岁币也就罢了,还要给这支庞大的军队按月发饷,实在让执政者叫苦连天又无可奈何。
4军事力量薄弱,还有一个很重要又很荒诞的原因:两宋严重缺马,是中国历史上最缺少马匹的朝代。尤其到了南宋,像陆游,他那么想骑马,就不能找匹马过过干瘾吗?他始终骑在驴背上跑来颠去,实在也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普通官员,想找匹马骑,也是很不容易的。
冷兵器时代,战马是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指标。没有战马,就没有能在战争中作为制胜关键的骑兵部队。北宋一开始对辽战争胜少败多,这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为什么没有马?历来产马的地方——西北、塞北、关东、西南全被其他民族政权占走了。中原地带以农耕为主,环境很不适宜养殖马匹,只能高价去向辽、西夏和大理买马。
5这种情况下还敢跟人打仗?一打仗立刻被封锁战马进口。到了南宋,与北方势成水火,每战都会损失大批战马。每一战败,恢复元气就难上加难,不得不议和以求休养生息。主和派对主战派恨得要命——老实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你不顾实力地冒进,难道不会害得大家全体完蛋?
滇、川、藏三角地带丛林中的那条茶马古道,就是自唐宋以来,用中原茶叶与边疆各国进行马匹交易的通道。南宋时,“关陕尽失”,西北地带的茶马交易已经无法进行,只得把重心转移到西南。大理也是产马区,马以个子小、能负重、善走山路著名,却并不适用于作战,运运军粮还差不多。战马还是西北的好。
6平时民间只得驴子骑。这是个驴子普及的朝代,翻开两宋诗文,驴的出场率远高于马。《清明上河图》反映汴京繁华实景,里面的马也寥寥。陆游关于驴和马的怨念,就很能解释了。但是呢,用曹操的诗来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陆游骑不成马,在后人看来,也没什么关系了,他早已在岁月里,把自己变成了一头悲壮的老马。
对于军队缺马这种心头患,两宋王朝都想了不少办法,其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外交史与商战史。北宋经历的两次政治革新尝试——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重头内容都涉及马。
王安石的“保马法”,让民间养马,然后再由政府出资买回,听起来很好,却和其他新法一起,很快流产了。
7关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从刚开始一直到千年后的今天,毁誉不一。只有两点是毫无疑问的:它像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每一次变法,在阵痛与代价中摇摆前进;而不论成果如何,首倡者,都有一个黯然悲凉的结局。
熙宁九年(1076年),推行新法六年后,五十六岁的王安石退居江宁(今南京)。新法推行过程中的斗争令人厌倦;无休止地应对争论和排除阻扰;突如其来的罢相;被诬告谋反,理由荒谬得让人听到的一瞬间,不是愤怒而是失笑;吕惠卿之流的背叛和暗算,让人直接对人性产生怀疑;寄予厚望的爱子王雱,聪慧机灵,才气逼人,亦在这一年病亡,年仅三十三岁。
8心灰意懒,急流勇退。不退也不能。仍在推行中的新法,像一艘开往未知海域的轮船,刚刚启程,就已经挤满了精明能干的野心家、利欲熏心的投机者。作为老船长的王安石,早已被挤到船舷边。
在江宁的日子,据记载,是这样的:“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自山距州城适相半,谓之半山。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zè乃归。”
就是骑着驴子,来来回回地在山水间走,每日如此。王安石是个坐不住的人,这一点可以想象。当年,他可是号称“拗相公”,说起国事,不惜跟好友翻脸,不惮在皇帝面前抗辩,厉声高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