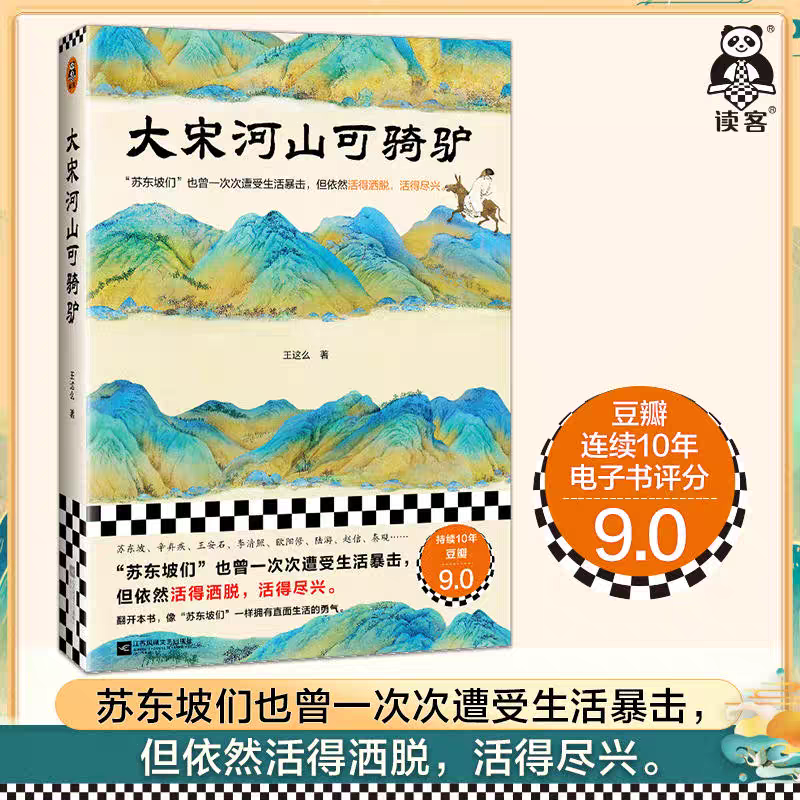
1「文前」这本书不是传统的词话,而是宋代文人生活的切片,是大宋风骨的另一种解读。那些骑着驴的词人,并不是风花雪月的雅士,而是理想主义的朝圣者,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怀揣一纸青词,走向命运的旷野……
文人的一生,往往是从金銮殿到荒野,从庙堂到江湖,骑驴而去,青衣染尘。那些未被提起的,还有骑马的、放鹤的、煮酒的、种花的……他们或孤傲、或疏狂、或温柔如水,各自在词里留下体温与魂魄。当你一首首读下去,会突然明白:原来真正的美感,不是震耳欲聋的喧嚣,而是像驴蹄轻踏在江南小路上的声音——慢,却稳,且远。
想当将军的诗人
2“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驴跟诗人,好像是一对完美的拍档。
诗人的气质,跟高头大马的确不搭调;而驴,体格小巧,加上诗人缓步而行的翩翩风度,就很相得益彰了。唐代郑綮qìng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边走边比画,“推”好呢还是“敲”好,也只能骑驴。
驴背平坦舒适,弱不禁风的小媳妇都可以安然坐着回娘家。马骑乘起来,就正式且粗犷得多,要配鞍,否则颠死你;得经过训练,不然摔死你;还要身姿挺拔,被坚硬的马鞍束缚着,在马上,人只能保持一种紧绷而待发的状态。连赏花那么优雅的事,骑马去就会变成一场盛会、一次游行:“一日看尽长安花”“踏花归去马蹄香”。昂扬,且快意。
3驴性愚执,形容冥顽不灵者,会说“春风不入驴耳”。诗人通常也有这种毛病,主观想法太多,不听劝谏。和马相处时间久了,是战友,是同志,风里雨里共进退,一个眼色,莫逆于心。驴则更像游伴,再相处融洽,私底下都有些小别扭,你想往东,它偏往西,这时候你俩得好好就地协商一下了。
驴跟马的区别,陆游是很明白的。“此身合是诗人未?”剑门关下,陆游很不高兴地嘀咕着,这一生,才不乐意骑驴,才不爱当诗人!他想骑的是战马“的卢”,想做的是如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将军。他不是将军,连战士都算不上。八十四年的人生里,他真正的军旅生涯只有一年多,而且是文职,而且年纪不小了。这一年的事情,他用足后半生来回忆和书写。
4“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过剑门关这一年,陆游四十八岁。孔子云“五十而知天命”,不该再发牢骚、再有无谓梦想。
岳飞、秦桧已死,被皇帝生涯弄得心力交瘁的宋高宗退位,换了年轻气盛的宋孝宗,上来雷厉风行,批秦桧,平反岳飞冤案,起用老将张浚北伐。没几日,兵败如山倒,朝野仓皇。热腾腾的激情,碰上兜头一大瓢冷水。主和派开始猛放马后炮,主战派必须有人为国耻负责。刚刚被皇帝爱才而赐进士出身的陆游,躬逢其盛,立刻又被免职了。“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罪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基本上属于派系间的打击报复。不久,陆游又被弄到夔州去当了通判。
5通判这个官位非常有意思,州郡长官的副职,协助处理事务;虽然只是八品官,却是由皇帝亲自委派的,可以直接向皇帝奏报州郡内一切官员的情况,暗地里起着监察与制约地方官的作用。
可见此时,皇帝对陆游还是颇有回护。只要站对队伍,抱对大腿,前途还是大有可为。很可惜,陆游这个人,天生一根筋,好像磨坊里的那头驴子,给它一只悬在眼前的胡萝卜,能转个一生一世。
那根“胡萝卜”,就是岳飞也曾经执着过的“靖康耻,犹未雪”,就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6陆游的家在汴梁,世代为官,到他这一代,风云突变。三岁时,金军攻陷汴梁,他被母亲抱在怀里,随着乱军和呼号的流民逃到江南。即使年纪尚小,他也是南渡之民,血液里有流亡的耻辱记忆,有故国三千里的不堪与思念,像火一样灼烈,像刀锋一样尖刻。无日可忘。
早慧孩子的志向,被长辈的哭泣与追忆敲打,他长成了热血沸腾的青年。习文,学剑,钻研兵法……像将要脱弦的箭,直指前程。
因为家世,他早早荫补为“登仕郎”,一个名义上的正九品,通往仕途最起始的阶梯。不过,必须参加一次吏部的考核,才能被正式授予官职。进临安城应试这年,陆游十六岁,首尝败绩。十九岁,他参加贡举考试,入闱,在礼部又被刷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