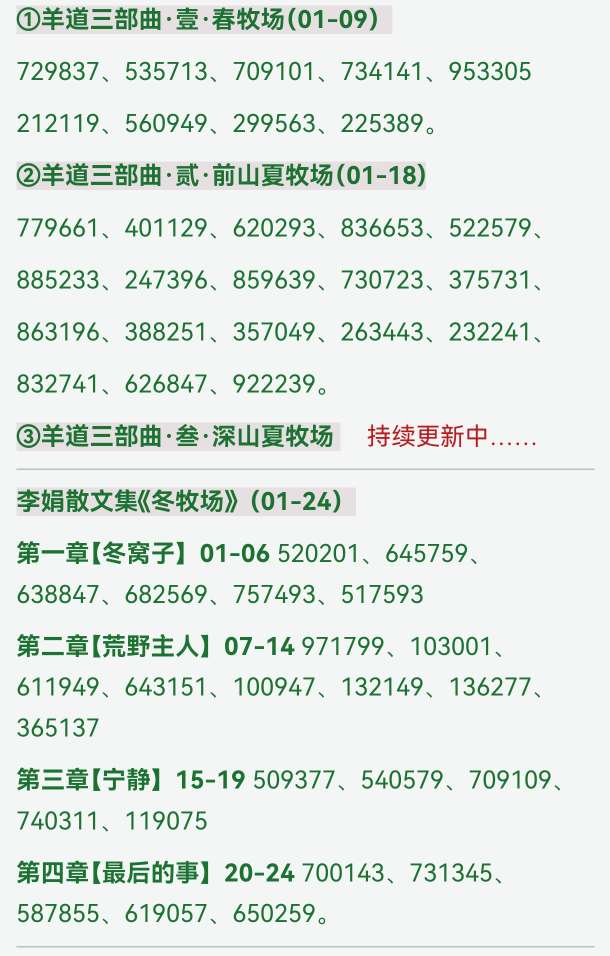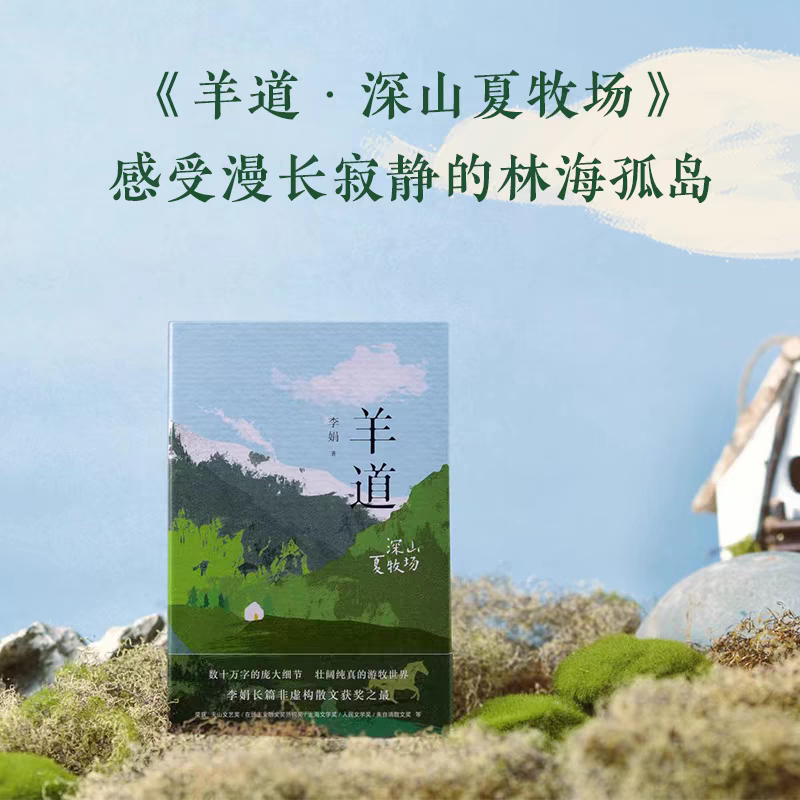
〔1〕哈萨克游牧家庭中处处充斥着羊毛制品,穿的、盖的、用的……统统厚实又沉重。对此,我的一个朋友提出疑问:“他们为什么不用羽绒?保暖性更强,并且轻便多了,更适合颠簸动荡的生活。”并举例,在高寒的西伯利亚地带,羽绒制品自古以来多么普及……
听她这么一说,我也颇感疑惑。想了很久才想通这个问题……真是!这种问题还用想吗?哈萨克牧人当然不会使用羽绒制品了,因为他们放的是羊,又不是鸭子。
在商品交易不便的遥远年代里,除了茶叶、面粉之类有限的物品需要交易得来,其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得自给自足。
〔2〕现在呢,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了。塑料绳能代替羊毛绳,牛奶分离机能代替捶酸奶的查巴袋,机制地毯能代替手绣的花毡,钢管骨架的毡房能代替红栅墙的木架毡房,连笼罩在毡房外的毡盖都有更加洁白耀眼的帆布可代替。
但是,远远不能完全代替。塑料绳虽然便宜,却不结实。它经不起转场路上的风吹日晒,不到一个月就脆裂开来。牛奶分离机制作的奶疙瘩由于干干净净地剔去了奶油,口感又硬又酸。而机制地毯花纹千篇一律,且不如花毡结实耐用。钢铁的毡房较为沉重,不便运送,其结构也没有木架毡房那么结实稳固。而且木栅栏的毡房使用起来更加灵活,可大可小,可高可矮。哪怕就两排房架子还能搭个依特罕呢。
〔3〕而更轻便更保暖的羽绒垫永远代替不了花毡,羽绒衣也代替不了羊皮大衣和羊毛坎肩。后者抗摔抗打,足以身经百战。羽绒衣呢,森林里、石崖边,扯扯挂挂,磕磕碰碰,没几天,羽絮就飞得剩不了几根了……牧人是天长地久生存于野外的,不是搞户外休闲活动的。
除非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彻底消失,否则传统细节也很难消亡吧?
全部的生活从羊开始。春天出生的羔羊,秋天死于无罪。它死后,生命仍未结束。它的毛发絮在家的每一道缝隙里,它的骨肉温暖牧人的肠胃,它的肚囊盛装黄油,它的皮毛裹住雪地中牧羊人的双腿。它仍然是这个家的一部分。
〔4〕早在五月底,就有一部分大羊脱掉了羊毛衣服。到了六七月间,天气越来越暖和,当年生的羊羔也开始脱衣服了。那时羊羔已经很大了。每天赶羊羔入栏时,面对拥上来的一群体态相似的羊,我几乎分不清大羊和羊羔。
晴朗的日子里,在羊群回家吃盐的间隙,斯马胡力和海拉提都会把一部分羊堵在南面石头山下的两块巨石间,挨个儿上绑,脱衣服。那种情景我只观摩过一次,只看了一小会儿,就实在看不下去了……剪羊毛,并不是一绺一绺地剪,而是成片地从羊皮上剪下来。就像剥橘子皮似的,剥下来后仍完整地连成一大片。
〔5〕只见斯马胡力张开羊毛剪子(说是剪子,其实就是两片尾部套连在一起的长刀片,跟个大铁夹子一样,没有剪刀把柄),插进密密的毛丛,一只手夹住一大片羊毛根部,另一只手握住刀尖一端,双手合力一捏,就有一片羊毛从羊身上剥离了。如是一刀一刀又一刀……斯马胡力的羊毛剪刀一尺多长,相比之下,羊那么小。他看也不看,逮着就插刀子,插进去就剪。这一家伙下去,要是不小心夹块肉,非捅出一个血窟窿不可!事实上,也的确给人家夹了好多狭长的血口子,看得人心惊肉跳。想起在吉尔阿特,这家伙给骆驼剪毛,也老是弄得人家一身血口子。真差劲!
〔6〕刚脱完衣服的羊看上去跟斑马似的,光身子上整齐排列着一道一道剪刀印儿。
剪下的羊毛像一块块完整的羊皮一样,一张叠着一张,在草地上堆起了蓬松的一大堆。听说不久后会运到下游耶克阿恰那里卖掉,我便又开始瞎操心了:这么多的羊毛,小山一样,怎么运走啊?如果紧紧地塞进大麻袋的话,至少得塞十个麻袋吧?而我家根本就没有大麻袋,只有二十五公斤容量的复合饲料袋和面粉袋。这种袋子起码也得装三十个吧,可我家总共就十来个……
〔7〕接下来,只见大家把羊毛片抖开,平铺在地上,像叠扑克牌一样,一张叠一张,铺了长长一溜儿,最后用一根短棍横着裹在最端头的那张羊毛里。接下来卡西手持棍子两端开始拧动。斯马胡力蹲在地上,随着拧动幅度一点一点把羊毛块朝相反方向卷掖。于是很快地,像拧绳子一样,这一长溜羊毛片被拧成了一大股水桶粗的“绳子”(因羊毛片之间有摩擦力,不至于卷散了)。斯马胡力卷到最后,用手拽住最端头不动,另一端的卡西继续拧动短棍上劲。当这股粗壮的羊毛绳被拧得很紧很紧的时候,海拉提才上前帮忙,在绳子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处各拦腰折叠一下。
〔8〕兄妹俩缓缓松手,这三折羊毛卷便像麻花一样,自然而然地紧紧绞成了一大块圆疙瘩。最后抽去棍子,把两个端头紧紧塞进麻花间的缝隙里。这下,原本松散的一大堆羊毛就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了,分散不得。其实这样已经很结实了,但两人又把另外两张羊毛用同样方法连起来绞,绞成一股较短较细的“绳子”。再用这根“绳子”把已经团得很紧的羊毛块拦腰一捆,更是上了双保险。哎,我们这里牧人打包起行李来,是出了名的结实、省地儿,毫不含糊。
这样,我原本以为非得装满半卡车的羊毛,立刻变成结结实实的六大坨(我家两坨,爷爷家四坨)。只需三峰骆驼就可以驮走了,哪里还需要装袋子!
〔9〕干这些活的时候,一直下着大雨。大家冒着雨干了很久很久。而这堆羊毛之前堆了两天都没人管,也不知头两天天晴的时候大家都干什么去了……再一想,莫非淋了雨的羊毛摩擦力更大,打卷儿的时候更不容易散开?
孩子们也不怕淋雨,围在旁边兴奋地观摩,一个个极想插把手。对他们来说,劳动无比神奇,劳动中的大人们也极富魅力。他们已经把看到的一切烂熟于心,等长大了,一上手,定会做得自然而然,熟门熟路。
并不是所有的羊毛都卖掉,家人会把最好的羊毛留下一部分,送到耶克阿恰经营弹花机的小店里弹开了,再带回家制作各种羊毛制品。
〔10〕弹花机非常厉害,能迅速把板结成块的羊毛片弹打得蓬松又均匀。在没有弹花机的年代里,主妇们只能用双手慢慢撕松羊毛,再以柔软的柳枝千万遍地抽打,工作量相当大。而汉族人则用弹花弓子弹。那玩意儿虽然比柳条省力多了,但未免太长太大,不便携带,不适用于游牧生活。
弹松的羊毛可以用来捻线、搓绳子、擀毡。捻出的线原色的用来缝制花毡,染出各种颜色的则用来绣花毡。另外,染色的羊毛线还能编缠彩色的芨芨草席。这种草席用来围在毡房内部的房架子四周,既装饰又挡风。而羊毛绳合成股后,有粗有细,系骆驼、捆包裹,各有用途。羊毛擀制的毡片的用途则更广了,从毡房本身,到坐卧的花毡,到头上的帽子、脚下的鞋垫、保暖的毡袜、毡筒……充斥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11〕当然,城里的市场里也销售各种机制的毡袜、毡筒,便宜又好看,牧人很少再自制了。但花毡的制作却是机器难以替代的。花毡是重要的生活用品,也是主妇们表现才情的最重要的创作阵地。
进入冬库尔牧场后,妈妈就开始不停地捻线。她顺着一个方向,把弹松的骆驼绒毛或细羊毛反复撕扯。再把扯顺的毛摊成一长溜薄片,再裹上一绺撕顺的粗羊毛,卷为一束,蘸点水,揉成一个个小团。这样的小团便可用来捻线了。一根绳子里,粗毛掺得多,就结实;绒毛多,就柔软。
〔12〕一个小毛团能捻一米多长的绳线,一天就能捻出一大把线。才开始我还担心捻这么多线怎么用得完。后来才知根本不够用,还得另外买毛线代替。
扎克拜妈妈整天纺锤不离身。赶牛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往草地上一坐,掏出纺锤就搓转起来。哪怕傍晚赶羊入圈前只有两分钟闲暇,她也一边望着已经爬到半山腰的羊群,一边跪坐在羊圈边争分夺秒地捻啊捻。莎里帕罕妈妈也同样如此。过来串个门,也会边喝茶边捻。两个妈妈一起走在山路上时,有时为某个惊人的话题停下脚步,就地坐下讨论许久。讨论的同时,不忘掏出各自的纺锤。
〔13〕莎里帕罕妈妈的纺锤和扎克拜妈妈的不太一样,捻杆下的锤状物不是铅饼,而是一块坚硬的、半球形的木头,还刷了红漆,刻着花纹。再仔细一看,居然是一个小毡房的造型!上面不仅有门有天窗,还刻出了缠绕在毡房外的宽花带子“特列蔑包”。虽然雕刻水平相当业余,但想法蛮别致。
纺出的线,不久后染上颜色,细密地缝进生活的各个角落,暗暗地紧绷着。一根一根的纤维,耐心地承受着生活的种种磨损,缓慢而马不停蹄地涣散。而新的线也马不停蹄地在妈妈手中搓转成形,一根一根有条不紊地进入生活之中。
〔14〕比起捻线,搓绳子的活计就辛苦多了。全凭妈妈一双手掌,先搓出细的,再合股成粗一些的,再合成更粗的……整个六月,妈妈的手掌边缘一直布满伤口,手指也破破烂烂的。
而最粗的绳子,跟小鸡蛋一样粗。合股这样的绳子双手根本使不上劲,就得靠大家的力量了。在搬家头一天拆毡房时,大家把三股二十多米长的中粗羊毛绳绷在房架子上,接头处呈“丁”字形巧妙地穿插固定。然后男孩子们用木棍各绞住一股绳子顺着同一方向拧,狠狠地给绳子上劲。三根绳子都拧紧后,斯马胡力在房架另一头拽住“丁”字形的绳头,从反方向一点一点抽取。绳子便自然地拧成了形,又紧又粗又匀,一点儿也不比机器打出来的差。
〔15〕等这根粗壮的绳子合股到最后,妈妈把三截越来越细的绳头合股,再擗为四股,交叉着搓为两股,两股再合一股。最后的梢尖上裹一块布,用细细的针脚固定。这样,绳头又漂亮又结实。要我的话,处理这种事,只会在末梢打个结儿了事。
“特列蔑包”是另一种羊毛制品,就是手织的长带子。它们作为更美观的绳子,用来缠绕在毡房内外,固定壁毯、毡盖之类的物品。有的也会作为装饰花边缝在花毡上。制作原理与纺布一样,也分经纬线,也会用到梭子。这种带子就是用染了颜色的羊毛线编织的。当然,现在很多女人喜欢以现成的腈纶毛线代替羊毛线,编出来的带子色彩更丰富,且更均匀、柔软。
〔16〕这种带子,窄的不过一指宽,宽的能达一尺。我见过的最宽的带子是冬库尔的阿依努儿编织的,足有一尺半宽,配了十几种颜色!图案繁复至极。她用的是专门编“特列蔑包”的木架,支在家门口的草地上,各色毛线散落一地,梭子别在带子中央,分开了已经编好的部分和仅仅只是绷着经线的部分。看在眼里,感觉奇妙异常。尤其这架子是支在一处幽静美丽的山谷里的,似乎眼下这根华美的带子是阿依努儿直接从四面的天然风景中一滴一滴榨取所需色彩,紧紧拧成一束,像拧湿衣服那样拧啊拧啊拧出来的。
〔17〕在吾塞,去西南面的邻居阿舍勒巴依家做客时,看到他家的邻居女孩也正在编织“特列蔑包”,却简陋多了,只有一指半宽,并且只有两种图案重复出现。也没绷架子,只是将带子一头系在房架子上,另一头用大腿压住绷直了,直接插上梭子编。可那情景看在眼里,仍然绚丽跳跃,无限丰富。
除了捻线和搓绳子,绝大部分弹好的羊毛是用来擀毡的。把宽大毡片裁剪成合适的碎片,煮出颜色。上面用肥皂片画出花样子,绣上种种优美的花朵、羊角等形象。把这些碎块连缀成一整块后,再衬以厚实的一整块原色毡片,沿着图案边缘穿透两层毡片缝上花边。最后沿着四周绲边。
〔18〕说起来,绣花毡就这么简单,但远不止如此。一块花毡的生长和一只羊羔的生长一样缓慢又踏实。有一个词是“千针万线”,一针扎下去,再一针引出来——就这么简单的动作,像走路,慢慢走遍了天涯海角。
还在冬天,还在荒野中的地窝子里时,扎克拜妈妈忙碌地赶羊、挤奶、烤馕、做饭。一天,在等待茶水烧开的时间里,她在一块三角形的紫色毡片上绣出了黄色花瓣的第一针。一个冬天过去了,这块毡片时绣时停。一直被扔在被褥堆上,时不时用来盖住一盆刚炼好的羊油或正在发酵的面团。于是,等上面的图案最终完成的时候,也稍有旧相了。等这样的毡片攒了六七块,冬天就过去了。
〔19〕到了春牧场上,妈妈把这些彩色毡片连缀成了一整块。尽管远未成形,已经开始投入使用。晚上妈妈把它垫在被褥下睡觉,白天也坐在上面干活。于是使之越来越平展、妥帖。
到了夏牧场,妈妈把这条单层的花毡两端补缀两溜长长的绿色毡条,并绣上枝蔓状弯弯曲曲的图案。再以长针脚将醒目的橘色线在每一个旧针脚间系两个结,使之更结实,也更丰富完整。这方面妈妈很厉害,她绣周边的装饰花纹时,直接在毡片空白处下针,不用描花样子。
〔20〕在吾塞牧场,花毡终于进行到最后阶段。这时它已经变得很宽大了,并衬上了底毡,越来越沉重。小木屋里不好施展手脚,每次妈妈都把它拖到屋外草地上,坐在上面绣。像是坐在花园里绣,花朵直接从手指上绽放。她在颜色各异的毡片接合处衬上“人”字形的装饰花边,遮挡接缝处的针脚。同时用这种花边将两指厚的两层毡子密密实实地缝合到一起。然后又裁了几条狭长的毡片煮成艳丽的孔雀绿色,一串一串搭在门外栏杆上。晾干后,用以裹住花毡的四边缝合。但这仍不是最后一道工序,还要在绲边处再缝一道花边,继续装饰,继续加固。
〔21〕缝完最后一针,妈妈侧身一倒,直接躺在上面睡了。花毡结束时是崭新的,又呈舒适的旧态。
每进入一个牧人的毡房,我都会细细地观摩各种花毡和壁挂。总是对那些热烈又纯洁的冲撞配色心仪不已。很大程度上,牧人的家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缝出来的。如果没有花毡子,没有墙上挂的壁挂和装饰性(其实也有宗教用途)的白围巾,没有漂亮的茶叶袋子和盐袋子,没有马鞍上的绣花坐垫和垂挂两侧的饰带,没有搬家时套在檩杆两头的花套子,没有包裹木箱的绣花袋……那么这个家的光景看着该多惨淡!
〔22〕顺便说一句,除了羊毛制品,家里的一切皮具也都出自斯马胡力的手工。马镫上的带子、马绊子、马笼头、马鞭……这些都不用买。还有那些细皮条编结的牛皮绳,双“人”字纹的、扁的、圆的、“丁”字形的……结实又精致,交叉处处理得天衣无缝。
斯马胡力做这些事时非常细心。尤其每到搬家前的日子,总是会把每个人的马具都搬到屋前空地上逐一检查,细细加固,以防搬迁途中遇到意外。同时还要制作新的皮绳。皮制品与羊毛制品一样也是持续消耗品。
〔23〕一个晴朗闲暇的下午,这家伙抱出一大堆裁好的牛皮带子堆在门口的草地上,摆开架势要大干一场。只见他用锥子在一条细长的牛皮带子一端打出眼,把另一条带子的一端剪成细皮条穿进孔眼里,打一个别致美观的扣结。再用榔头在打结儿处敲了又敲,弄得平平展展、结结实实。再以同样的手法连接下一根……如此这般地干了半天,将那堆牛皮带子全部连接到了一起。
他笑嘻嘻地对我说,这些以后可以用来当马缰绳,或牵骆驼。然后坐直身子,拍拍脖子,准备收工。他扯着这根长长的绳子一圈一圈地拽,拽了半天也找不着头。拽到最后,我们都乐了!原来这个笨蛋一看到绳端就扎孔、打结儿、扎孔、打结儿……最后连成了一个大绳圈。我们笑了半天。亏他处理得那么结实!想拆开都不容易。
〔24〕耶克阿恰是杰勒苏山谷最南端的一处空地,两条河以及沿河的两条路都在那里交汇。由于是山野里的一处交通要道,森林管护站在那里设立了关卡。渐渐由此聚集了很多生意人,非常热闹,号称“小香港”。当然,让香港人见笑了,不过是一处扎有三十多顶毡房和帐篷的山野角落而已。
从吾塞去耶克阿恰,得骑三个多钟头的马。大家都很向往那里,包括班班在内。每次家里有人去耶克阿恰它都要跟着跑一趟,从不嫌远。斯马胡力说,耶克阿恰有班班的女朋友。
〔25〕去耶克阿恰,无非为了采办一些日用品,或去卖羊毛。但日用品一次性就能采办齐全,羊毛也一次就卖光了。所以,去耶克阿恰的机会并不多。
但大家很能创造机会。斯马胡力不知从哪儿听说他的一个中学同学从外地回来了,会在耶克阿恰停留几天,于是硬缠着哈德别克同去(奇怪,又不是女生上厕所,非得搭个伴)。卡西鞋子坏了,脾气暴躁,一定要去耶克阿恰买新的。而扎克拜妈妈一接到莎勒玛罕捎来的口信,便立刻准备启程,也不管莎勒玛罕究竟有什么事。
〔26〕可家务活那么多,哪能架得住大家三天两头地撂挑子,因此扎克拜妈妈去耶克阿恰的头一天晚上顶多只能睡两个小时。忙一整个通宵,差不多做完了第二天所有的活——把两大桶牛奶全部脱脂,又煮沸了,再沥干,制成干酪素。大家也一起上阵,就着烛火(呜呼,那时太阳能灯坏了)干到凌晨一点才睡下。而妈妈仍独自继续忙碌着。半夜睡醒,看到妈妈还在烛光中努力地捶酸奶、揉黄油。酸奶和黄油是准备捎给莎勒玛罕的礼物。
妈妈不在的这一天真是漫长又寂寞。再加上没什么活儿做了(妈妈全都做完了嘛),大家便拼命睡觉。我睡了两个小时,卡西睡了三个小时,斯马胡力最牛,足足睡了四个小时。可是,尽管这么享受,大家还是更羡慕去了耶克阿恰的妈妈。
〔27〕为了迎接妈妈回来,这天下午卡西把家门口五十米范围内的空地打扫了一通,好让妈妈回家时感受到自己等待的心意。
但山坡上四处都是深深草丛,所谓垃圾,无非是些碎木片和石块,有什么可打扫的呢?再说,不是过几天就要搬家了吗?还扫什么……再一想,这可真是标准的定居者思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搬家意味着“舍弃”;对牧人们来说,搬家是为了“保护”——为了让大地得到休息和恢复,才不停地辗转迁徙。
是啊,我们来到这个林海孤岛还不到一个月,附近的草地明显变薄,发黄了。
〔28〕总之这一天,卡西不但将房间和整个山坡大扫除了一番,还抽去所有花毡,搭到外面木围栏上,以木棒狠狠拍打了一番,把尘土拍得干干净净。
拍完花毡,这姑娘把木棒一扔,往草地上一头扑倒,身子拉得直直的,舒舒服服地躺着。好一会儿,突然开口:“李娟,耶克阿恰好得很,有温泉,有商店,我们以后也要去!”
傍晚,妈妈在挤牛奶之前及时赶回,然而一回来就大发牢骚。原来莎勒玛罕受有事出门的努尔兰夫妇所托,请妈妈去帮忙照料家中婴儿。唉,本来妈妈还打算在耶克阿恰好好串串门呢,结果小孩哭闹了一整天,只好费尽心思哄了一整天。什么也没干成。
〔29〕妈妈一边挤牛奶,一边生气地向我们模仿孩子哭的样子,挤着眼睛发出“哈啊哈啊”的声音。
努尔兰家虽说也住在耶克阿恰,但离热闹的商业中心还有两三公里远呢。总之妈妈失算了。别说玩,连颗土豆也没能买回来。亏她还特意打扮了一番,亏她通宵没命地干活。
不过此行还是有收获的,努尔兰的媳妇玛依努儿送了妈妈一大块白白的肥肉。同去的班班怕是也受益不少,回来时肚子滚圆。
妈妈结束耶克阿恰之行后,卡西也开始蠢蠢欲动。两天时间内,她一共申报了五个理由。全都被斯马胡力一一驳回。但又不好恼怒,因为确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30〕最后经过一番协商,两人决定各去一次。妈妈无可奈何。
斯马胡力拉着哈德别克先去。两人回来后的当天晚上,卡西就开始打点行装,第二天一早就立刻上路了。当然,上路前一定要借走我的书包背着,然后又借走我的小梳子。她一边把梳子往口袋里揣,一边说“谢谢”。被放进口袋之前,我冲那把可怜的梳子深深看了一眼,心想:恐怕这是最后一面了……
另外,卡西还狠狠抠了一大坨粉底霜往脸上抹,把脸弄得跟蒙了层塑料壳似的。
我撇嘴:“不好的!”蔑视之。
她也撇嘴:“贵的!十块钱的!”更为蔑视。
〔31〕总之,小姑娘脸蒙塑料,身穿新衣,闪闪发光地上马出发了。同去的还有杰约得别克及精神抖擞的班班。班班这家伙连着几天来回奔忙,每天几十公里,也不嫌折腾。
卡西不在的日子突然变得特别忙。以前斯马胡力赶羊前起码得喝四碗茶,今天只喝了两碗就匆忙出门。妈妈代替卡西出去赶小羊和牛。我呢,孤零零地摇了两个小时分离机,再烧茶,收拾房间,挑水……好半天才休息下来,时间已晃向正午,却没一个人回家喝茶。只好自己铺开餐布,自斟自饮。
〔32〕有一只小牛在东面松林里吼了很久,又刨土又撞树,无比愤怒。我忍不住过去看。刚走到附近,松林深处又跑出一头大黑牛。它跌跌撞撞奔向小牛,边跑边叫。小牛立刻做出回应,欢呼着冲向黑牛……这两头牛非常陌生,显然不是我家的,也不是爷爷家的。但我本能地追上前,想分开它们。却不知怎么赶,也不知该赶往何处。小牛在黑牛肚皮下咬着奶头,一边躲我,一边急促吮吸……好吧,今天傍晚有一家人得少挤半桶奶了。
要是卡西在就好了,以她的神勇,这点儿小事不在话下。得逞的牛母子很快消失在密林深处,我只好慢慢往回走。
〔33〕一大团明亮耀眼的白云稳稳当当地经过南面山巅。别看此刻天气大好,灿烂的阳光会令地面的水汽很快蒸腾起来,等满满当当糊住天空后,又得下一场雨。可怜的卡西,可别在回家的路上赶上大雨。
回到安静的家中,空空落落,困意陡生,便披了件外套躺倒。刚睡着就冻醒了,咳个不停,双脚冰凉。外面果然开始下雨了。天阴沉沉的,花毡潮乎乎的。还是没人回来。
正发着呆,突然斯马胡力低头闯了进来,身上扛着一大卷羊毛,头发和衣服被雨淋湿透了。他把羊毛往干燥的空地上一扔(房间里好几个地方都在漏雨),又转身冲进雨幕。我赶紧跟出去说:“先喝茶吧?雨停了再干活。”他似乎没听到,径直走进西面低处的林子里。
〔34〕突然扎克拜妈妈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们先喝吧。”回头一看,妈妈不知何时回来了,也浑身湿湿的,身子一侧全是泥巴。我连忙跑进小木屋摆桌子,她一瘸一瘸地跟在后面。茶摆好后,我又赶紧生起炉子。妈妈一边喝茶,一边烤火,然后告诉我,赶小牛时摔了一跤。却没提摔坏了哪里,只是惋惜地说:“鞋子摔破了!”我一看,果然,她右脚的鞋帮子从鞋底子上撕开了一大截,补都没法补。这一跤摔得真厉害!
喝到第三碗茶时,妈妈突然问我上次换下来的红鞋子还要不要了。上次进城时我买了一双新鞋,便把之前那双鞋尖处已经顶破了两个洞的红色旧鞋换了下来。当时想扔掉,但妈妈阻止了,搬家时便一直带着。我连忙把它找出给妈妈。但鞋太小了,妈妈只能像穿拖鞋一样趿着走。
〔35〕这时我又想起自己还有一双大靴子,是上次进城时特意找朋友讨要的一双旧鞋,只为鞋子大了可以多穿几双袜子,多垫两双鞋垫,更保暖。于是赶紧翻出来。这双鞋妈妈倒能穿进去,但穿上后就拉不上侧边拉链了。但她还是很高兴。这么旧的鞋子送人,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便请她把鞋子脱下来,摸出斯马胡力珍藏的鞋油细心擦了一遍,然后再让她穿。她踩着靴子在木屋里转了两转,非常满意。郑重地说:“谢谢!”我索性又把一双还很新的厚羊毛袜也一并送给她。她把袜子和那双旧红鞋放进一只袋子里,小心收藏起来,踩着新鞋高兴地出门干活去了。
〔36〕正准备收餐布撤桌子,斯马胡力也拎着羊毛剪回来了。我赶紧沏茶。他掰碎了满满一碗干馕泡在茶水里,用勺子舀着大口大口吃了起来。看来确实饿坏了,连吃两大碗后才开始慢条斯理地喝茶。并取来磨刀石,坐在床沿上磨起了羊毛剪。磨一会儿,就转身喝几口茶。看来喝过茶后不能休息,还得继续剪羊毛。
外面雨已经停了。
有一只牛慢悠悠靠近我们的院子,在栏杆外站了一会儿,四顾无人,开始在木桩上蹭痒痒。蹭啊蹭啊,蹭完脖子又转过身蹭屁股。要是卡西看到这情景,肯定会立刻冲过去赶跑。
〔37〕可我看它蹭得那么舒服,实在不忍心赶。结果没一会儿这家伙就把桩子给蹭翻了,栏杆倒了一片。我还没赶呢,它自己先吓跑了。我只好过去把桩子扶正,用大斧头敲了几下,使之重新坚固地立在地面上。再把栏杆扶起,修补了一番。
卡西不在的这一天,林海孤岛格外寂静,我也格外悠闲。在山顶转了几圈,想了又想,回家拎了扫把开始打扫院子,虽然实在没什么可扫的。
又回家把所有的锅子擦了一遍。水桶都是满的,柴火还有很多。坐在木屋床沿上,左想右想,向后一倒,还是继续睡觉吧……虽然困意很足,但睡得并不实沉。
〔38〕花毡硬邦邦的,侧睡时硌得肩膀疼,便翻个身换另一侧睡。没一会儿,另一侧肩膀又疼起来,同时浑身发冷。要是晚上就好了,晚上就可以铺开被褥踏踏实实地睡。迷迷糊糊中,觉得木榻上又多了一个人。睁眼一看,斯马胡力这家伙不知啥时候回来了,裹着大衣睡在旁边。门外天色很暗,不知何时又开始下雨了。浑身无力,闭上眼继续陷入昏沉的睡意之中。
彻底醒过来已是三点半了,雨也停了。斯马胡力还在睡。出去看时,四面茫茫雾气。羊群不知为何漫游到了驻地附近,围着山顶不停咩叫。
〔39〕妈妈在毡房那边进进出出,见我起来了,便嘱咐我煮上午刚分离出的稀奶油,然后消失在林子里。
我吹燃炉火,把盛稀奶油的小铝锅放到炉沿边,并把炉火控制得很小。
透过木屋小门,远远看到吾纳孜艾和加依娜从林子里走出来。吾纳孜艾挑着水,加依娜跑前跑后,边唱边跳。两人一起进了爷爷的小木屋。很快吾纳孜艾又出来了,抱着一大卷花毡,然后在草地上用力抖动毡子,扬去上面的尘土。加依娜依旧绕着他跑来跑去。
〔40〕雨后天晴,气温升高了许多。被雨水浸泡后的植物在西斜的阳光中像刷了一遍新漆似的崭新。房顶上的植物又浓又深,开满白花和黄花。爷爷家的屋顶则开着蓝花,还高高地挑出几朵窈窕的黄色虞美人。
我们这边山头晴朗了,可南面群山雾蒙蒙的,几乎快要消失在水汽弥漫之中。
然而光顾着在门口东张西望,竟忘了炉子上的稀奶油,一不留神煮沸了!一听到奶油漫到炉板上的嗞啦声,赶紧冲进屋里端锅。但端下来也没有用,沸腾的奶油仍源源不断地涌出,流得一地都是。连忙用汤勺搅——搅也没用!还是一个劲儿地流啊流啊。这才想起,稀奶油过于黏稠,一旦烧开,比牛奶更难止沸。而止沸的唯一办法是加冷水降温,于是又赶紧加冷水。
〔41〕奶油在炉板上烧煳的味道极其难闻,一直到妈妈回家了还没有散去。对此妈妈很生气,念叨了半天。我早就听说哈萨克牧人忌讳牛奶洒地,更别提牛奶的精华海依巴克了。唉,真是可惜,浪费了足足大半碗呢……要是卡西在就好了。她虽然粗心大意,但应付这种事还是很从容的。
妈妈是五点回来的,远远地就开始大叫:“李娟!李娟!”我一听就知道又有牛来房子附近捣乱了,冲出去就打。果然还是刚才那头肇事牛。岂有此理!到处都是树,哪里不能蹭痒痒?
〔42〕和妈妈一起回来的还有几头小牛。马上开始挤奶了,可卡西还是不见踪影。妈妈也念叨了起来。系好小牛后,她站到山顶最高处的爬山松边,手遮在眼睛上向北面的山谷看了好一会儿。这时,又下起雨来。
平时这个时候,卡西也总是站在那里视察领地,还像领袖一样叉着腰。当她拍一拍手,呼唤几声,远处的羊群就慢慢向坡顶漫延,逐一向她靠拢。那时,她就像是夕阳中的女王。
虽然只是半天没见,突然那么思念。不但思念她,还思念她有可能会带回家的意外—— 一个外面的消息,或者一些糖果。
〔43〕奶牛统统回到了牛宝宝身边,妈妈和莎拉古丽冒雨挤奶。今天牛回来得好早。如果没有意外,今晚可以早早结束一天的劳动,早早睡觉了。可偏偏今天羊回来得好晚,天色很暗了才全部入栏。少了卡西,顿感做什么事都不顺利。
这一天,大家很晚才结束全部的工作。吃晚饭的时候,母子俩议论着,认为今天卡西可能会在莎勒玛罕家留宿。正说着,突然听到狗叫声,妈妈和斯马胡力一同放下碗,起身向外走。卡西回来了!
马儿驮回来了一袋面粉和一只鼓鼓的编织袋。斯马胡力把重物卸下来扛回家,卡西留在后面卸鞍子和嚼子,并给马系上马绊子。马背被面粉染得白白的。
〔44〕等她进了门一看,穿得可真少!我赶紧给她沏茶。连声问她冷不冷,是不是被雨淋惨了。谁知她说那边根本就没下雨。
喝了一碗茶后,姑娘开始献宝。从编织袋里依次取出一大瓶葵花籽油、一瓶分离干酪素的药水和两节二号电池。最后她在袋里抱住一个圆东西,慢慢掏出来……一个哈密瓜!多么隆重的食物啊!是莎勒玛罕给的!
妈妈立刻把瓜切开。一半留到明天吃,另一半切成月牙,每人分了两片。嗯,太甜太好吃了!我都啃到瓜皮了还忍不住啃了很久很久。但卡西却只挑了最薄的一片吃,又把切瓜时掉落的一些碎屑捡着吃了。不由令人诧异。我问怎么了,她哀愁地冲我伸出舌头。一看,舌尖上起了一小片水泡。她苦着脸说:“耶克阿恰的哈密瓜……”原来在那边已经吃得上火了。
〔45〕斯马胡力一整天没怎么说话,此时突然显得非常愉快。他一边啃瓜皮,一边用汉语对我说:“这个嘛,阿克哈拉的房子嘛,多得很!”
开始没听明白,后来才搞清,家里在定居点那边有几十亩地,除了种饲草,也种有哈密瓜。哇,真厉害,看起来好高端的经济作物啊。要知道在阿克哈拉,大家一般只种麦子、苜蓿或玉米。我又问:“种了多少?”
答:“半亩。”
原来不是种来卖的。又问:“收了多少?”
答:“四个。”果然不适合种如此高端的作物……
〔46〕这顿晚餐结束得慢慢吞吞。我收拾碗盘,妈妈把炉火拨得旺旺的,好让卡西烤火,并伸出脚展示今天刚得到的靴子。卡西一看,嚷嚷着也要穿,却怎么也穿不进去。于是这双靴子仍然是妈妈的。
母子三人围着火炉谈论从耶克阿恰得来的消息,包括羊毛的价格变化和莎勒玛罕家的情形。当谈到一件与马吾列有关的事时,妈妈表示震惊,不停地说:“不,不!……”我听着大约是说有一个重大的活动会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举办。因为实在太远了,大家都去不了。为这事,大家感慨万千,又沉默许久。
〔47〕直到睡觉时,卡西这家伙才觍着脸慢吞吞地用汉语告诉我:“李娟,那个,梳子的,那个,没有了的,那个,马的不好!”——还怪马!
今天中午收拾厨房时,我特意为远行的班班留了两块馕,用剩奶茶泡在一个破盆里。为了不让牛羊吃,我把破盆藏进了柴火堆,睡觉前才悄悄取出来,轻轻地唤班班过来吃。看它吃得那么高兴,一副着实饿坏了的样子,不由得问道:“耶克阿恰真有那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