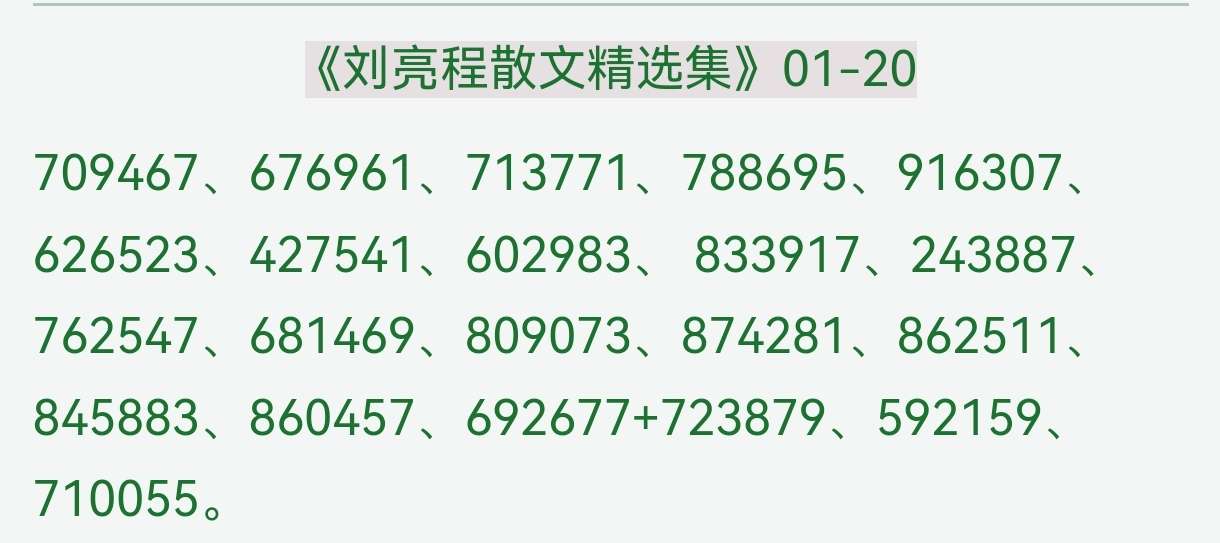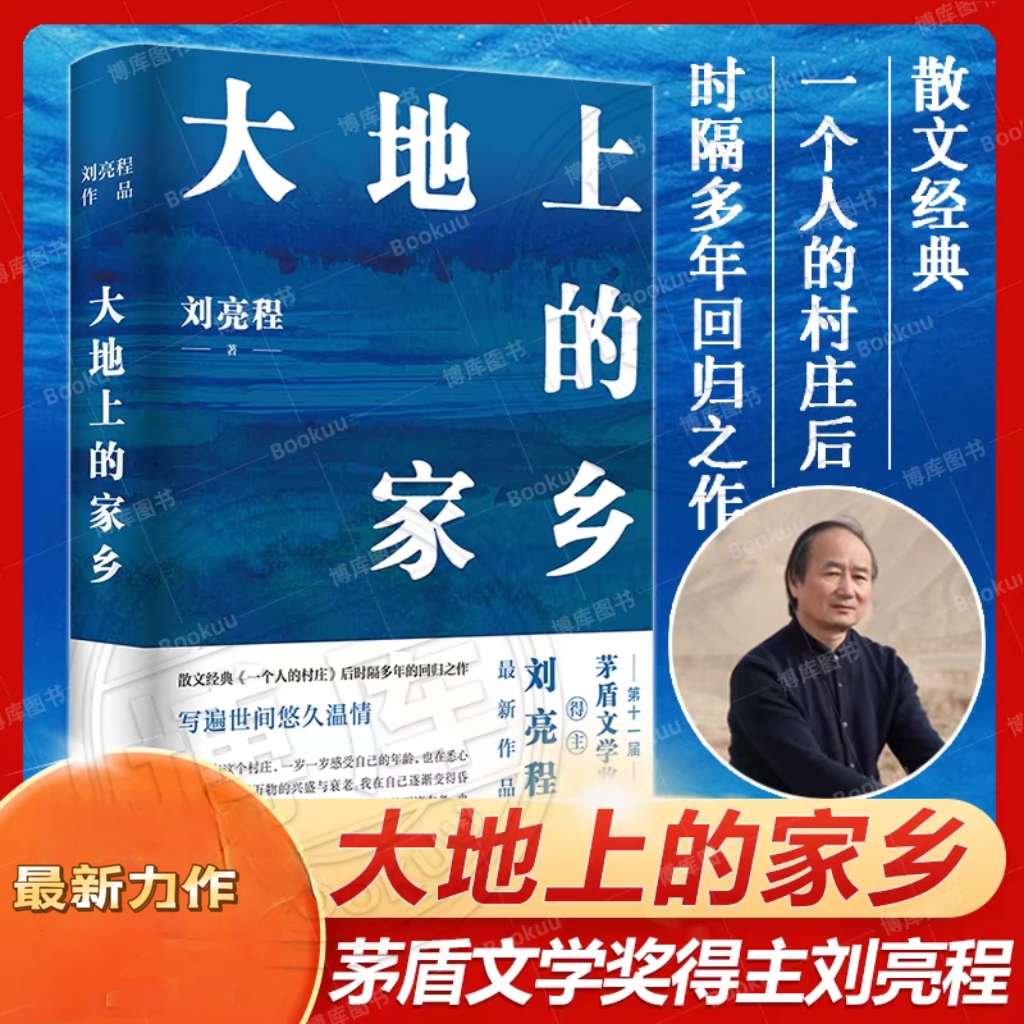
【开篇导读】
〔1〕《大地上的家乡》是刘亮程创作的散文集,首次出版于2024年3月。
《大地上的家乡》共分三辑。第一辑《菜籽沟早晨》写的是作者在菜籽沟村的生活日常,村里的人与事,天上的飞禽和地上的动物,以及缓慢流动的时间和躲不过去的衰老;第二辑《大地上的家乡》主要是作者谈创作的体会和感想,譬如谈及第一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的写作契机;第三辑《长成一棵大槐树》则是作者远游的记录。他去甘肃崇信看大槐树,到南京研究虫子,在金佛山活成一棵树、一株中草药、一座山。看似闲游,实则把自己谦卑地置于自然,感受人间大地真实的美与疼痛。
〔2〕如果说《一个人的村庄》是刘亮程离开故乡在城市里对家乡的一场深情回望,而《大地上的家乡》则是他把心中的理想家园重新安置在大地上的一部完整作品。从黄沙梁到菜籽沟村,作者在精神上从未离开过自己熟悉的乡村文明。鸡鸣狗吠中醒来,耕读写作中养老,依循自然的木垒生活是一种“慢生活”,《大地上的家乡》呈现出的也是一种“慢哲学”,即“在慢事物中慢慢煎熬、慢慢等待,熬出来一种情怀、一种味道,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道德观念,这就是乡村文化、乡村哲学。”
2024年4月,《大地上的家乡》入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4年第一季度影响力图书(文学类)。
〔3〕(作者说)我在这个村庄,一岁一岁感受自己的年龄,也在悉心感受天地间万物的兴盛与衰老。我在自己逐渐变得昏花的眼睛中,看到身边树叶在老,屋檐的雨滴在老,虫子在老,天上的云朵在老,刮过山谷的风声也显出苍老,这是与万物终老一处的大地上的家乡。——刘亮程
【第一辑·菜籽沟早晨】
菜籽沟早晨
〔4〕我要在一山沟的鸡鸣声里,再睡一觉。布谷鸟、雀子、邻家往小河对岸的大声喊叫,都吵不醒。满山坡“喳喳”疯长的红豆草、野油菜、麦苗和葵花吵不醒。山梁呼噜噜长个子。在我傍着她的均匀鼾声里,有一匹马和小半群绵羊,打山边走过,行到半坡拐弯处,一只羊突然回头,对着我半开的窗户,咩咩咩叫,仿佛叫它前年走失的羔子。
我就在那时睁开眼睛,看见我被一只羊叫醒的另一世里,我跟着它翻过了山梁。
我认识乌鸦中的老者
〔5〕我认识乌鸦中的老者。它们一大伙在杨树梢“哑哑”叫时,我听出它苍哑的嗓音,像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在喊叫。我不知道它喊谁。我听见了,它就是在喊我。我朝杨树下走几步,想从一树黑乌鸦中认出老了的那只。可是,乌鸦再老羽毛也是乌黑的,不会像人,活到头发花白。
我住的菜籽沟村最多是白发老人,那些沿路零散地排开的老宅子里,有的住一个老人,有的住两个。住两个的过一阵剩下一个。村委会上班的也是老人,村长支书都老了,天天到办公室开会,讨论菜籽沟未来发展的事。
〔6〕乌鸦在讨论什么呢。它们在树上开会,听上去每只都在“哑哑”叫,只有我一个人在树下听。
我听了半辈子乌鸦叫,仍然不知道它们在叫什么。
但我终于听出一只老乌鸦的叫声。在一树黑压压的叫喊中,有一个粗哑的喊声落下来,像在喊地上的人。
我一冲动,对着树上扯开嗓子“哑哑”大叫几声。
它们全惊飞起来。
它们飞过菜地时,我认出那只老乌鸦了,飞在最后面,迟缓地扇动翅膀,脖子伸得长长,像人老了一样,身体走不快了,头却慢不下来,使劲往前伸。它明显跟不上疾飞的乌鸦群。它们飞过河沟和马路,飞到那片长满藏红花的山坡后,不见了。
〔7〕那只老乌鸦留下来,落在小河边的榆树上,头朝这边看我,张嘴“哑”叫了一声。
我学它“哑、哑”叫了两声。
它一定听出我的叫声比它的还要苍老。
接着它飞起来,从我头顶缓缓掠过时,头偏了一下,一只眼睛朝下看。它的眼睛也许跟我的一样老花了,辨不出地上是一个人还是一只乌鸦。也许在它眼里我就是一只老乌鸦,弓着腰,背着膀子,匍匐在地上。
它又“哑”地叫了一声。
我知道它是对着我叫的。我没好意思再学它叫。多少年来我跟着乌鸦学它们叫,早已学得太像一只乌鸦了。我担心把它从天上叫下来。万一它真的飞下来,落我身旁,要跟着我走,我会把它领哪去呢。
鸽子
〔8〕一只灰白鸽子,站在屋檐上看我们在院子里做饭,大案板上摆满青菜、肉和醒好准备下锅的拉面,它大概看得嘴馋,“咕咕”叫。我抓一把包谷撒上去,它跳开几步,眼睛依然盯着我们锅里的饭。
我们一家人坐在锅头边的案子上吃饭时,它落下来,小心地朝饭桌旁走来,走两步,偏着头望一阵,又走几步,仿佛它认识我们中的谁,前来打招呼。又仿佛它是我们丢失很久的一个孩子,回家来吃饭了,我们忘了给他摆筷子,忘了给他留位子,忘了做他那份饭。
突然地,我们全停住筷子,看着它一步一步走过来,快到跟前时它停下来,依然偏着头望,像一个一个认它久别的家人。
我妈说,给它撒点米饭,鸽子爱吃米。
方圆起身拿米饭时它飞走了。
它朝屋后的麦田飞去时,连头都没回一下。仿佛它真的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
我做梦的气味被一只狗闻见
〔9〕我妈去英格堡赶集,见有铃铛卖,老式黄铜的,顺手摇一下,有她早年听熟的声音,就买两个,在黄狗太阳和黑狗月亮脖子上各拴一个。月亮的没几天丢了,它不喜欢这个乱响的东西,自己甩掉了。我妈拾回来再给它戴上,第二天,它又脱掉。它当我妈的面,把一个前爪蹬住脖圈,头往后缩,脖圈就掉了。然后,它衔起带铃铛的脖圈,一路响着跑到屋后面,在我妈看不到听不见的地方转了好一阵,无声地跑回来。它把那个讨厌的铃铛藏掉了。
太阳的铃铛一直戴着。它喜欢那个声音。它个头比月亮小,但它觉得自己比月亮多一个声音,它经常晃着头在月亮面前摆弄自己的响声。
〔10〕它成了一条“叮叮当当”响个不停的狗,跑到哪儿我们都能听见。
夜晚它的叮当声成了院子里最清晰的声音。我们从不知道晚上院子发生了什么,半夜被狗叫醒,侧耳朵听,是月亮在南边大叫,或许进来人了,或许是一只野猫或獾进了院子。有时我开灯照一下,若是外人进入,看见窗户亮,也就跑了,我并不出去看究竟。更多时候我呼呼大睡,不去理会狗在叫什么。一夜,狗吠声传到梦里,我在远处听见狗叫,匆忙往回赶,家里进来生人了,门开着,窗户开着,我惊慌地站在门外不敢进去。
〔11〕月亮大叫的时候,听见太阳的叮当声跟在后面。太阳很少叫,它知道自己的叫声太小,吓不住入侵者,它让响亮的铃铛声跟在月亮后面助威。它的铃铛声摇遍院子的每个角落。月亮只有自己的汪汪声。有时它在北边杏园叫,那里有一只大白猫,夜夜惦记我们伙房里的肉,有一个夜晚,后窗户没关,大白猫进来,把案板上一块骨头偷走了。月亮闻着那块骨头的味道追咬到后院墙边,白猫越墙跑了。月亮在院墙边狂叫。太阳的铃铛声也追到院墙边。
这个四处漏风的院子交给两条一岁多的小狗看守。月亮看上去个头大,很凶猛,太阳只是条小宠物犬,秋天抱来时浑身精光,担心过不了冬。果然天稍一凉就往屋子里钻。每次我都毫不客气赶它出去,它得习惯这里日渐寒冷的天气,让自己成为能在外面过冬的动物。
〔12〕菜籽沟已经是冰雪世界了,它的毛还没有完全长出来。天亮前那阵子外面最冷,听见它在门口叫,拿头顶门,门缝露出的一丝温暖会被它的身体接住。金子一起来就开门放它进房子,说让它暖暖身体。我坚决反对,我们不能让它依赖屋里的暖和,它要在漫长冬天的寒冷中长出自己的暖。
它的铜铃铛声在冬夜里听起来尤其寒冷,我们抱火炉取暖,它戴着冰冷的铃铛在寒风里来回跑。不跑便会冻死。月亮不怕冻,它是藏獒和牧羊犬的后代,身上有厚厚绒毛。天冷前给它们俩挨着修了狗窝,里面垫了层麦草。太阳不敢自己在窝里待,放进去就跑出来。它往月亮的窝里凑,一进去就被月亮咬出来。月亮真是条守原则的小母狗,白天跟太阳这只小公狗怎么打闹都可以,晚上就是不让太阳进自己的窝。
〔13〕后来不知为什么月亮也不在窝里待了,可能狗窝在院墙边,太阴冷。我在门口用纸箱给太阳做了一个小窝,纸箱侧面掏一个洞,上面砖压住,里面和洞口处铺上麦草,太阳晚上住里面,这次月亮随了太阳,卧在洞口的麦草上,那个纸箱做的窝盛不下月亮,它只好给太阳守窝。
经过一个冬天—我们在菜籽沟的第一个冬天—太阳终于从一条宠物犬,变成了狗,它在寒冷的冬天里长出一身细绒毛。接下来的冬天,它将不再寒冷,不会在冬夜里不停地响着铃铛跑。我们也不再寒冷,书院在建锅炉房,到时候每个房间都会暖暖的。
〔14〕那天太阳把铃铛丢了,它从坡上凶猛地跑下来,像另一条狗。
丢掉铃铛的太阳没有声音了,它一路跑,一路往后看,好像那个叮当响的自己在山坡上没有下来,跑到坡下的又是谁呢。它跑一阵,回头朝坡上汪汪几声。那个刚刚还在叮当响的自己,在山坡草地上转一圈突然不见。往山下跑的是一条没有响声的狗。
月亮也觉出太阳不对劲,对着它咬。好像要把它咬回去,把那个叮当声找回来。
第二天一早,我扫院子,突然听见叮当声,太阳嘴里叼着系了绳子的铃铛,从山坡杏园里狂跑下来,一直跑到我身边。
〔15〕它自己把丢了的铃铛找回来了。
那以后它又成了一只叮当响的狗。
深夜醒来,又听见它的铃铛声绕着房子转。它可能闻见我醒来的味道了,有意要让我听见。在它的嗅觉里,我醒来和睡着的气味或许不一样,做梦时的气味更不一样。
我曾在梦醒时分隐约听见狗吠,看见自己站在屋外的黑暗中,我刚从遥远的梦中回来,未来得及进屋子,而睡在屋里的正在醒来。我闻见我的将从睡梦中醒来的气味,像一间老房子的门沉沉推开,全是过去的旧味道。
〔16〕那个在梦里远走的我,带着一缕不散的旧气息回来,站在窗外,他要在我完全醒来前回到我的睡眠里。或许是他的睡眠。我并不认识梦里那个我,不知道他在下一个梦里会干什么。我没有一只可以醒着伸到梦中的手,去安排黑暗睡眠里的生活。我活了五十年,至少有二十多年,活在不能自已的睡梦中。
睡是我生命的另一场醒。
我曾在这个黑暗世界一遍遍地醒来。
我醒来和睡着的气味,被一只叫太阳的小狗闻见。
麦收
〔17〕昨天午后,拉了高高一垛包谷秆的拖拉机,“突突突”从书院门外驶过时,突然觉得我们院子少了一车什么。书院菜地的包谷秆稀拉地站了几行,没来得及吃一口青玉米棒它们就老了。刮风的夜晚,包谷叶子干燥的响声传入梦中。我们忙乎半年,似乎只收获了一地干喳喳的风声。
从麦收开始,先是拉麦捆子的拖拉机,一座山一座山地,从门口驶过,接着是拉豆秧和包谷秆的车。
菜籽沟的秋收漫长到下雪,那时坡地上的麦子都要一镰一镰地割,从路上望去,人像小虫儿爬在坡上,一点点地蠕动,动一天,麦地凹下去一块。扎捆的麦子成行竖摆在麦茬地,远看像一块粗针脚补丁。
〔18〕从七月到八月,沟里都在收麦子,这个季节找个干活的都困难。前面雇的七个甘肃民工,六月初回家割麦子了,他们把盖了一半的房子扔下,把我们预计八月完工的计划扔下,说要回老家割麦子。
不回行吗?
说不行。
为啥不行?这边挣钱,在老家雇人割麦子,不一样吗?
说雇不上人,家家的麦子都熟了,谁有空给你干活。
盖一半的房子扔了半个月,他们一起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是黄昏,从拖拉机上下来,个个脸色像饱满麦子。
〔19〕第二天,他们的身影又晃动在墙头上,还是那些人,接着半个月前那个茬往上垒墙,只有我知道,那个茬再也接不上了,首先砖缝难完全对上,即使后来勾了砖缝,我也一眼能看出他们停顿又续接的缝隙。更重要的是活搁了十几天,房子主人的想法变了,原先定的木头架房顶被钢板替代,木工活被铁活替代,事实上盖出来的房子变成另一栋。半个月前他们因为回家割麦子而耽搁的那个砖混木框架的房子,永远都不会再盖出来。
甘肃的麦子割完了,新疆菜籽沟的麦子才开始黄。坡地陡,收割机上不去,全靠人工镰刀割。一人一天顶多割一亩地,一家种几十亩,就得一个劳力起早贪黑累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书院的其他活耽搁下来,除了那几个回来的甘肃民工,再找不到给我们干活的人。
〔20〕这个季节,哪有比割麦子更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只有眼巴巴看他们快快收割,院子里不打紧的活停下来。多好的太阳啊,多好的白云,多好的月亮和星星,我们干等着,看他们收获。我们挖管沟、修路、收拾院子的活,放一年也没事。路不铺也没事。哪有比割麦子更大的事呢。
地上收麦子的季节,天上星星月亮都闲着。地上的麦香往星空里飘,那里有一层人,每年这个季节让麦香熏醒,他们眼睛朝下看,跟我们朝上望的目光相遇,仿佛黑夜里面对面走来的亲人。
〔21〕我在这样的夜晚清闲下来,躺在靠椅上看星星。夜空像茫茫戈壁一样,那些朝黑暗里走远的人,夜夜回头,我在书院的松树下,等候他们回望的目光。迟早我也加入其中,在奔赴无尽黑暗的路上,我夜夜回头,到那时坐在夜空下看星星的人是谁呢,谁从茫茫星空里辨认出我微弱而深情的目光。谁的思念会让我如花开放般醒来呢。
在书院的松树和杨树上面,在稍远的山坡上面,星空荒芜着。它底下的山坡沟底,年年种麦子种土豆,年年丰收。
挖坑
〔22〕我蹲在坑沿,看他们俩往外扔土。头一天,他们挖到半人深回去了。第二天挖到中午,老八找到方如泉,说坑两天挖不完,原来说的六百块太少了,让方如泉加点钱。方如泉说先干,干完再说。第三天下午,他们终于把自己挖进了坑里,只见一锨一锨扔出来的土,我没再去坑沿上看。我一去,老八就跟我说干亏了,让加点钱。
老八和老五算天工的时候,可能都忘掉自己的年纪,他们都五六十岁的人了。年轻时挖一个菜窖,也就一两天工夫。后来,菜籽沟就没有人家挖菜窖了。老八老五也有十年时间没挖过菜窖了。这十年他们挖的最多的是管沟,自来水通到村里,光缆拉进村里,都得挖沟往地下埋。他们早已忘了挖菜窖这回事了。
〔23〕可是,我们书院要挖一个大菜窖。我们地里的洋芋丰收了,黄萝卜也丰收了。得有一个大菜窖来冬藏。方如泉找来老八,老八在地上踏了尺寸,一口价要了六百块。老八回去又拉上老五。他们俩计划两天干完,一人挣三百。可是,他们干了整整三天。最后一天,干到星星出来了,菜窖的深度还差半尺。第四天上午,两人又过来补挖,等于干了三天半。
多干的这一天半,成了老八给自己挖的一个坑。菜窖挖完了,院子的其他活还在继续,老八每天一早骑摩托来,干到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又来干到天黑。只要碰到方如泉,老八就说加钱的事。
〔24〕他说自己多干一天半不要紧,关键是老五不愿意,老五六十多岁的人了,被自己叫来干活,还干赔。说自己挖菜窖累得胳膊疼,现在都没缓过来。还说自己夜夜做梦,梦见自己在一个越挖越深的坑里,出不来。方如泉只是笑着装糊涂。老八一嘟囔他就走开。
方如泉到最后也没给老八他们加钱。这期间我去湖北“长江讲坛”讲了一场课,题目是“从家乡到故乡”。我用自己独特的散文语言,带着在场的五六百人,从家乡出发,往永恒的故乡走。那么多的人,跟着我回家,一个童年的家,路窄窄的,天低低的,光线时暗时明。我讲的是我一个人的家乡,但是,那条语言之路通向所有人的故乡,仿佛人人都回到自己的故乡,我带他们去,喊他们回。他们仿佛忘记了回。
〔25〕演讲结束后,突然觉得我给他们挖了一个叫故乡的大坑,我把他们带进一个大坑里。离开武汉后的好多天,一些人还在我挖的那个坑里,我从微博信息中看见他们留言,有一个读者说,刘亮程老师都回新疆了,我还在他讲述的那个村庄里。
我回到菜籽沟时菜窖已经挖好,里面躺了一堆洋芋。这个温暖的盖了顶棚的大地窖,成了一堆洋芋的家。在接下来的漫长冬天,我们会一次次地下到窖里,拿洋芋出来,炒土豆丝,做土豆烧牛肉。到那时,老八梦里的那个坑或许还没挖完,这个活他得在梦里干一个冬天,我们帮不了他,或许他会叫上老五,老五比老八聪明,但老五不知道,每个夜里老八都拉着他挖坑,一边挖一边听老八嘟囔活干亏了。
〔26〕老五就这样被老八白白地在一场场的长梦里使唤,他以为自己睡觉休息了,他干完白天的活,回家洗漱,吃妻子做的汤面条,有时还自己喝两口酒,然后上床睡觉。可是,他睡着后被老八喊走了,他不知道自己夜夜在老八的梦里跟着他挖坑,那个坑越挖越深,永远挖不完了。因为老八认为挖亏了,所以在每个梦里,老八都扭亏为盈,他在一些梦里轻松挖好坑拿了钱,分给老五一半,有时不分,自己独吞。可是,那些梦里挣的钱他带不到梦外。醒来他依然是亏的。这个梦没完没了。老五每天睡不醒,白天干活老没劲,他不知道劲去哪儿了,只能承认自己老了吧,有些人就是这样老的。当然,也有另一种老法,像老八,掉进一个坑里,出不来。
〔27〕我们的菜窖呢,只装了小半窖洋芋。我们说洋芋丰收了要挖一个大菜窖的时候,没有谁怀疑。可是,我们在书院的第一季洋芋没有丰收,但也足够吃到来年的洋芋成熟。其间大菜窖会逐渐空荡地等候新一年的收成。只是我没下去看过,下菜窖都是方如泉和方圆的事。我只是偶尔经过时探头朝里看看,有时晚上经过,突然想起老八,不由得站住。菜窖上面星星密布,在多少个有月光的夜里,这个菜窖被一次次重新开挖,我看不见老八和老五,他们或许能看见我,在老八完全封闭的梦里,我的脚步声传不进去,太阳月亮的吠叫声传不进去,厨房煮肉炒菜的香味飘不进去,金子提茶壶倒的一碗水递不过去。在他们挖菜窖的那几天,金子每天做完饭洗好碗给他们烧一壶茶放在坑边,老八老五都夸金子热心。
〔28〕在老八不着边际的梦里,金子是否也一次次地给他烧茶,我不知道进入老八梦境的门在哪。但我一定夜夜在他梦里,他光梦见挖坑不行,得有一个梦中给他付钱的人,那个人肯定不是方如泉,因为方如泉不会给他加工资。他有一次找到我,说坑挖亏的事,我答应给他加一点。可是,我去湖北讲课了,回来再没见到他。他在梦里每重挖一次坑,我就给他加付一次工钱,我不知道给他付了多少钱,一个小小的菜窖会让我没完没了地给一个梦中人付钱。也许我早把所有的钱付完,变成一个穷光蛋。接下来,老八会不会在梦中翻身,我们书院和所有房子,都归了他。他背个手,站在坑沿,看我给他挖菜窖,一天天把自己陷到一个深坑里。他低头跟我说话,我在坑里仰脸看他,说这个坑挖亏了,让他加点钱。他说加钱?没门的事。一扭屁股走了。
黑暗
〔29〕老八拖着黑黑的影子从坡上下来。他的摩托车停在大路边,我以为他会骑摩托回家。如果他骑上摩托,黑影会被他甩掉。老八骑摩托野得狠,“鬼都追不上”。这是老五说的。老五的意思是鬼追不上飞跑的摩托。我有点不信。年前我看见有人在路边烧纸汽车纸摩托,可能鬼早已经骑上了摩托。也可能鬼不骑摩托,他们有更快捷的工具—影子。
鬼在黄昏时躺在那些疲惫的人影里被带回家。人在地里干活,鬼蹲地头看。也不看,冥冥地待着,等人干完活。也不等,等和看这些事情,对鬼来说也早已不存在。鬼只是冥冥到日头倒西,人的影子伸长过去,把鬼接上。
〔30〕在能看见鬼的小孩眼睛里,鬼仰脸躺在人影子里,头脚对齐,很舒坦的样子。有时鬼坐起来,驾牛车一样吆喝人的影子前行。藏了鬼的影子拖累人,但人认为是自己干活累的,不会想到被影子拖累。
鬼舒坦地躺在影子里跟人回到家。也早不是原先的家。墙上的照片都撤了,以前的旧家具也不在,房子的主人换了几代,但人还是熟悉的相貌,姓也没变。
鬼是能记得自己的姓的,也记得在世时家人的样子。后人时不时地念想让鬼冥冥地睁开眼,朝着人世里望。望着就想回来一趟。循着黄昏时母亲喊孩子的叫声回来,听着吱呀的开门声回来,挽着袅袅炊烟回来。更多的贴着地上长长的影子回来。
〔31〕路拐个弯,影子颠簸一下,到家了。墙根玩耍的邻家小孩对着影子大叫,自家的狗也对影子叫。人烦了,喝住小孩,撵走狗。小孩和狗都惊愕地看着一个躺着的黑影鬼鬼祟祟进了院子。
菜籽沟能看见鬼的小孩都长大走了,到外面上学谋生活,逢年过节回来一下。也都再看不见鬼。
剩下半村子老人,都避讳言鬼。看见鬼也不说。装没看见。就真的好多年没人看见鬼了。好像这世上真的没有鬼了。
老八没骑摩托回家,他直直进了我们院子。月亮猛扑过来,对着老八的影子狂咬,它看见这个人拖来的黑影里有不好的东西。
〔32〕我也看出了,他的影子比黑狗月亮的还黑。一个累坏的人,拖着比别人更黑的影子来到我们院子。我故意朝老八走近几步,两个影子并一起时我吓一跳。我闲了半天,影子淡淡的。老八的影子比我黑一层。
我赶紧问老八啥事,我害怕他把影子丢我们家院子。
有些人知道自己影子里藏了不好东西,回家前想法把影子丢掉。丢的方法多。比如,把影子拖进树荫里,自己溜掉。还有,骑驴背马背上,人和牲口影子叠一起。再就是天黑前找个借口进谁家,太阳落山了再出门,影子就丢给这家了。
〔33〕再就是骑摩托,油门一轰,“呜”地一溜子土,人瞬间不见。啥东西都甩掉了。
老八不像是要有意害我们的人。他割了一天麦子,腰还没全直起来。他的影子也弓着腰,看上去比老八委屈。
我问:今年麦子收成咋样。
老八说:没球相,顶多打一袋子多。
老八说的是一亩地收了一袋子多麦子,也就一百公斤的样子。每公斤麦子卖两块多,一亩地收二百多块钱,加上政府每亩地一百多的补贴,合三百多四百多块,机耕费种子费一除,落二三百块,还不算自己的工钱,要给别人割一亩地麦子,少说也挣一百五十块。
〔34〕老八种了三十亩地麦子,算下来纯收入六千多。
“白忙活。”老八说完咧嘴笑了笑,骑摩托走了。
他没说来我们院子有啥事。我也没问,他丢下一句“白忙活”走了。
我突然觉得心里闷闷的,好像他把三十亩地的负担全卸给了我,把白忙活的一年丢给了我。
老八一夏天在我们书院打零工,每天挣一百三十元。他六十多了,比我大几岁,没有啥手艺,只能干小工的粗活,拿小工的低工资。
老八干得最多的是挖管沟,他一点点地把自己挖进沟里。然后,只见一团一团扔出来的土。每次他从自己挖的深沟里出来时,都拖出黑黑的一截影子。
〔35〕月亮见他从管沟里爬出来就扑过去咬。月亮是天生的看家狗,见人在院子里拿东西就咬,对两手空着走在院子里的外人,它只是盯着看。从土里钻出来的老八让月亮感到了不安。它看见了我看不见的东西。
一个黄昏,老八拖着从自己家麦地里弓腰一天的劳累,来到我们院子,他把那片麦地里的黑拖到我们院子,就像他一次次地从自己挖的管沟里爬出来时,把土里的黑拖到地上。
月亮跟着他的屁股咬,想把他撵走,可是他不走,跟方如泉说账的事,他挖管沟的活少算了一天,把一天丢了。按日期算天数又没丢。他进院子挖了七天管沟,按七天付工钱。但他硬说是八天。他干了八天活。这七天里他从沟里上来下去多过出来一天。谁知道这一天该咋算。
〔36〕老八出院门时月亮依旧对着老八的影子咬。它可能闻见影子的不明气味,看见影子里藏着的黑东西。老八不理识月亮。在月亮一嘴紧迫一嘴的吠叫里,老八的影子渐渐拉长,月亮的叫声也渐渐拉长。最后,老八的影子伸到院门外,跟门口小河边榆树的影子并成一体,跟门外坡地上麦田的影子合为一体,一个更大的阴影从天上地上盖过来,天突然黑了,我一低头看见整个夜晚,跟在老八拖进来的黑影子后面,悄悄地覆盖进院子。
我们没有在天黑前关住院门,把黑夜挡在门外。
我们的院门一直敞开到月亮出来。那时我在半睡半醒间,听见书院的皮卡车从外面回来,车灯直直照亮院子,照到台阶上的孔子像。然后,我听见铁门和锁链相碰的声音,高高的,仿佛响在月亮和星星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