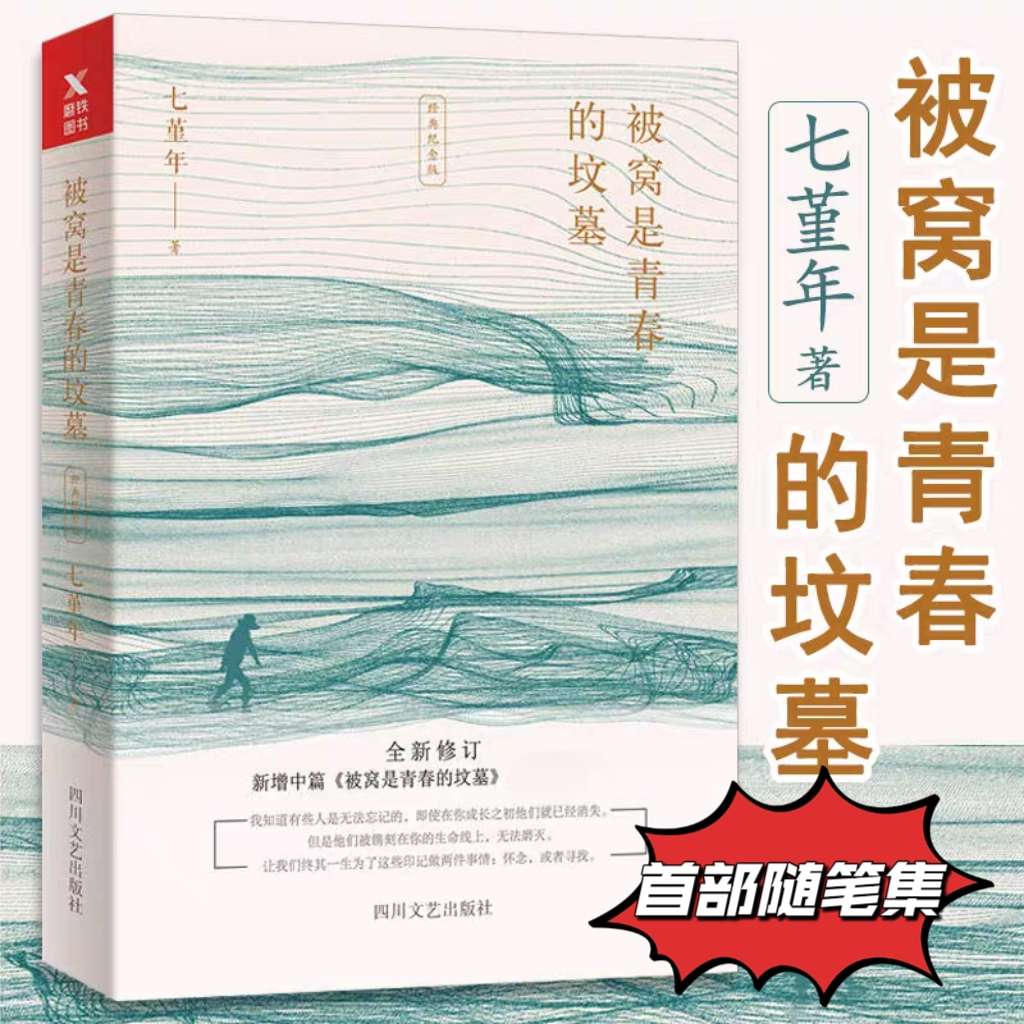
〔1〕翌日又是不停地乘车,导游按照大家的建议临时更换了路线,于是我们的车在渺无人烟的山间行驶。植被荒凉的岩山。盘山公路屈曲回绕。风异常大,干冷而且凛冽。下山的时候坡度减缓,山坡上有当地人废弃的石头房子,更显荒凉。随着山路的转弯,河流忽隐忽现,岸边开满了黄红紫相间的野花——我从未见过这样美丽而繁盛的野花——像是维吾尔族少女的羞涩笑容,明艳并且色泽饱满,充满了生命的质感。我们停下车来,所有人都拥向这片野花。它们在开阔而干燥的土地上一直烧到天边,在这塞外的六月阳光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茂盛。我替那位小姐姐照了一张相。她拘谨地坐在地上,笑容浅淡。阳光和她身边的野花一样,兀自撒欢。
〔2〕我突然想起一部伊朗的电影叫《天堂的颜色》。电影里有中东的沙漠上大片紫红色的野花,两个盲小孩天天采集这些野花,装在篮子里带回家碾碎,制成天然的染料。奶奶在家织出精美的挂毯,用花的汁液染色,在集市上出售,被旅行者带到很远的地方去。
突然直面生命中这么纯真的一面,几乎令人感怀得落泪。
后来我们就进入了乌一号和乌二号冰川地区。
在雪线以上的陡峭山脉间小心行驶,窄小的公路上时刻有翻车的危险,遇到迎面而来的卡车,小心翼翼地倒车,错车。你可以看见悬崖边上的碎石滚落下去。也许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从三千七百米的山上滚入谷底。
〔3〕十几个急转弯之后,我们终于望见山川之巅积覆的冰雪。
下车,陡然感到寒冷的烈风穿透自己的身体一般,迅猛地进入胸腔。站在悬崖边上俯视铁灰色的崇山峻岭,丝带一样盘绕的公路,以及近在视野中央的银白色冰川覆满整整一面高山。只穿了一件短袖,零度的气温让我冷得嘴唇发紫。
站在这样的悬崖边上,有摇摇欲坠的仓皇快感。仿佛生命可以以这样一种壮烈而寂静的方式断裂。于是突然于这六月的雪山艳阳下瞻仰起生命最本真的脆弱与阒静。你不由得怀疑起经历它的目的与意义,感到满目冰川一样寒冷的绝望,轰然坠落。
〔4〕这是我在新疆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无论是后来我踩在五十度的火焰山上,还是在天池的水边,都不及冰川,给我这样的峰极体验。
新疆是这样一片丰富的土地。有着塞外江南最阴柔的脂粉和大漠孤烟最阳刚的汗液。你看见青山绿水之中的溪涧,以为自己身在不为人知的江南小镇;但是走出绿洲,你又见到大片大片黄沙漫延的悲情荒漠。历史与景象交错。它们在维吾尔女子的一颦一笑中歌舞升平,丰美盛极。你几乎能见到从阿尔卑斯到西伯利亚,从盛唐遗风到现代商业区的全部景观。
在这旅途的夜晚,仰望这里最纯净的深色天幕上面布满星辰,突然觉得能在这里生活,是神的赐福。
〔5〕我结束了十五天的行程,在乌鲁木齐休整了一整天,和那位小姐姐一起,继续乘坐北疆线,在奎屯下车。从奎屯,至克拉玛依、乌尔禾、吉木乃、哈巴河,然后国道终止。那位小姐姐在这里终止旅途沿原路返回。我继续向北。向阿尔泰山区深入。
这些路程花费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沿途风景优美,许多牧民和村舍,令你怀疑身处阿尔卑斯的村落。但长途坐车,听不懂语言,夜晚来临时非常害怕。极致的孤独,使我面对并且自省本我。
幸好一路上我和那位小姐姐是很好的旅伴,在夜晚露宿的时候,她让我先睡,她守夜,然后凌晨叫醒我,我来守夜,她接着睡。她只睡不长的时间。她告诉我长期的旅途使她异常坚定,有时候一个人,还不是得彻夜地熬过来。
〔6〕在哈巴河我们分手。各自踏上旅途。
我已经对这样的行走着迷。
一路上小心询问驻守边疆的士兵。大概清楚了去禾木的方向。在阿尔泰的林区工作人员有很多是汉人,他们大多很久没有回过家了。我甚至遇到了一位同乡,一个四十多岁的林业管理员。我和他说起老家的事,他忍不住掉下眼泪。但是我亦不敢在那里停留,问了路就匆忙行走。临走的时候他给我一件军大衣,说这么冷的地方,你一定熬不住。这是以前一个朋友的,他大概永远用不着了。你带上。
我说,谢谢。
抱着陌生的温暖,心怀感激。
〔7〕在路上又过了一个月。走走停停。七月末,我到了禾木。
这个村寨有十几户人家。在阿尔泰的山谷里。额尔齐斯河有细小的支流养育这里的人。风景如画。每家每户有自己的一群牲畜。生活非常原始。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记得我刚刚到那里的时候,已经将近黄昏,搭乘采金矿的工人的拖车。下车后自己走了几里路。天色渐晚,林区的黄昏迅速寒冷起来。我在远处望见童话一般的小木屋零星点缀。
我在艰辛的行走之后累得不行。走向最近的一间木房子。敲门。这仿佛是某部神话或者电影里的情景。门被打开的时候,我惊讶至极地发现站在门口的是一个白种女孩。但似乎也有东方血统。非常清澈的面孔。
〔8〕浅棕色的长发编成辫子垂至腰际。高寒地区的人们普遍高大,但从她的身形依然看得出来是非常年轻的少女。衣着和当地人一样朴拙。我看着她蓝色的眼眸,如同旅途之中见过的高山湖泊。寂静并且清澈。非常熟稔。
心生好感,觉得安全。我比手画脚地向她表示,我可不可以在这里留宿?
她微笑着说,好。
我没有想到她还会讲汉语。后来的交往中我知道她会说一些简单的汉语。
拉拉衣加。三弦琴的意思。这是你的名字吗,衣加?真美。
〔9〕就这样我随她进屋。非常窄小而温暖的屋子。我在房间里四顾:正屋的墙上挂着一把三弦琴,我知道那是俄罗斯古老的民族乐器。她对我说,这是外祖母的宝贝。她是俄罗斯人。所以我的名字就叫拉拉衣加。就这么简单,没有其他。
房子全部用原木搭建而成。散发着森林的清香。窗子和墙缝透进一束束细细的昏黄光线。由自家手工制作的宽大毯子,手感温厚。她把我领进她的卧房,极为简陋。两张木床之间刚好侧身通过。她说平日里她和外祖母一起睡。外祖母不久就会回来。我把行李推到床脚边的角落里。和她一起走出去。
我们坐在灶边,衣加忙着烧火煮食。跳动的火光映在她温润的脸庞上。我们不说任何话。
〔10〕不久衣加的外祖母便回来了。她扛着一大袋土豆,看到我略微震惊了一下。我拘束地站起来,向她行躬身礼——除此之外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做。衣加走过去接过袋子,用俄语向老祖母说着一些话。外祖母向我微笑。真正的俄罗斯老太太。臃肿肥胖的身体,面色红润,大辫子发白。
老祖母走到我面前,用我听不懂的语言热情地说话。衣加说,外婆很欢迎你。她很喜欢你。
那晚我们一起吃饭,席地而坐,手抓牛肉和土豆泥。非常美味。饥饿太久,我狼吞虎咽地吃着。抬起头来发现外祖母怜惜地望着我。喃喃自语。衣加的面容忧郁起来。
〔11〕晚上非常寒冷,我与衣加睡在一张床上。外祖母发出均匀的呼噜声。我非常疲倦,却整夜无法入睡。轻轻一动,木床就发出嘎吱嘎吱的巨响。我不敢辗转反侧,怕吵醒衣加和外婆。凌晨的气温大概只有几度。我不得不拼命裹紧棉被蜷缩身体。窗下有牛儿低声叫唤。
思维平行着像铁轨那样往深处延伸。触及遥远的有关家的事情。
我暗自计算,离开家已经两个多月。母亲是否会苦苦等待我的归来?是否会在每一声门铃响了之后都欣喜地站在门口以为是我?是否像我一样体验了真正的绝对孤独之后开始怀念亲人的意义?父亲又在哪里呢?十禾呢?
〔12〕我就在这边境的村庄,在这寂静无声的夜晚里想念你们。
有时候明白人的一生当中,思念是维系自己与记忆的纽带。它维系着所有过往。悲喜。亦指引我们深入茫茫命途。这是我们宿命的背负。但我始终甘之如饴地承受它的沉沉重量,用以平衡轻浮的生。
我这样想念你们。
清晨,远镇有着熹微的晨曦。雾霭缭绕在林间,视线因此迷离起来。衣加和外婆先后起来,开始忙碌各种事情。我局促地站在一边,问,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衣加笑着说,没有,不过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放马。
〔13〕就这样我们带上手抓饭和马奶,随马群行走,跨过湖泽和草甸、树林与野花。如同在欧洲的童话里,向神秘王子的城堡前进。
禾木有很多高大的桦树,树干雪白,桦叶渐次变黄。恍若油画上斑斓的色彩,肆意蔓延。
清晨天气很凉。到处有零星绽放的野花。未上鞍的马儿低头吃草,鬃毛被镀上金色。都是我从未奢望得见的景象。宁静如同儿时睡前母亲在耳畔唱过的歌。在这片不食人间烟火的净土上,难以想象我是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而来的。在那个世界我们贫穷得需要出卖灵魂以求生存。在充斥着压抑气氛和粉尘的污浊教室里做着习题。面对着心口不一的嘴脸。与身边同样不知道哪里来也不知道哪里去的人们一起,度过一天又一天。
〔14〕而现在我在这个风景如画的远镇。看时光静止。记忆摇曳多姿。多么好。
一个星期之后我和衣加一家渐渐熟悉,力所能及地为她们做一些事情。我喜欢这个家庭,祥和并且神秘。她们的善良让我这样温暖。夜里,衣加喜欢牵着我的手入睡。有时,会有节奏缓慢持续的对话。
你妈妈呢,衣加?
她去找我爸爸了。很久没有回来了。
那你爸爸呢?
以前他会每年都来看我们。可是后来,他渐渐不来了。
你想他吗?
我很想他。爸爸是很好的人。
那你外祖母呢。她为什么会来这里?
……这些事情太远了。真的很远。
〔15〕你看见墙上的三弦琴了吗?外祖母年轻的时候和外祖父一直在一起。外祖母喜欢弹奏三弦琴。她是村里弹唱得最好的姑娘。我没有见过外祖父。但是外祖母告诉我外祖父是第一批来中国勘探矿产的俄国人。那个时候外祖母怀上了我母亲。她因为想念只身来到新疆,被队友们告知外祖父罹难,成为苏维埃的烈士。外祖母承受不住打击,险些流产。同事们送她回国,在边境上外祖母身体不支,差点死去。当地人救了她。两个月之后,早产生下了我母亲。由于大雪封山,无法行走,外祖母在这里停留了下来。来年化雪的时候,她已经决定不回去了。因为她要和外祖父在一起。
〔16〕就这样外祖母在这里定居。俄罗斯是让她伤心的地方。因为那里充满了恋人的气息。
我的母亲与外祖父很相像。外祖母非常爱她。母亲后来遇到一位来这里勘探的汉人,也就是我父亲。母亲陷入恋情。她不顾一切。在他离开之后,母亲固执地留下了我,以此纪念他的爱。在我一岁的时候,父亲来过这里。后来父亲曾经很频繁地来看过我,教我汉语,给我带来衣物。五岁的时候父亲又来过一次。却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了。母亲在等待了两年之后决心去找他。
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见过父母。
〔17〕我们一直说到天亮。我看见衣加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烁着。我伸出手小心触摸,唯恐惊吓了这个幼小的婴孩。我抚摸她的长发,渐渐抱紧这个可怜的小孩。衣加把头埋在我的脖颈之下。我感到她灼热的眼泪滚过我的皮肤,几乎将我烫伤一样疼痛。
十一月。阿尔泰下了第一场雪。
天地间只有一片雪白,那种真正的漫无边际的皑皑白雪。纷扬的大片雪花欲要原谅一切。不停地飘落。我从来没有见过雪。于是站在木屋的门口,心中寂静如这空山,只被大雪覆盖。
很多个夜晚,衣加向我诉说她的父亲和母亲。我只是安静地听,却说不出来任何话。忽然感到生命的韧性可以如此顽强。遥远的边疆,有遥远的故事。我忍不住想永远留下来,守护可怜的衣加,还有外祖母。
〔18〕在我自以为痛苦的城市生活中,从未曾想过,时时刻刻都有不幸的事情发生。而你能与他们擦肩而过,并在此刻只是聆听这种残忍,已经是多么庞大的幸运和福祉。
我吻衣加的额头。衣加,我想一直留在这里。陪伴你们。
家里储存了一冬的粮食:土豆、青稞、荞麦面粉、腌肉。由于不适应这里的饮食,没有蔬菜和瓜果,我的牙龈溃烂,流脓流血。鼻血不断,皮肤有道道皴裂的血痕。衣加心疼地冒了大雪走很远给我摘来一种果子。青红颜色,非常酸。我感动地不知道说什么好。吃了两天的酸果,病很快就好转。
〔19〕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每天给马厩加草料,煮食。那些日子里感觉自己一不小心就成了关心粮食和蔬菜,喂马劈柴的诗人。夜里很早便睡去。禾木的当地人非常好心,常常有人给衣加一家送来粮食和御寒的兽皮。这些垒木为室、狩猎为生的人,知道衣加她们无法打猎,好心地送来兽皮,让一家人过冬。
阿尔泰的冬天这样漫长。黄昏的时候,天黑很早。天空是纯净的钴蓝。夜幕下的雪也是蓝色的。美丽得无以言表。广阔的林海成了一片雪原,额尔齐斯河冻结。我们在温暖的小木屋里生火,取暖,煮食。听外婆弹奏那把三弦琴。唱着俄罗斯忧伤的民谣。
〔20〕我凝视着燃烧的柴火,映着外祖母苍老慈祥的容颜,伴着忧郁的琴声,看见爱情最深沉动人的面容。优美至极。
生命在这样的瞬间,显得充满尊严和永恒。那亦是爱。永无止息。
衣加坐在我旁边,神情平静。我轻轻抚摸她的脸。
衣加。你在想你的母亲吗?
是。我非常想念。还有我的父亲。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还有老祖母。
不用说这么绝对的话。我已经十五岁。完全习惯了。我只想好好陪外祖母,一直生活下去。
外祖母担忧地抬起眼睛。看着我们。
大雪封山,皑皑白雪好像永不会消融。我已经在禾木待了六个月。这已经是我十九岁这一年了。
〔21〕二月,阿尔泰的春天还没有来。在这些安静的时日里,除了帮衣加和外祖母干活,其余的时间,就和衣加聊天,或者写些文字。我的背包里有两支上好的炭笔,一本速写本。我画了几幅素描。一幅是衣加,长长的辫子,眼神清澈。靠在一匹马身上。甜美无知疼痛的微笑。还有一幅是外祖母。她坐在火炉边弹奏三弦琴。最后一幅是木房子门前的溪流、野花。层层叠叠铺到天边。衣加最喜欢的那匹小母马,低头吃草。
其余的白纸上,有凌乱的文字和诗句。
衣加曾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以看吗?我说,这本来就是送给你的。她看见我画的人物肖像,惊喜地问,是我吗?是我吗?我有这么漂亮吗?
〔22〕我说,衣加,你和你母亲,还有外祖母一样,都是这世界上最漂亮的人儿。
然后她天真的淡淡笑容,徐徐绽放。
禾木的冬天里,安静的夜里偶尔听得见冰雪压断树枝发出的裂响。噼噼啪啪几声,寥落地在大山里反复回荡。春天来临的时候,额尔齐斯河的冰大块大块地崩裂,浮冰在生机勃勃的流水中撞击,如同远方的鼓声。雪渐渐融化,湛蓝的天空之上,偶尔见到候鸟优雅迁徙。土瓦人高亢的歌谣,同春晓之花一起绽放。一个新的季节来临。一转眼,就快一年了。
〔23〕衣加和我忙碌起来,砍柴,喂马,帮外祖母织毯。木房子檐上覆盖干草用以保暖,屋顶上又有空洞用于通风。独特的房屋结构。我尝试修葺熬过了一冬的老木屋,寻找新的干草换掉已经腐烂的那些。劳作的感觉异常充实快乐。
我们放马的时候,漫山遍野奔跑。我采摘野花,插在衣加浅棕色的辫子上。她穿长的布裙子,被风吹得裸露出膝盖。羞涩地笑起来。
初夏来临的时候,山区才渐渐转暖。阳光漫过重重山林千里迢迢而来。带着森林的清香。草长莺飞。温暖如同童年梦境中的仙境花园。外婆织了整整一冬的挂毯终于快要完工。上面是西伯利亚最常见的雪景。俄罗斯广袤的雪原深处,零星闪烁的温暖灯光。与繁星一起熠熠生辉。天空犹似海洋的梦境一般。充满了故乡的气息。
这竟是我们最后的夏天。
〔24〕五月。我出来整整一年。那天清晨,我和衣加起床,却发现外婆依旧躺在床上。以往她总是醒来很早的。我轻轻走过去,推推外婆的肩。然后看清她的脸,吓得不轻。大概是中风或者脑溢血之类,只见半边脸抽搐,口水从嘴角流出来。手脚都抽着筋。我抓住床沿,努力站定,控制自己不叫出来。衣加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我紧紧抱着她,拦着她不让她看见,拼命挡住她的视线。衣加,你不要看了,祖母只是生病……衣加……听话……不要过去……
衣加大哭着拼命挣扎,用俄语大声喊,老祖母,老祖母——她的手肘戳在我的肋骨上,一阵剧痛。我放开手,衣加冲了过去,跪在床边,凄厉叫喊。她推搡外婆的身体,非常用力。
〔25〕我冲出门去找邻居,本来就不会说当地语言,这下更是语无伦次。哭着敲门,门打开。是一个来送过毛皮的邻居,我话音未落,那个男子抓起我的手臂就跑向我们的木屋。他进了房间,看见老祖母,然后喃喃的,表情很难过。他把哭得快要闭气的衣加扶起来,徒劳地劝慰着。
我站在一边,心慌如焚,手足无措。
那把三弦琴还挂在墙上。刚刚织好的精美挂毯上还留着她的温厚摩挲。
衣加几天没有进食。她只会坐在外婆床边,凝视一个方向。
我笨拙地煮来荞麦面,加上盐,给衣加端来。她依旧坚持不吃。整个人表情呆滞。我放下碗,缓缓靠近她。
〔26〕衣加。吃一口。不要这样了,我求求你。走过去紧紧把她抱在怀里。亲吻额头。渐渐用力,似乎想把她全部藏进我的怀中。这个可怜的孩子,怎么会在成长之初就遭遇这么多。
衣加渐渐恢复知觉似的,缓慢伸出手,犹犹豫豫地抱着我。我心中快慰许多,这一夜之间,衣加开始长大。
按照当地人的习俗,邻居们帮忙安葬了外祖母。宰杀牲口。祭祀仪式悲壮而繁琐。他们燃起篝火,飞扬的黑色灰烬被风吹起,向天空深处飘落。在葬礼上,牛角的奏鸣低沉悲哀,我忍不住落泪。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心中很歉疚没有好好照顾她们。寨子里的人无论老小,看见我和衣加,都悲戚不已。
〔27〕木屋陡然空了。那张大床就这么空空如也地等待着一具已经不存在了的身体。深夜里,我们因为惧怕相拥而眠。她的确比我小,能够很快陷入沉沉睡眠。而我整夜目不交睫。黑暗中,长久凝视衣加的安静睡容。
一个月之后,我们的生活和情绪渐渐恢复正常。衣加真是坚强可怜的孩子。我们每天照样劳作,夜里靠得很近。互相取暖。
有一个夜晚,她显得精神很好,很久都没有睡着。她试探着碰碰我,问:睡了吗?
没有。
我睡不着。我想外祖母了。
〔28〕衣加,老祖母是很幸福的。她去很远的地方。我们应该祝福她。如果太想念她,她就会在路上频频回头看我们。那样会耽误去天堂的路。
我该怎么祝福她?
衣加,和我一起好好过。这样,外祖母就会得到安慰。她可以见到外祖父。
衣加,跟我走好不好?我们离开这里。或许你会见到你的母亲父亲。如果你不喜欢外面,我们就回来。好不好?
外面是哪里?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衣加最后说,如果我不喜欢外面,你保证和我一起回来?
我保证。相信我。
〔29〕过了些天,我们便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上路。衣加固执地要带上三弦琴和挂毯。她只带了这两件东西。我将牲畜交给隔壁的大叔,挨家挨户道别。土瓦妇女们善意地给我们食物,送我们走很长一段路。
就这样我踏上归途。我想先带衣加到我父亲那里,再作商计。
沿着一年前我艰辛跋涉过的路程往回走。一路上是熟稔的风景。身上还有父母给的钱,不至于挨饿。从林区出来,上国道,长时间地行车。衣加从来没有坐过车,晕车非常厉害。我们不得不一再停下来,休息,徒步行走,累得不行,然后又拦车。在诊所买到了晕车药给她吃,情况好多了。
〔30〕车子渐渐驶进大漠的边塞城市,新奇的景象是衣加从来没有见过的。她惊奇观望周围一切事物,幼童一般天真。始终紧握我的手,生怕被遗失。她这些缺乏安全感的小动作令我非常心疼。只要有食物我总是让她先吃饱。看见她像以往一样甜美的笑容,心中很快慰。
路上衣加睡觉,将头枕在我的腿上。我昏昏沉沉地望着车窗外的景色。想起遗忘中的人们……母亲,父亲,十禾,送我来这里的那个维吾尔男子。明媚的面孔。海岸线一样迷人的线条。我轻轻笑了起来。
此去经年,我的那把黑色吉他应该布满了灰尘,钢弦上沾着斑驳锈迹。挂在墙上的景物写生应该开始褪色。我的朋友应该将我遗忘,一如我不经意间就遗忘了他们。
〔31〕三个星期之后,终于又到了库尔勒。晚上。我带着衣加朝父亲的铁皮屋走去。我在远处就能看见铁皮屋在夜色之中闪着寂静的光。疲惫而温情,是属于一个父亲的内敛感情。
打开门,父亲带着疲倦的神情站在门口。他惊异地看着我,然后把目光投向了衣加。
爸爸!衣加突然大声喊。
我感觉微微晕眩。继而努力确认衣加扑进父亲怀里,父亲严肃镇定地将她揽入怀中并轻轻抚摸的情景——是真实的。
一瞬间我就什么都明白了。我低下头。衣加天真地喊,你怎么知道我爸爸在这里?
我努力镇定地说,衣加,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们只是碰巧有同一个父亲。
〔32〕衣加依旧不懂,只是沉浸在欢喜之中。
父亲无限隐忍与尴尬的表情,重重烙在我心底。
进房间之后,衣加新奇地参观房间。父亲安顿好我们,让我们上床睡觉。睡前衣加惊喜地看着床头那张陌生女子的照片说,妈妈!
——爸爸!你有妈妈的照片?衣加激动至极。
父亲已经明显很尴尬,他悄悄过来,说,其实……
我微笑着打断他,说,不,什么事也没有,真的。我理解。但是衣加的外祖母已经死了。我希望你去找到衣加的母亲。她母亲没有来找你吗?她们的生活有多可怜,你完全无法想象。我与她们生活了将近一年时间。我很了解她们需要什么。
〔33〕父亲直视我的眼睛,我们之间已经明显有了成年人的对峙。这让我非常难过。
那夜我依旧与衣加相拥而睡。她善良单纯,我不忍心对她多说一句话。月光倾泻进来。我又感到风沙落在我的眼睫上。我看见父亲站在小窗旁边,猛烈地抽烟。黑暗之中,他不过是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三天平静的时间。衣加情绪良好,单纯快乐。与父亲相处融洽。我知道父亲非常疼爱她。这让我放心。
三天之后的夜晚,夜色深浓如酒。衣加仍然在沉睡,父亲已去值夜班。我起床收拾行李。轻轻拿开衣加握着我的手。她习惯不论何时都牵着我。
〔34〕我留了一张字条。放在衣加母亲的相框下面。
父亲,衣加:
我打算回家去。我很想念母亲。你们好好过。父亲,务必好好待衣加,她母亲来找你,没有下落。
堇年
我放纸条的时候,端详着衣加的母亲。发现衣加有着与她非常相似的面孔与神色。都是天真而且明媚。但是唯一的不同是,衣加脸上清晰浮动的,还有父亲的影子。
我起身,拿走了我和母亲的那张合影。看着沉睡中的衣加,心中非常不舍。她原来是我的亲人,我非常爱她。我在她额头上亲吻,像从前那样。但我已经不能拥抱她,因为这样她会醒来。我要她永远在这场梦境里。永远不要醒过来。我宁愿减去十年寿命,换取她在仙境里漫游,直到长大,直到老去。
〔35〕如旅途的开始,在同样的凌晨,我踏上归途。
列车驶过之处,有西域的黄沙柔软沦陷,尘土飞扬起来。落日一成不变。我在列车上蜷缩着身体,用睡眠打发时间。混乱的梦境中不断出现衣加的影子,还有老祖母、父亲、母亲、十禾。他们都在招手。这些摇摇欲坠的梦境,早已在生活中与我相遇了又相遇。就像我在高三的时候看过的一句话:
我只是好笑这些结局的雷同。这是早该料到的结局,却走了这么远的行程来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地上演一个闹剧的圆。
〔36〕当我真正以一个旅人的姿态回到城市的时候,我肩上的旅行包显示出我与城市里那些趿着松糕鞋、穿吊带短裙、妆容复杂的女子们的本质不同。从街边咖啡厅的巨大落地玻璃上,我看见自己风尘仆仆的行容一闪而逝。
我恍惚地想起西域忧伤的春天,山区的茫茫大雪。还有我的亲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时时刻刻都有比你意想中伟大得多或者悲哀得多的事情发生。而且,不只是爱情和死亡。
这个南方小城在暮色四起的时刻,平静地迎接我的到来。我站在熟稔的街道上,于火树银花的暖暖夜色之中又见此去经年的繁盛记忆。
〔37〕沿着暮色深浓的小街回家,想起在高三下晚自习从这里经过时,一路抚摸墙上被夜风吹得簌簌抖落的灰尘。哼着小调。默默用英文念出印象深刻的电影台词。
那还是十七岁的我。在下雨的时候独自赤脚蹚过哗哗积水的小小少年。有着温暖的梦境与凛冽的成长。
而如今我不过是以在幻想和回忆之间流盼的浮躁姿态,向死而生。
就这样我站在我家的庭院里,看见她耐心修剪花草的背影。素净,平然。是经历过悲欢离合之后不带任何悲喜的镇定。她明显老了,终究不可避免地衰老下去,以和我成长一样的迅疾速度衰老。
我把巨大的背囊甩在地上。
妈。我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