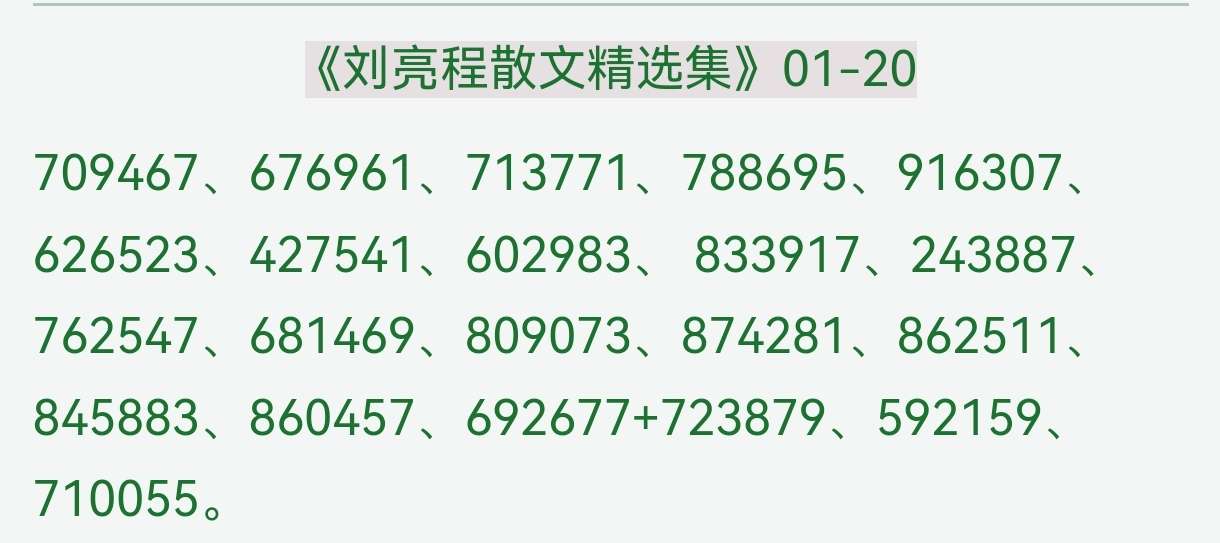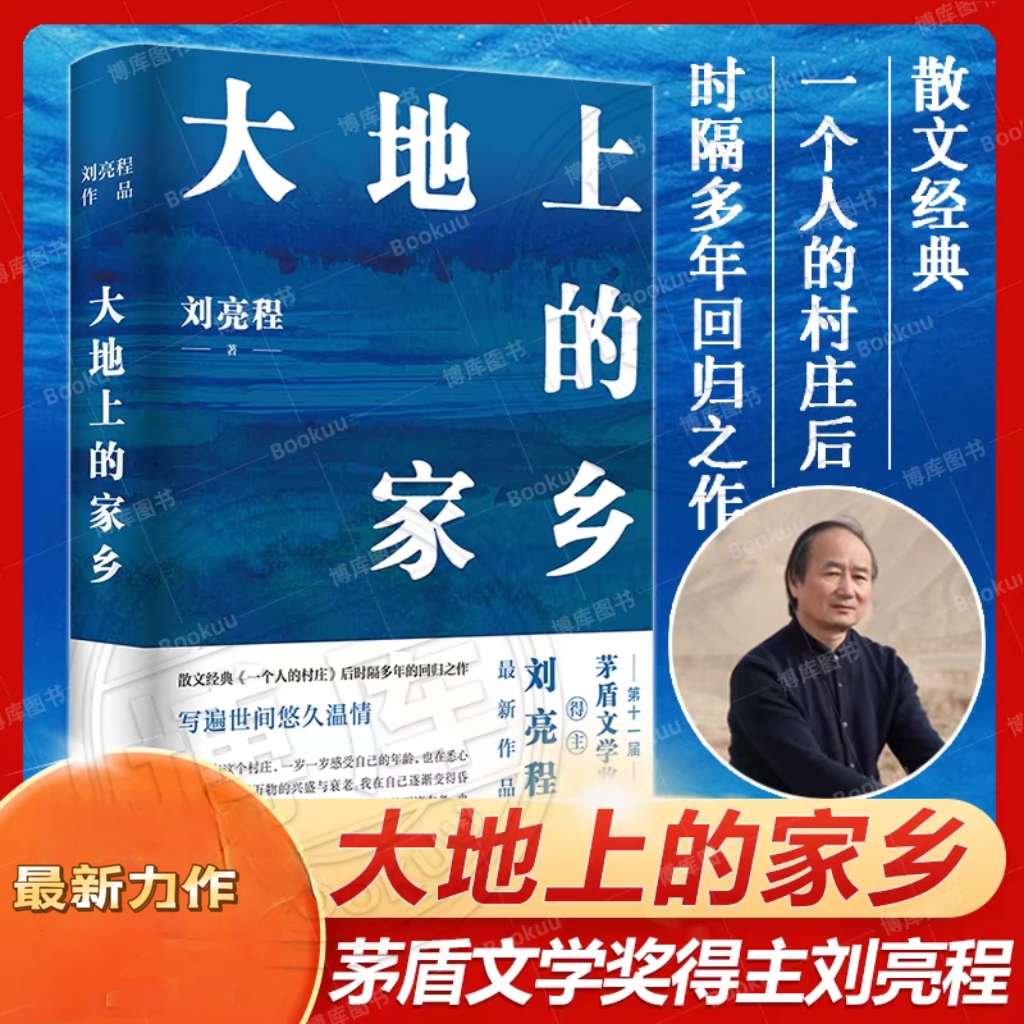
【第一辑·菜籽沟早晨】
赵木匠
〔1〕赵木匠家弟兄五个,以前都是木匠,现在只剩下他一个干木匠活。菜籽沟村的老木匠活只剩下一件:做棺材。这个活一个木匠就够做了。做多少都有数,只少不多。村里七十岁以上的,一人一口。六十岁以上的也一人一口。算好的。也有人一直活到八九十岁,木匠先走了,干不上他的活。这个不知道赵木匠想过没有。也有人被儿女接到城里住,但人没了都会接回来。
赵木匠的工棚里,堆了够做百十口寿房的厚松木板,一个寿房六块板,所谓三长两短,是前后两块短挡板,左右帮板和底板三块长板,没有算盖板。我在里面看了好一阵,想选几块做书院的板桌,又觉得不合适,那些板子在赵木匠心里早有了下家,哪几块给哪个人,都定了。做一口寿房多少钱,也都定了。不会有多大出入的。
〔2〕村里的老人或许不知道赵木匠心里定的事。有时哪家儿子看着老父亲气不够,可能活不过冬天,就早早地给赵木匠搁下些定金,让把寿房的料备好,到时候很快能装出来。更多时候是赵木匠自己做主,把他想到的那些老人的寿房都定制了。早晚都是他的活,人家不急他急,他得趁自己有气力时把活先做了,万一几个人凑一起走了,他又没个打下手的,那就麻烦了。
赵木匠心里定了的事,人不知,鬼会觉。棺材铺是鬼聚会的地方。半夜里鬼忙活着抬板子,三长两短盖房子,给每人盖一间,盖到天亮前拆了,板子抬到原处。我不能买老木匠和鬼都动过心思的板子。我看几眼,倒退着出来,临出门弯个腰,算请罪了。
〔3〕我们的大书架和板桌、木桥,原打算请赵木匠做的,问了下工钱,也不贵。但最后请了英格堡乡打工的外地木匠。也是想着赵木匠二十年来只做寿房,他把菜籽沟的门窗、立柜、橱柜、八仙桌还有木车都做完了,一个老木匠时代的活,都叫他干完,我不忍再往他手里递活。另一个就是考虑他下料、掏卯、刨的时候,脑子里可能都想的是打寿房的事,我不能让他把这个活想成那个活。
赵木匠到我们书院串过几次门,他跟我们说着话,眼睛盯着院子里成堆的木头木板,他一定看出这摊木活的工程量。
〔4〕他没问我们要干啥。我也没给他说我们要干啥。赵木匠耳朵背,我怕跟他说不清,我说这个,他听成那个。所以啥都不说。赵木匠是个明白人,他心里一定也清楚,一个木匠一旦干了那个活,也就不合适干别的活了。对木匠来说,干到可以干那个活,就简单了,所有以前学的花样都不用了,心里只有三长两短的尺寸,和选板的厚道。赵木匠是厚道人,我看他备的松木板,一大拃厚,觉得踏实。
我们来菜籽沟的头一年,村里走了三个人,外面来的小车一下摆满村道,仿佛走掉的人都回来了。
冬天的时候我不在村里,方如泉说菜籽沟办了两个葬礼和十几家婚礼,礼钱送了好几千。我交代过,只要村里有宴席,不管婚丧嫁娶,知道了就去随个份子。
〔5〕村委会姚书记说他一年下来随礼要上万。哪家有事情都请他。他都得去。姚书记一点不心疼随了这么多礼。他的儿子这两年就结婚,送出去再多,一把子全捞回来。
村里出去的孩子,在城里安了家,结婚也都回村里操办,老人在村里,养肥的羊喂胖的猪在村里,会做流水席的大厨子在村里。再有,家人大半辈子里给人家随的礼账子也在村里,要不回村里操办酒席,送出去的礼就永远收不回来了。
也是我们到菜籽沟的这一年,英格堡乡出生了两个孩子,我听到这个数字心里一片荒凉,几千人的乡,一年才生了两个孩子,明年也许是一个,后年也许一个孩子都不出生,到那时候,整个英格堡、菜籽沟,只有去的人,没有来的。
醒来
〔6〕在我不曾醒来的早晨,你们挖开渠口,往我半月前浇过的菜地放水,你们低声呵斥月亮别叫,把渠边那根大木头抬到后墙边,又担心我醒来看见木头不见,四处找。你们把地边的草割了,晾干码成垛,在我让老王架起的草棚上,你们又往高垛了半个夏天的干草,你们中的谁爬到垛顶,低声喊月亮太阳,它们俩欢蹦着朝上吠叫,又更低声地似乎正在心里喊我的名字,在连狗都听不见的那声呼喊里,我早年的醒又醒来一次,我看见那时的我,好多个我,从菜地,从果园的浓密绿荫下,从门外的大路,从我一次次睡着的西北间的屋子,从山坡,从和谁的匆忙握别里,朝那个声音处走,步子轻快,眼睛朝上,耳朵侧着,那些走来的身影里有三十岁的我,二十岁、十五岁的我,亦有五十岁、八十岁的我,
〔7〕他们在谁的一声喊唤里来了,一步步往草垛聚拢,在渠边,十五岁的我好奇地看着五十岁的我、八十岁的我像一个孩童,蹦蹦跳跳超过十岁的我,然后,他们到了草垛下面,似乎又摞了好多个夏天的干草,我看见它高入云端,他们也仰头看,又好奇地相互看,那个呼唤声再没有了,草垛上只一个梯子,高晃晃竖立,我认出那是我少年时爬过的梯子,他们也都认出来了,在我的记忆里,那个上房的梯子总是短一截子,下房时一只脚探下来,找梯子,身体害怕地爬在房檐。这个记忆延伸到无数的梦里,他们围着梯子,谁先上去呢,已经站在高高草垛上的又是谁呢,他朝下看,看见我各个年岁里朝上仰望的眼睛,那是他们中间的一双,早早地到了高处,星星一样静静回望。
〔8〕在我不愿醒来的那个早晨,你们收住渠口,地里的菜都已长熟,我最喜欢吃的茄子、西红柿、芹菜长得尤其好,它们从未长得这么好过。在一个又一个早晨的无边长睡里,你们起来摘菜做早饭,喊干活的人吃饭,大声地喊,我寂静地听着。突然地,谁的一声喊到了我,又猛地停住,她意识到自己喊错了,声音已放出去,收不回来,所有人都听见了,都停住,走路的停住脚步,吃饭的停住筷子,太阳月亮也愣住,我喜欢地听着,用我长长一生里所有的耳朵,去追那个散远的声音。
〔9〕我等着谁喊第二声,等她声音再大点喊我一声,等她没有声音地在心里唤我一声,喊第三声,像她习惯喊我的那样,她早已习惯了连喊我三声,我早已习惯了在她的第三声里起身,我等她的第二声,等她喊第三声,她喊了我就起来,出门左拐,到餐厅,到她喊我去的任何地方。
可是没有,她只喊了一声,突然就没声音了,所有人都没声音了,月亮太阳都不叫了,我在那时装糊涂没有起来,没去吃那个早晨的洋芋面条,没去走那个上午的路,没去晒那个下午的太阳。然后,我听见刮风了,满天空的落叶声,一层一层树叶,给大地盖上被子,我暖和地闭上眼睛,想着一百个一千个秋天的金黄落叶会是多么的温暖。
等一只老鼠老死
〔10〕我妈种的甜瓜,熟一个被老鼠掏空一个。去年老鼠还没这么猖獗,甜瓜熟透,我们吃了头一茬,老鼠才下口。可能这地方的老鼠没见过甜瓜,我们让它尝到了甜头。今年老鼠先下口,就没我们吃的了。
“白费劲,都种给老鼠了。”我妈说。
老鼠在层叠的瓜叶下面,一个一个摸瓜,它知道哪个熟了,瓜熟了有香味,皮也变软。我们也是这样判断甜瓜生熟。老鼠早在瓜苗开出黄色小花,结出指头小的瓜娃时,就在旁边的洋芋地里打了洞,等甜瓜长熟。老鼠不吃洋芋,除非饿极了。只有我们甘肃人爱吃洋芋,吃出洋芋的甜。去年给我们盖房子的河南人和四川人都不喜欢吃洋芋,他们爱吃红薯。
〔11〕甜瓜的甜确实连老鼠都喜欢,它吃香甜的瓜瓤,还嗑瓜子。有时老鼠把一个熟了的甜瓜咬开,只是为了嗑里面的瓜子,把整个瓜糟蹋了。我们没办法跟老鼠商量,瓜熟了我们先吃瓤,瓜子留给它们吃。事实上,我们所吃的西瓜甜瓜籽,都扔在外面喂老鼠和鸟了。老鼠明知道我们不吃甜瓜籽,我们只吃瓜瓤,瓜子迟早丢在地上给它吃,它为啥不等一等,非要跟我们过不去,让我们想方设法灭它呢。
瓜糟践完就轮到葵花苞米。秋天收葵花时才发现,那片低垂的葵花头几乎没籽了,老鼠老早已顺着葵花秆爬上来,一粒一粒偷光了葵花子。我提着镰刀在葵花地里找老鼠漏吃的葵花,一个个地掀开葵花头,下面都是空的,像一张张没表情的脸。
〔12〕我们种的葵花一人多高,老鼠得爬上爬下,每次嘴里叼一个葵花子,得多久才能把脸盆大的一盘葵花子盗完,又多久才能把一地葵花子盗走。老鼠也许不用爬上爬下,它用牙咬下一颗,头一歪扔下来,下面有老鼠往洞里搬运。老鼠甚至不用下去,沿那些勾肩搭背的阔大叶子,从一棵转移到另一棵,挑拣着把籽粒饱满的葵花头盗空,把没长好的留给我们。
最惨的是玉米,老鼠爬上高高的玉米秆,把每个玉米棒子上头啃一顿。我妈说,老鼠啃过的,我们就不能吃了,只有粉碎了喂鸡。
〔13〕老鼠赶在入冬之前,把地里能吃的吃了,吃不了的也啃一口糟蹋掉,把能运走的搬进洞。我们收拾老鼠剩下的,洋芋挖了进菜窖,瓜秧割了堆地边,豆角和西红柿架收起来,码整齐,明年再用。不时在地里遇见几只老鼠,又肥又大,想一锨拍死,又想想算了。老鼠在洞里储足了粮食,或许就不进屋里扰我们。冬天院子里寂静,雪地上一行行的老鼠脚印,让人欣喜呢。老鼠在大冬天走亲戚,一窝和另一窝,隔着几道埂子的茫茫白雪,大老鼠领着小的,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细如针线的路。
〔14〕那时节村里人一半进城过冬,一宅宅院子空在沟里。留下的人喂羊养猪,各扫门前雪,时有亲戚上门,吃喝一顿。
还是有一只老鼠进屋了,把我们住的屋子当成家。它在屋顶的夹层里啃保温板,掉下一堆白色颗粒。在书架上蹿上蹿下,偶尔在某一本书上留下咬痕和尿迹。钻进我写废的宣纸堆,弄出一阵纸的声音,和我白天折宣纸时弄出的声音一样。爬上我插干花的陶瓷酒瓶,不小心翻倒花瓶。还吱吱吱叫。屋里就我和它,如果它不是叫给我听,便是自言自语了。它应该知道屋里有一个人在听它叫,它满屋子走动,用这些响动告诉我这个屋子是它的吗?
〔15〕最难忍的是它晚上咬炕头的大木头磨牙,大炕用一根直径半米的大木头做炕沿,木头原是人家老房子拆下的横梁,表皮油黄发亮,似乎那家人百年日子的味道,都渗在木头里。炕面是木板,贴墙顶天立地一架书。书架的圆木也是老房子拆下的料。当初用木板一块块地封住炕面时,我就想到了这个空洞的大炕底下,肯定是老鼠的家了。
老鼠不早不晚,等到我睡下,屋子安静了开始咬木头,咯吱咯吱的声音响在枕头底下。它在咬炕沿的老木头磨牙。我咳嗽一声,它不理睬。我用拳头砸几下床板,它停住,头一挨枕头它又开始咬。我在它咬木头磨牙的声音里睡着,有时半夜醒来,听见它在地上走,脚步声轻一下重一下。
〔16〕我从厨房带两个土豆过来,在炉子里烧一个吃了。第二天,剩下的那个土豆不见了。一锅拳头大的土豆,它怎么搬走的,又藏在了哪里。
一次我们离开半个月,它把屋里能吃的都搬走吃了,或藏了起来。客人带来的两包小袋装的鹰嘴豆,它从一个角上咬烂外包装袋,把小袋装鹰嘴豆全搬空。我在炕边的洞口处,看见一堆吃空的小塑料袋。它可能真的饿坏了,我放在书架上作为插花的一大束麦子,全被它掐了穗头。连插在花瓶的一大把干野花都没放过,有籽的花秆都咬断。一篮子苹果吃得一个不剩。
〔17〕留下过年吃的一个大甜瓜,被它从一头咬开一个洞,又从另一端开洞出去。我侧头看它咬穿的甜瓜里面,散扔着瓜子皮,瓜瓤依然新鲜黄亮,本来留着自己吃的甜瓜,让这只老鼠品尝了。
厨师王嫂说,他们家灭老鼠,一是投药,二是放夹牢,三是布电线。
我们院子不投药,有猫有鸡有狗。况且,凡是跟药沾边的我们都不用,村里人打农药、除草剂、上化肥,我们全不用。
夹牢买来一个,铁丝编的方笼子,诱饵挂里面,老鼠触动诱饵,出口会“啪”地关住。
〔18〕当晚在诱饵钩上挂了半个香梨,老鼠爱吃香梨,上次回家留在书房的半箱子梨都让老鼠吃了。结果老鼠果真进了笼子,咬梨吃,触动机关,铁笼子“啪”地关住。我们睡着了没听见笼子关闭的声音。可能没关死,老鼠硬是挤一个缝逃了,把几缕灰色的鼠毛挂在铁丝上。接下来的几天几夜,诱饵依旧是香梨,夜里老鼠依旧在床板下啃木头磨牙,就是再也不进笼子了。
我想菜籽沟的老鼠被各种各样的夹牢灭了几十年,早认下这个东西,知道它的厉害了。为了迷糊老鼠,我把那个黑铁丝笼子拿白纸包住,诱饵放在里面,老鼠记住的也许是那个黑色的方笼子,现在笼子变成白色的,它就不觉得危险。可是,老鼠不上当。
〔19〕我把夹牢移到隔壁房子,想这只老鼠没夹住不进笼子了,别的老鼠会进。结果呢,换了几个房子,还在常有老鼠偷出没的鸡圈放了几天,笼子里做诱饵的香梨都干了,没一只老鼠上钩,好像书院所有的老鼠都知道这是夹老鼠的夹牢,都绕着走了。
夹牢没用,五十块钱买来电灭鼠器,一个简易的盒子,我研究半天没敢用,那个电灭鼠器太玄乎,它直接将铁丝接上电源,拉在地面十公分高处,铁丝上吊诱饵,老鼠看到诱饵会立起身去吃,或将前爪搭到铁丝上,只要一挨铁丝,立即电死。
我问王嫂,他们家的电灭鼠器打死的老鼠多吗。
〔20〕打死好几个。王嫂说。就是操心得很,人不小心挨上也会电死。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堵住墙根能看见的所有朝外的洞,不让其他老鼠再进屋。这只自然也跑不出去。我只忍受一只老鼠闹腾。我想,老鼠的寿命也就两三年,这只老鼠有两岁了吧,我会等它老死。去年冬天它啃木头的声音好像更有劲,我们忍过来了。春天正在临近,夜晚屋子里没以前冷了,它啃木头的声音也变得迟钝,随着它进入老年,也许会越来越安静,不去啃木头磨牙,它的牙也许在开春前就会全掉了。他会不会变得老眼昏花,分不清白天黑夜,会不会糊涂得再不躲避人,步履蹒跚在地上走。如果他真的那样,我们怎么办?我是说,如果那只老了的老鼠,真的再不惧怕我们,跑到眼前,我们该如何下手去灭了他。
〔21〕这真是件麻烦的事情。
在它老死之前,我们和它共居一室的日子,好像仍然没有边。我已经习惯了它咀嚼木头磨牙的声音,习惯了它留下的一屋子老鼠味儿。每次回到书院,金子都先打开所有门窗,把老鼠味道放出去。我甚至在夜里听不见它磨牙的声音了,是它不再磨牙,还是我的耳朵聋了再听不见。要说衰老,或许我熬不过一只老鼠呢。在它咯吱磨牙的夜晚我的牙齿在松动,我的瞌睡越来越多,我在难以醒来的梦中长出更多皱纹。还有,在我逐渐失聪的耳朵里,这个村庄的声音在悄悄走远,包括一只老鼠的烦人响动。
〔22〕终于,我们和一只老鼠一起熬到春天,院子里的厚厚积雪已经融化,冬天完全撤走了,把去年的果园、菜地、林间小路都还给我们。金子打开前后门窗,在明媚的阳光里,要把一冬天的阴气和老鼠味道全放出去。
这时,我看见那只和我们折腾了两个冬天少有谋面的大老鼠,摇摇晃晃走出来了。它迟钝地迈着步子,往敞开门的光线里走。
我喊金子,喊方如泉,喊王嫂,喊烧锅炉的老爷子。
〔23〕大家全围过来,看着一只大灰老鼠,颤巍巍走出门,它显然不是因为害怕而颤抖,它老了。它费劲地翻过门槛,下台阶时摔了一跤,缓慢爬起来,走到春天暖暖的太阳光里。它可是一个冬天都没见到太阳,好像晕了,朝我脚边跌撞过来,我赶紧躲开。我被它的老态吓住了。在我们讨论着要不要打死它的说话声里,它不慌不忙,朝有鸟叫和水声的院墙边走去。它或许记得两年前走进这个院子的路,那里有一个排水洞,通到院墙外的小河沟,翻过河沟,过马路上坡,就是年年人种老鼠收的旱地麦田,那是它过夏天和秋天的最好地方了。
两只老鼠的半个冬天
〔24〕靠门口的墙角斜立着两个铁皮烟囱,下面三个尿素口袋,一个装扁豆,两个空着。它每晚在那里折腾,钻进空袋子里上蹿下跳,弄出哗哗啦啦的响声,也不怕我过去封住口袋捉住。它还钻进斜立的铁皮筒子,往上爬,爬到顶端呼啦啦滑下来。
我在夜里睡得安稳,听不见它弄出的声响。只有在睡前,它知道我们上床睡了,地上一旦没有人的脚步声,它胆子就大起来,一次次地在那个铁皮筒子里爬上溜下,爪子抓铁皮的声音吱吱啦啦。
〔25〕我们忍受着它的闹腾,逐渐地对那个声音习以为常,房间没有电视,只有炉火呼呼地燃烧,更多时候听不见,火静悄悄地把煤燃完,剩下一点点的白灰。木垒的煤是我用过最好的,耐烧,一晚上填两次,烧到天亮,屋里始终暖和,早晨打开炉圈,炉膛里最大的那块煤剩下一块紫红火炭,那是再续新煤的火种。
它们不是一只。是两只。另一只稍小点儿,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也许一直在洞里,刚长出毛,会走几步了,哥哥领着弟弟出来玩。在我夜晚的长梦里,它们一个跟一个,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听见我的呼噜声也不害怕,听见我说梦话时会警觉地停住。
〔26〕只是唯一听见我梦话的小老鼠耳朵,从来不知道我说什么,我也从来不知道自己在梦中说了什么,那么多的梦遗忘在长夜里。
后来我发现它们俩长得不像,不是一窝的。或许是它从外面领回来一只。在我们敞开门透风的大中午,它被外面亮晃晃的阳光吸引,也溜出晒太阳,正好碰到一只雪地上流浪的小老鼠,就领了回来。它领一只老鼠进门也不问问我们愿不愿意。这个屋子的事,它竟然一口做主了。下雪前我看见好几只乱窜的老鼠,它们着急了,大雪覆盖了地面,老鼠就只有靠洞里储藏的粮食过冬。
〔27〕当然,实在没吃的了,也可以钻在雪下觅食,那样就很费劲了,不见得刨一个雪洞过去,就正好对上一粒秋收遗漏的包谷。也许刨一天洞,累个半死,还没吃到一口呢,在冬天看似白茫茫的厚雪底下,散布着老鼠觅食的洞,它们偶尔从雪下面探出头,看看自己走到哪了,那个探头的小洞就留在雪地上,到春天雪会从这个冒着热气的小洞口开始融化,整个大地上的春天,有一只小老鼠的微小温暖。
〔28〕如果雪底下再也找不到吃的,老鼠就往人家里跑,老鼠进人家的方式有几种,一是在门口蹲守,趁人进出门时窜进来,先在哪个隐蔽处藏着,待没有人声时沿墙根搜索一圈,再在桌子柜子床下面搜一圈,最主要是找到厨房,看有无以前老鼠打的洞,有了最好,没有就选个墙角挖。二是从外墙根挖一个洞进来。我们早知道老鼠的这些把戏,入冬前屋里屋外的老鼠洞口都用水泥封住,进屋前看看身后是否跟着一只老鼠。我们可以接受一两只老鼠,但无法和一群老鼠在一个屋里生活。老鼠一多胆子就大,敢上床,往被窝里钻,往脸上爬。
〔29〕果园后面的坡地上有十几个碗口大的老鼠洞,我不太清楚这些老鼠洞每个是一家呢,还是一个大家族的许多个门洞,或许在地下它们洞洞串通。要是在早年,我会拿铁锨挖开看看,探个究竟。这样的探究,在年少时干了也就干了。好多事情一错过时间,就再不会去做。现在这些老鼠洞都是我们家院子的,老鼠或许不知道我是这个院子的主人,但我每天背个手走过果园时,它一定知道院子里住进来另一个人。
那两只小老鼠呢?有一天小黄狗太阳进屋来,闻见老鼠味道,三两下撵出小的那只,太阳像猫一般大,老鼠在床下躲不了,窜出门,太阳跟着追出去,我赶紧关门。剩下就是狗和老鼠的事。我真不喜欢有两只老鼠在屋里。
〔30〕又一天我出去提煤,回来见太阳嘴里叼着一只老鼠,半个身子和尾巴在外扭动,赶紧喊一声,老鼠掉地上,已经半死,太阳抬眼看我,又看地上蠕动的小老鼠。我叹了口气,进屋关住门。外面的世界成了一只狗和一只老鼠的。我不想再管它们的事。炉子里的火快灭了,我得赶紧把煤续上。我拿火钩子掀开炉盖,往里倒煤,全是铁的声音,待一切做好,我坐在炉边,屋子里空荡安静,一点声响没有了。我看墙角,又看床下、铁皮筒、尿素口袋、葵花头、床腿,都空荡安静,再不发出一丝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