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人生》
图文来源于网络,仅限习读,如侵联删。
本文配乐是首歌曲,分享给大家,可以按个人喜好选择性播放,也可以自配舒缓的曲子诵读。
【Deep East Music - Bygone Bumps (昔日的颠簸)】
【Raphaël Beau - Micmacs à la gare】
【Richard Clayderman - Greensleeves (绿袖子)】
【林海 - 欢沁】
【纯音乐 - 所念皆星河 (钢琴版)】
【龙舟 - 千与千寻 (与你同在)(陶笛版)】
【樹莓蛋奶酥 - ふわふわ♪ / 轻飘飘♪(翻自 牧野由依)】
【吴金黛 - 森林狂想曲】
【羽肿 - Windy Hill (风之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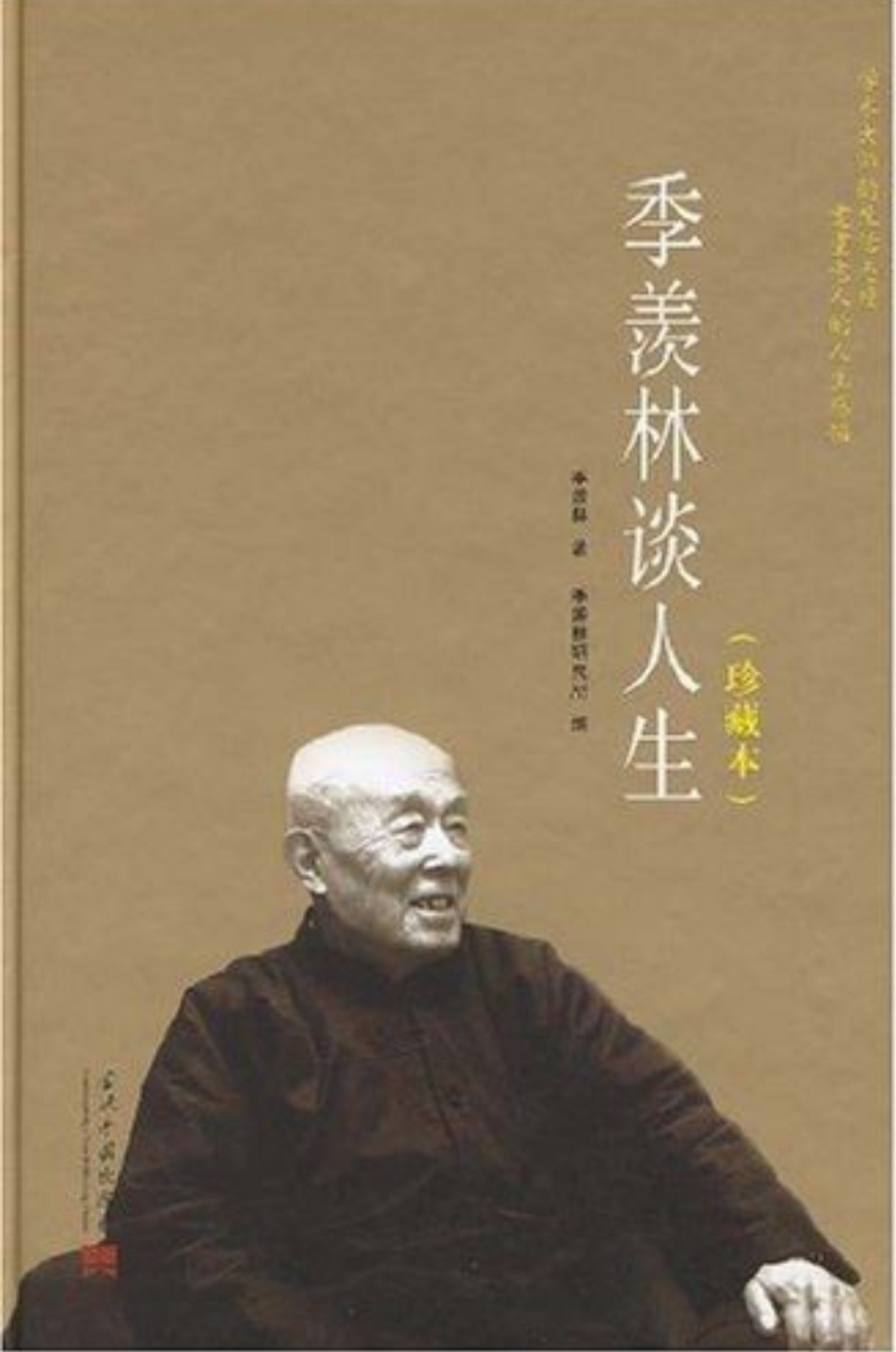
关于作者
季羡林,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屯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糖史等。
关于本书
本书是季羡林晚年的散文随笔代表作。学术大家季羡林先生结合九十多年的生活体验,谈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缘分与命运、做人与处世、容忍、成功、知足、朋友、毁誉、压力、长寿之道、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感悟。
核心内容
本书思想核心是: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而是20世纪世界东方学的重镇、印度古学研究的巨擘、梵典翻译的大师、中西交通史的大家。他也想来不追求做“完人”,一直在坦诚地向世界袒露自己真实的思想和人生。在他的98岁人生旁边,开出来了一列什么样的感悟清单。没什么高深道理,只是他奉行的准则:人生的起点肯定不一样,然而多知道一些,就能多自由一些。我们总是要穿过糊涂才能逐渐明白:生活的意义,就是完成这一代人该负担的责任。要做事,就要追求彻底的认真和真实。在其中去确立“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我”的关系。与人相处,真情和忍耐之外,要“反求诸己”,想想换成自己,能不能好到哪里去?季羡林谈古印度语言,我们听不太明白,但他说人生时,我们都懂。然而,这些道理要认真彻底去做才行。
前言
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季羡林谈人生》。这本书很薄,是季羡林晚年的散文集。不过,我下面要为你讲的内容,还包括了季羡林全集前几卷的日记和回忆录,摞起来是很厚的几大本。目的只有一个:为你讲讲我读到的季羡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只看他在这本书里对人生的感悟,不太容易知道:这些话是从何而来,又指的是什么?
有人说“名气是所有误解的总和”,这句话用在季羡林身上很合适。在我看来,公众对他的评价,基本上都是错的。
有人说他是国学大师,是大儒。这就是错的,季羡林是学问大家不假,但专业不是中国古代学术。他是国际知名的东方学者,也就是研究印度学、梵语语言学的,这是很冷僻的学科。他早年也是学外国文学、写散文小说起家的,从来不在国学或者新儒家的圈子里。他和另一位著名的东方学者,我为你解读过的《书读完了》的作者金克木不一样,金克木是擅长自学的通人,横跨多个学科,让人眼花缭乱;而季羡林是专精于自己的领域,他的学术成果众多,但都从古印度语言里生发而来,内力深沉精纯。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金克木像黄药师,季羡林像洪七公。季羡林全集有30卷,几千万字,我这次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前8卷。后面大多是学术著作,看不太懂了。
还有人说:季羡林是位公共知识分子。这也不准确,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研究学问。对于知识分子该不该介入社会活动,他一直很困惑,提醒后辈要讲“学术良心”,也就是要严谨治学,守住学者的本分。到晚年,他才逐渐谈人生和社会话题,但也不是公共视角,而是从个人回忆出发,说的既直白又恳切,几乎不套用理论。
至于“国宝”、“泰斗”之类的称呼,季羡林曾经严肃地要求社会为他摘掉这些帽子,还自己“一个自由身”。他本来一直过着冷清的书斋生活,在晚年才突然受到热捧,自嘲说“近年来季羡林走俏”,是“被‘打’成了学术泰斗”。这也没办法,在全社会渴望文化大师的时候,老一辈名家里,只有他硕果仅存,学界地位又高,还当过北大副校长。2009年,98岁的季羡林去世,是一个轰动性新闻,他的学生遗憾地说:整个告别仪式人潮汹涌,像是赶庙会,毫无肃穆可言。
那么,最适合的季羡林的标签是什么呢?说名气来自误解,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用标签来理解别人、定义别人了。下面,我试着用季羡林最推崇的彻底真实态度,给你讲讲他的一生,请你自己体验完整的季羡林。
我把这些内容整理成了一份他的人生清单:左边一列内容,来自他的日记和回忆录。右边一列,大部分是他晚年随笔杂文里做的回顾和反思。如果给这份清单取个名字,可以借用他另一本散文集的书名《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他在九十岁时还是说:“什么叫人生?我不清楚。我看芸芸众生中,也没有哪个人真清楚。我们的诞生都是被动的。”生的对立面,并不只有死,还有别人的生。当生命互为镜像,可以映射无尽深度。这也是我为你讲这本书的目标:在季羡林的心灵历程里,照出我们自己的样子。
第一部分
我讲到这本书里的散文时,就要结合季羡林的自传了。他的自传也是好文章,他有个当之无愧的头衔:当代中国散文大家。大学者都是有性情、有人文关怀的,何况季羡林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发表散文,前后写了八十年,一共两百多万字,形成了自己的文体风格。这些文章,可以说是学问在人生中的延展。
在我们这份清单的第一行,当然是季羡林的家庭和童年。我们来看他怎么形容:“我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的一个小村庄。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说得好像他家是全国最穷的。
其实他家也暴发过,他叔叔中过一次彩票,得了几千两银子。他父亲为耀武扬威,要盖全村最大的砖房,买不到砖,就扬言谁家愿意拆自家房的砖卖给他,他出几十倍的高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兄弟俩的这口恶气倒是出了,但我们也看出他们的做事风格了。于是,到季羡林出生时,家里又重返全村最穷的赤贫,一年只能吃到一两次白面。
季羡林是整个家族唯一的男孩,为了将来光大季家门楣,他六岁就离家,被叔叔接到济南去读书。他的成绩一直很好,考进了全省闻名的山大附中,校长是前清状元、有名的书法家王寿彭。这位状元可能从科举获得了灵感,规定:各班级的甲等第一名、各科成绩都在九十五分以上的,要给予额外褒奖。全校只有季羡林达标。那个额外奖励就是王寿彰写的几幅字和扇面,称他为“羡林老弟”。季羡林说,自己的整个高中时代,都为了维持这个虚荣而苦学,连续拿了六个学期第一。
他当时并没有想过深造,家里给他的规划是:报考邮政局,拿一个“铁饭碗”,熬上二十年,当个小官员。他是因为没有通过那次面试,才报考了大学,一下就被清华和北大同时录取了。季羡林说:我不是想当什么学者。只是因为想上大学“镀金”,容易抢到一只饭碗。
这一段故事,给我们一种启示:季羡林是天生的读书种子,这不用说。但他早年的一切都是由家里决定,是完全被动的。我们经常谈论孩子的起跑线,天资和意志力,可以说是第一道起跑线。人生而不平等,从这里就决定了。季羡林在这方面是一等一的。
至于家长的视野,那就是第二道起跑线了。我们可以拿季羡林和钱锺书作个比较,因为有的可比:他俩年纪相仿,前后入学清华外文系。季羡林说:“我们系能出钱锺书、曹禺这样的大师,当然不是一无是处。”钱锺书出身学问世家,父亲钱基博也是著名学者,写过《现代中国文学史》,做过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的中文系教授。钱锺书入校时,不光才学过人,而且对学术界有通盘了解,对自己的学者生涯也早有规划。这样的条件,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而季羡林是标准的寒门学子。他此后的道路,早就超出了家里的想象,眼前只有一片漆黑。这在表面上是信息的不同,实际上的区别是:他俩走上学者道路,有着必然和偶然之分;后来,也有自由程度的不同。以后我会选本合适的书,为你说说钱锺书和杨绛夫妇。他们相对季羡林这些同时代学者,总是显得从容自如,就是因为一直拥有更开阔的视野,选择多了一些。我后面还会再说到:早年的环境,影响到了季羡林的个人生活。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季羡林的第二行人生清单:他的大学生涯。我说他入校时眼前漆黑,不是不尊敬老先生。他有本当年的《清华园日记》就讲到,自己当时没有明确志向,还稀里糊涂地想去读数学系。他有一点很可敬,就是不遮掩自己。有人建议他,作为德高望重的名人,出版这本日记时最好删去一些不雅的话,像“(今天)去看清华对附中女子篮球赛。说实在的,看女人打篮球,其实不是去看篮球,是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季羡林不同意,说自己就是如此,为什么不让人知道?他回忆自己的师长,也是同样的态度,说“中国古话: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道理我不是不懂。但为了真理,我不能用撒谎来讳。”
季羡林大学主修德文,但他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两门课是: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和中文系教授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他回忆:陈先生上课,任何废话都不说,先在黑板上抄写资料,抄得满满的,然后根据所抄的进行讲解分析,对那些一般人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崭新的见解,令学生觉得石破天惊。这种风范,对他产生了一辈子的影响。
大学时代,季羡林经历了两件人生大事。其一是母亲突然去世。他从小有个心愿,是将来赚钱以后,让母亲吃上白面,从此成了泡影。另一件事是作为家族单传的男丁,很早就成了亲,生儿育女,妻子比他大四岁。季羡林虽然没有推翻这段父母之命的婚姻,但也没怎么在家里呆过。他儿子季承说:“我刚出生3个月,他就去了德国。回国时,我都12岁了。他和我母亲的关系,等于是一直分居到死。他的内心当然很丰富,但对这个家庭没有感情。”季承认为:父亲从小寄居叔父家、婚姻中没有爱情等等原因,塑造出一种压抑、封闭而又孤傲的性格。当然,要我看,这是家务事中的一面之词,这种婚姻状况,也是那个年代的常见现象。季羡林能坚持到底,已经算相当正派了。提这一段是因为,季羡林父子间的纠纷,曾是很有名的公案。
季羡林直到晚年一在追悔说:“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对于个人家庭问题,他觉得:爱情是人生特定阶段的事,不值得花太多时间,更不能为此牺牲事业。总之,为追求学问,他在情感和家庭上,有无法弥合的伤痛和残缺。
在他的这行经历中,右面那栏“人生感悟”该填点儿什么呢?我觉得可以这么总结:人生总是要从糊涂、从朦胧里求明白。季羡林青年时代的日记,特别爱用一个词:“一塌糊涂”,既形容别人也形容自己。他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只不过是在昏昏沉沉地追求一点儿享受,没想过自己为什么活。他是从被动到一塌糊涂,然后才在这本书里得出一个道理:人类的前途,在于朝一个共同理想努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要完成。这像一条链子,每个环节本身微不足道,但这一点儿东西影响了整个链条。如果人生有意义,那就是这种对人类承前启后的责任感;如果人生有价值,那就是去完成自己这一代的任务。
这个观念,在季羡林留学前还没有成型。他当时只是不愿意放弃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的机会。家族对他的支持,是觉得这是中了“洋进士”,将来更能“大发特发”。于是,他留下了经济濒临破产的家,在1935年8月、24岁时远渡重洋,前往德国。原计划是留学两年,但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十年。
我们再来看他这第三行人生清单。季羡林进的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哥廷根大学,大数学家高斯曾经是这里的教授。这时,季羡林已经熟悉了学术圈的规则,想在两年里拿到德国的博士,基本上不可能。唯一的取巧办法,是用中国题目作论文。但季羡林的性格,真像他儿子所说,既孤傲又倔强。他说,“我立下大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讲庄子、老子这些中国学问谋得博士头衔,让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康德、黑格尔,我不步他们的后尘。”
季羡林还说:我为什么非要一个博士学位呢?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都没有博士头衔。可他们是天才,用不着学位。我不是这种人,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就会在抢夺饭碗的搏斗里失败。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写这段回忆时,季羡林早就被公众称为“大师”、“国宝”了,但还是有一说一。贫穷的记忆和家庭影响,让他在当时日记里,总是为饭碗问题惴惴不安。
但为了这个博士的含金量,他还是选了最难的梵文和巴利文,整个班上,起初就他一个学生,后来和其他年级合并,跟到最后的,还是只有他一个。梵文到底有多难啊?季羡林当年写道:“梵文真是鬼造的!文法变化极复杂,最要命的是例外,每条规则都有例外,例外之内还有例外,把人弄得如入五里雾中。左看右看,终于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断开一个字,自己断开了,字典上也找不到。恨不能把书撕成粉碎。”他为此患上了失眠,几天几夜不能合眼,骨瘦如柴,你猜他的对策是什么?他写的是:“除了工作,还能作什么?我反正拼上了,你失你的眠,我偏工作。”他选的其他辅修课,也是吐火罗文、阿拉伯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这些小语种文学,季羡林一共精通十几种语言。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一部印度典籍里的动词变化。毕业以后,他留在哥廷根担任教员,听说他要回国,导师难过不已。
为什么他在德国要呆十年呢?咱们算一下时间就知道了:他赶上了二战,交通断绝,回不来了。季羡林说,童年自己只是吃糠咽菜,还能吃饱,真挨饿是在那个“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德国,这留下个病根:回国后的很多年,无论吃多少,他都感觉不出饱来。
十年的德国生活,留给季羡林一个行为准则:追求彻底的认真和真实。他认为:德国人能在短短一两百年里造就惊人的文化,是因为奉行一丝不苟和专注。有个著名的医学专家,面试学生时,拿出一副猪肝,问这是什么。学生看出来也不敢说啊。教授就给了个不及格,说:“医学工作者一定要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还当什么医生?”哥廷根遭到轰炸时,季羡林看到一个流体力学教授站在操场上,观察炸弹爆炸的气流是怎样摧毁墙壁的,自言自语说:“真是难得!我的试验室装配不起来这样的效果。”
季羡林也看到了德国人的另一面:他们在战争前期陷入了集体迷狂,政治判断力很低。二战期间,几乎没人质疑法西斯,都显得忘乎所以,洋洋自得。每隔半年,报纸和电台就说:某个邻国正在迫害德国人,于是全国沸腾,他们把出兵占领外国叫做“抵抗”。逐渐,大学里只有女生和前线下来的伤兵,教学楼的走廊上,终日回荡着双拐触地的清脆声响。几年后,这个天才辈出的民族,一夜之间沦为了战败国。
季羡林被大家误会成国学大师,也有个原因:他在晚年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大意是:西方文化在现代出了问题;世界的未来,应该被“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主导。我打算为你说完季羡林这个人之后,再为你解读一本他的东西文化比较。批评者认为,他的观点是出于民族情感,论据不足。我们看他这段经历就知道:不完全是。他亲历了德国的二战,对西方文化有自己的批判。他的道理,值得听一听。
第二部分
季羡林在晚年总结,人生问题不过是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天人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如何平衡思想情感矛盾的自我关系。
1945年8月,季羡林34岁时,从德国回到了北京。这是我们为他划分的第四行人生清单。他当时的想法是不考虑那么多的关系,专注地施展自己的学术抱负。当时北大有个规矩,回国的留学生,无论学历和经历如何,最高只能定副教授。而季羡林创下了最快升任正教授的记录,同时还兼任东方语言系系主任。
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校长胡适非常赏识他。胡适到了台湾时还说:“做学问就该像北大的季羡林。”胡适向来关注佛教思想史,那几年在和辅仁大学校长、宗教史学家陈垣争论一个考据问题:浮屠这个词——就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那个浮屠,母语是什么?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涉及到一部佛经的真伪。他们的争论依据都是中国古代文献,季羡林写了一篇论文,直接从梵文、吐火罗文等古印度文献里考证出:汉语里是先有“浮屠”这个词,这是印度古代的方言;之后才有“佛”这个词,它起源于吐火罗文。季羡林从中推断出:佛教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到中国,而是由中亚间接传来的。我们知道,这个结论太重要了。
从五十年代起,胡适和陈寅恪被大批判。季羡林是当时国内少数能保持沉默,守住学术底线的学者。那也是他人生里的一段苦难时期。对于这段时期,季羡林有一本《牛棚日记》,非常有名,我就不多介绍了。他在老年时说:自己在57岁的冬天之后,每一天都是多活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那时候,他差一点儿自杀。他事先也是用德国培养起来的严谨态度推理了这件事,他说:原以为离自己很远很远的事,现在出现在眼前。我平静地、清醒地、科学地考虑实现这个决定的手段和步骤,我想得很细致、很周到、很全面。就在他准备夜里翻墙出校门,到圆明园去吞安眠药时,却意外地因为有人觉得他态度不好,被拉去参加批斗了。他说,那晚的经历,让他毕生难忘。
这本书里,他回忆那段经历时,有点儿黑色幽默。说“我是因为态度坏,才捡了一条命”。之后的几年,他成了校园里人人见到都绕着走的人,有个女同事帮他推过一次车,让他感动得热泪盈眶,终生难忘。他后来被平反、任命为副校长时,没有对谁实施过报复,在这本书里,他分析自己的心理历程时说:我是倾向“人性本恶”的,我也知道坏人不会改好。但我能原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是我度量大,是由于我反思:假如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的行动也不见得比别人好。人从本能上说,就是趋吉避凶的。他引《孟子》的话,说这是“反求诸己”。我理解,这不只是对他人宽容,也是在反思中解脱,不让仇恨绑架自己,更不让报复心耽误自己的学术研究。
季羡林不刻意追求长寿,他晚年的养生之道是“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不嘀咕”就是不过度关注健康,不纠结生死问题,他最喜欢陶渊明谈论生死的几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八十岁以后,他每天清早四点起床工作,连续完成了《糖史》等几部开创性学术大作。
于是,我们在晚年这最后一行人生清单里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季羡林:他的生活像清教徒一样简单,到老还穿着从德国带回来的雨衣,在被年轻人夸时髦时,他才发现,原来时尚潮流是五十年一轮回。他在校园里走,被新生误认为是老校工,让他照看行李,他也微笑着答应。他表面上安静严肃,内心却是滚烫的。他总结自己喜欢的性格是:“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在一个‘真’字,要做性情中人”。
对于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我这三个关系,他完成了最后的思考。他说,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没有一样的,也捏不到一块儿去。重点不在理论,而在于去做,用自己的思想去包容人情世事。他自己的三条回答,都是平常话:对于人和自然:人要把自然看成伙伴,征服的姿态一定会有恶果。对于人和人:尊重社会的准则秩序,对善良之人报以真情和忍耐。对于自己:努力去除情感中的杂念。他在90岁时说:我是个呆板保守的人,工作就是爬格子。我只能保证我写出来的东西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之后,能让人爱国,爱家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我活得太累了,但休息是不可能的,只能向前走,向前走……
总结
那么,我们最后来一起看看,在季羡林的98岁人生旁边,开出来了一列什么样的感悟清单。确实没什么高深道理,只是他奉行的准则:人生的起点肯定不一样,然而多知道一些,就能多自由一些。我们总是要穿过糊涂才能逐渐明白:生活的意义,就是完成这一代人该负担的责任。要做事,就要追求彻底的认真和真实。在其中去确立“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我”的关系。与人相处,真情和忍耐之外,要“反求诸己”,想想换成自己,能不能好到哪里去?季羡林谈古印度语言,我们听不太明白,但他说人生时,我们都懂。然而,这些道理要认真彻底去做才行。说了这么多,对于该怎么评价他,你一定有了自己的答案。
季羡林说,如果真有个人,人人都说他好,此人一定是极端圆滑的人。他拒绝了社会给他的美誉,除了性格朴实、较真,也是种智慧。追逐虚名的人,大概没怎么想过:德不配位,名过其实,实在也是灾难。人的才德和社会地位之间,需要大致平衡。名誉地位太低,容易变得愤世嫉俗,性格乖张。但太高,且不说会成为众矢之的,心理也会逐渐变得既极度自大又极度自卑,越来越不正常。一般来说,社会地位稍低于真才实学,个人欲望低于实际能力,是最适合保持自在平和的。人们觉得谦虚和低调是明智之举,原因就在这里。说起来,又何必追求不了解自己的人来夸自己呢?他们也夸不到点儿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