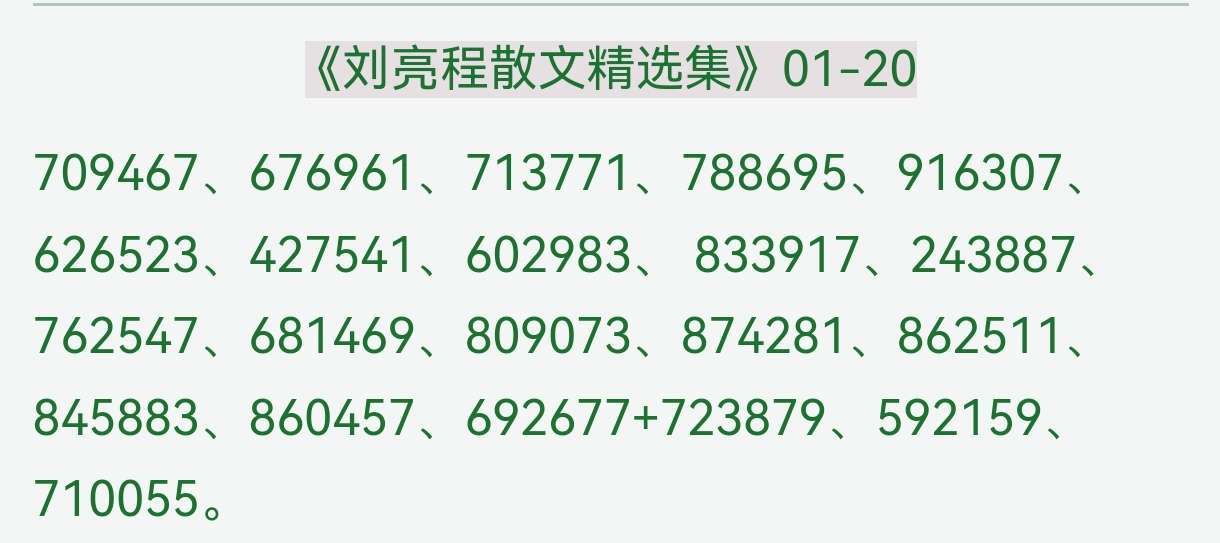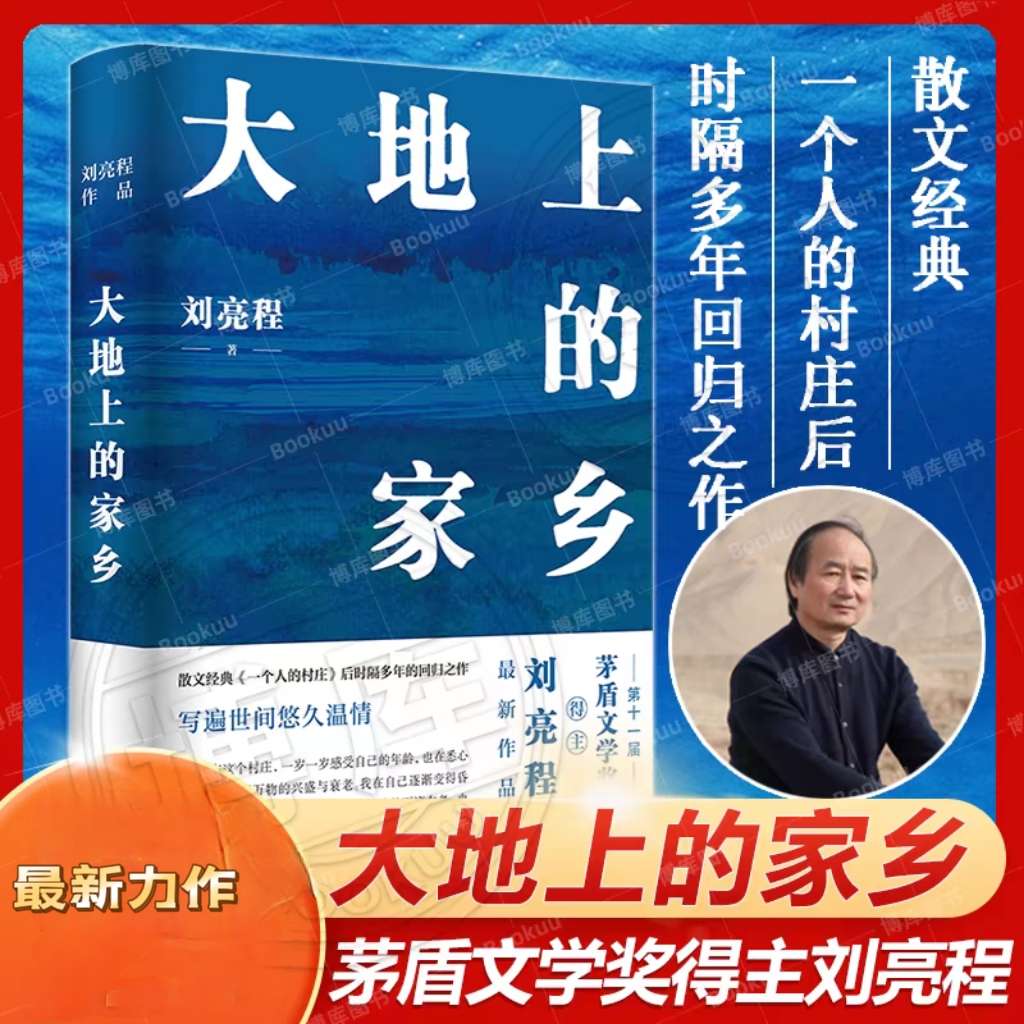
椰落
〔1〕椰树不是树,是大草。十年前我第一次来海南时,一位朋友告诉我。我也一直把椰树当草。相信这里的雨水和阳光,会让一棵草疯长成树一样。
她确实像草,独独一个秆,不分叉。长着草的脸和腰身,一丛一丛,树干是实的,却没有木质。我仔细看过一根腐朽的椰木桩,锯开的断面纹理清晰,年轮间多余的东西朽去,剩下一圈一圈的树皮。她从里到外都是皮,一层层紧卷起来,没有木心,心也是皮。这个奇怪植物,把自己的皮一层层卷成内心,皮的皱褶在里面熨平,纹路理顺。然后,就放心去生去死。死了也闲不住,做梁做柱,结结实实让人用几年、几十年。
〔2〕然后呢,她的心变虚,但还没完,人把树皮剥开,里面是一卷崭新麻布,一层层叠得好好的,剥开一层,下一层更新更细密,剥到最后,剩一溜布丝儿。
在海边宾馆的椰林里,我看见一棵年老的椰木,歪斜身体,靠在另一棵年轻椰木上,她本会倒下去慢慢朽掉的,却被拦腰扶住,扶她的椰木显然不够强壮,受不住,压歪身体。我不知道她能支撑多久。我坐树下仰脸看。一棵老年椰木,靠在一棵年轻椰木上,年轻的走不开,或许她有腿也不会走开,她强撑着。我不知该咋办,看见一棵椰树的累,也帮不上忙。
〔3〕椰树跟我见过的所有树都不一样,她活简单了,几片粗糙叶子长在头顶,显眼的几棵果挂在脖颈。像个往天上背水的人。她的水葫芦紧封密闭,高高举起,不让人触及。一年一趟,她把水背往高处。仿佛她的家在天上。又仿佛她将天上的水背回人间,她个子高,弯不了身,得人从她怀里取。我见过爬树收椰子的妇女,瘦丽如椰,几下爬到树梢上,拿弯镰“咔嚓”一下,椰子落下来。我听见椰子落地的声音,像一个孩子从树上跳下来。
〔4〕那晚在宾馆睡至半夜,听见窗外“腾”的一声,接着又是“腾腾”几声,我知道落椰了。当地人讲,椰子在人入睡的夜里落,在人离开的空林子里落,从不伤人。
我起身站在二楼阳台看,外面密密的椰林与阳台齐平,树梢高矮起伏地铺展成一片朦胧山地,仿佛我一迈脚就能走上去。在我小时候的梦中,我夜夜在树梢上行走,从一棵树梢走到另一棵,鸟都睡着了,我不踩落一片叶子便走出很远,低头看树枝下的屋顶和路,看见月光在地上一层层种树,每棵树都有两棵,一棵站着,一棵躺着。
〔5〕晚间我从林中走回时,脚下铺满一棵一棵椰树的影子,那时我突然预感到,今夜或许会有梦了,梦里树的影子站起来,大片椰林的影子站起来。踩着树影回家的人,会获得一个在树梢上悠然行走的梦。
回到床上我又听见“腾腾”的落椰声,连成一片,由近而远,在落椰声的尽头,是海涌。
大清早,我到昨晚听见落椰声的林子捡椰子,一个也没有,椰子都挂树上,一棵未落。
那些椰落的声音呢?若我在这里久住下去,会听到所有椰子落地。或许不会,据说这里生活的许多人,都没看见椰子坠落。也没听见过。可是这个夜晚,椰子在一个外乡人的梦中,无边无际地落了,那些声音传到海里又回来。
〔6〕我在一排椰树影子的末梢站住,在这里能看见宾馆二楼阳台。昨晚会不会有人站在这里看我呢。我突然对着那房间喊了声我的名字。在我多少年后的梦里,我会听见我的喊声,我会回到这片椰林,看见椰树的影子全站起来,落椰的声音站起来,我对着那空房间的呼喊被自己听见。曾经踩着树影走来的一个人,踏着月光里的平展树梢轻轻走远。在那里我会遇见往天上背水的人,或将天上的水背回人间。我跟她们同路。我会帮她背一个。
在我所有的饥渴里,有一场渴留给椰子。
斯古拉
一
〔7〕这一天的时光是给斯古拉的。所有向上的路走向斯古拉,每一双眼睛都朝她仰望。
我相信仰望可以像云一样寄存在天上。千百年里人们对她的仰望,一层层地,在山上又堆出看不见的一座山。后来人们所望的,只是前人日渐堆高的敬仰。
我相信所有仰望的目光都会回来。
这一天,我看见千百年里人们朝她望去的目光再返回来,从银白的雪峰、从云朵、从阳光透彻的虚空中,那些目光回望过来。
我迎着她在望。
这一天我们被一座银白雪山的回光照亮。
〔8〕那些马蹄和人的脚,踩在往日的蹄印脚印上。仿佛我是无知时间里的重来者,仿佛初次望见她的惊喜里包含着不知道的无数次。
那些满含眼泪的仰望。比天空还空的仰望。像看见自己逝去亲人的仰望。什么都看不见被孙女搀扶着上山的盲人阿妈的仰望。跪拜的人群后面羊的仰望、马和牦牛的仰望,都寄放到她头顶的天空了。
谁都不说他们望什么。谁都不告诉谁望见什么。小孩见大人望就跟着望。牛羊见人仰望也跟着望。我见所有人在仰望也跟着望。在这个永远不需要问什么的仰望里,我清楚地认出自己,和这座大山里跟我一样的陌生熟人。
二
〔9〕这一年年的时间都是给斯古拉的。山脚下叫长平的藏人村庄,叫四姑娘的小镇,都为她忙碌。
赞增说他的马就是为斯古拉买的,以前他在外打工,当厨师。几年前回到村里,买了这匹马,往山上接送游人。
来看斯古拉的人越来越多。早先只是当地藏人祭拜斯古拉。每年端午节的前两天,是属于斯古拉的。这一天,人们把所有的活停下,大人、老人、小孩,远处近处的人,聚拢在一起,都往山上走。牦牛和羊也往山上走,它们供祭祀用,只有上山的路,没有返途。
〔10〕赞增居住的长平村,上千口人和三千匹马,都为斯古拉干活,把游人驮上山又驮下来。他们卖马的力气挣钱。
赞增一家五口人,夫妻俩、两个孩子和岳母,妻子在县上照顾大孩子上学,岳母在家里照顾小孩子,一家人所用全靠他的马挣钱。
家里养了三头牦牛,跟邻家的牦牛一起放在山沟里,闲了去看看,不会跑远。人去山里看牦牛时,会带点盐,牦牛爱吃盐。主人给牦牛喂盐的地方,就成了他们的约会点。还养了有几只羊。它们中的几只,是每年供祭给斯古拉的。
〔11〕路边时有倒伏的巨大松树,我原以为是树老了自己跌倒的,赞增说是地震震倒的。“那个大石头也是。”他指着一块小山似的巨石,上面刻有“地震落石”。
赞增说,“512地震”那天,他在斯古拉对面的山上采虫草。整个山“轰隆隆”巨响,像要垮塌下来,山上的巨石往下滚落。赞增说他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还以为采虫草得罪了斯古拉,手里的虫草赶紧扔掉,双手紧紧抓住树干。
“一棵大松树‘轰隆隆’倒下,砸在石头上。石头也从头顶滚下来。我吓得蹲在地上。那个时候,不知道抓住什么可靠。抱住石头,石头往下滚。抱住树,树在倒。”
〔12〕赞增就在那时看见对面的斯古拉,她摇晃着,双臂伸开,像在跳藏族舞。只跳了几步,突然停住。她一停住,所有的山和树,都停住不动了。
马道在松林间的乱石中穿行,松树高大蔽日,随处可见的倒伏的大树,在沟壑间横架成桥,像要渡什么过去。
步行和骑马的人混杂一起,人像矮树桩,直直斜斜插满山路,都面朝上,脖子伸长,走一截停下缓口气,这里空气本来稀薄,上山的人一多,就更不够用。
三
〔13〕斯古拉脚下的简易客栈,歇息疲乏的人和马。炉火在这里也有气无力,烧不开一壶水,煮不熟半锅面条。
多数人走到这里原路返回,多数人没有往高处走的时间和气力。
一些人走向海拔更高的下一个营地。我们斜躺在草坡,看步行和骑马的人,拐一个弯消失在山谷。在下一个营地,炉火的力气只能把水烧开到不烫手的温度。马匹全在那里停住,再往上的路是人的,那些陡峭山岩上没有马的落脚处。
〔14〕还有人往更高处走,走到他们在来路上远远看见的半山腰,站在那里望一路经过的村庄城镇,望游丝一样隐约在山谷林间的路,望朝着斯古拉涌来的人和车辆。
极少数的人攀到峰顶,用剩下的半口气支起沉重的身体,在凛冽寒风吹起的雪片里,面如雕塑,朝下望他们活过的人世,望丢在那里的忧伤和痛苦。据说攀到顶峰的人会莫名地忧伤,无论一个人或几个人,寒冷把表情冻住,不费力气地忧伤,跟在一口口费劲的呼吸后面。没有忧伤人会断气。
〔15〕更多时候攀顶的人被罩在云里,什么都看不见。他们出发时山顶晴朗,爬到山腰看见一团团的云飘过头顶,云是斯古拉掀开又披上的白头巾,山有心事,云便汇聚。聚多了下一场雪。阿坝的群山下雨时,斯古拉顶上在飘雪。
每年都有攀登者坠落。山风大,风推着雪和人往上。上山时人抱着一座山,人是山的孩子。下山时人抱不动自己这块石头了。坠落的都是下山的人。人要下山,还有一个东西比人更着急下山,那是人的忧伤,它跟在后面,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
四
〔16〕回返时我租了赞增的铁青马。我和赞增是熟人了,上山时我随他走了一大段路,听他讲了许多斯古拉的事。我知道他的马刚驮一个红衣女子上山,又要驮我下去,不知道马的力气够不够。
赞增说,“下山不用劲。”
步行上山耗了两个多小时,几乎把一天的劲用完,在半山腰的营地吃了一碗没煮熟的汤面,又回来一些力气。本打算走下山的,马队和泥泞的马道吸引了我。上山的路上,我们几次与马道并行又错开而去,有一大段马道在河对面,能看见骑马人穿行于森林中,听到人吆马的声音,马蹄的声音被静静的流水声挡住。那时我就想,我回来的路一定在河的那边。
〔17〕和赞增说骑马下山的价钱,他要二百块,我觉得贵,想还价,扭头看见铁青马微眯的眼睛,就觉得张不了口,两个人在马跟前讨骑马的价钱,多不好意思。
赞增说,“养马的费用高呢,每年给马买草,买加料,就得四五千块。”
赞增说话时手抚着马脖子,马直立的耳朵就在他嘴边,我觉得他是说给马听的。
“有这么多吗?”
我本来不想知道马能花多少钱,听主人说这么大一个数字,就好奇,像要替马问清楚它一年的花费。
〔18〕赞增说的加料,是给马喂包谷,赞增家里几亩地,种的青稞刚够家人吃,马吃的包谷都要到粮食店买。
我和赞增算马的费用,一年下来,竟也消费七八千块,从这个方面一想,马驮人干活也是给自己挣钱,它得现把自己的草料钱挣回来。
赞增说,“我每天上下跑两三趟,只收个马的钱。自己来回牵马,都没算钱。”
我把缰绳从赞增手里要过来,自己翻身上马,赞增看出来我是骑马的行家,也就不牵马了,他走在旁边干燥的人道上,马道在泥泞的石头里。
一位牵白马的藏族女人赶上来,跟赞增笑笑,牙齿跟雪一样白。
〔19〕“怎么没驮人?”赞增问。
“上来的时候驮人了,下去跑虚趟子了。”
我看着牵马走在前面的女主人,看着马背上的空鞍子,看着往下走的人,心里空落落的,像是把什么丢在山上了。
走到山弯处我回过头看,斯古拉孤独地竖立在天上,跟我上山时看见的一样,那么突然,仿佛天空对她的出现毫无准备。一路上我跟赞增说话,忍住没有回头看。但我分明感到她的光芒,照在我的脊背和头发稀疏的后脑勺上。我在她的注视里缓缓走远。
我想走到她看不见我的地方,再回过头来看她。
那时我看见的,就是我一个人的斯古拉了。
五
〔20〕其实我只看了她一眼。
山路一转,她突然悬浮在半空,完全不像这座山里的山。别的山翠绿,长松树长草,开花结果,她周身银白,不参与生长和凋谢的事。别的山蜿蜒起伏,她陡然而立。一尊纯银的锐利山峰,亭亭玉立在群山之上,跟这个世界脱离得干干净净。
那一刻所有目光都被她吸引。仿佛我去年前年没遇见她时的目光也在朝她仰望。
他们叫她女神。我看见的是千百年里人们积攒在那里的眼神。我久久久久的注视也积攒在那里。
以后的时间里是她在看我。
〔21〕我在她的目光里来了又走,她不知道我回到世间的哪个角落去过生活,我在别处沉默和微笑她看不见,我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她也不会知道。但是,我会因为她而仰起头,她的陡峭让我在某个瞬间挺直腰。我会想着她而忧伤。我的忧伤不费力气。也不危险。
我从没想过去攀上她的峰顶。我的力气或许只够我在世间度日。我喜欢在一条小山沟里,目送日落日出。在那里,我的炉火有足够的力气烧开水,煮熟米面。
〔22〕可是,当我回到远处,我在她山脚下吃的那顿半生不熟的面条还在胃里。我仿佛还在奔赴她的人群马队中,永远都不走近,只是步行到山下,仰头看她,看我寄存在那里的目光,和太阳照暖的云朵,和星星月亮,和所有的仰望聚合在一起。
我这样想着她的时候,什么都耽误不了。就像马夫赞增把一年的活干完,到每年端午节前,属于斯古拉的这一天,把所有的事情放下,把马缰绳放开,带着家人步行上山,在正对着她的山顶,煨松烟,磕长头,把一年的平安、一生的心愿默默倾诉给她。
〔23〕或许我已错过的每年每年的这一天,在云朵上积攒成完整的一年。那是我留给她的整整一年。当我在世间的时光不够用时,我就来她的永恒里续命,用她的时间做更长久的事。我会看见四季围着她轮回,而她在唯一不动的季节里。
我会在她的黄昏里,一山山地看落日。我不知道她的太阳落到哪里。四周都是山。每座山都带来不一样的黑夜。斯古拉在她自己的高高白天里,在那里,落得再远的太阳都在她的地平线上,我沉入黑夜的梦也在她的默默注视里。
长成一棵大槐树
〔24〕崇信县最老的大槐树,立于山间台地的打麦场上,孤独一棵,据说三千二百岁了。几乎与中华文明同寿。麦场下方是关河村,名字同槐树一样古老。四周一块一块的山洼里长着麦子。想必关河村人,牵驴赶牛拉着石磙子,在槐树下一圈圈地打了几千年麦子,到如今,还在为那些麦子操劳不息。
崇信山多地少,养人不易。活下来的古树却不少。我们看到的另一棵大槐,长在一方小寺庙里,只剩下半面树皮。看守寺院的老者说,他小时候树还完整,只是里面空了,空心树洞里摆一小方桌,常有人围坐打牌喝酒。后来大半面树干都朽了,剩下的一面树皮支撑起巨大树冠,茂盛地活着。据说这棵树也三千岁了。
〔25〕另外两棵夫妻大槐,长在一户人家的院子。去年春天,家里老父亲爬上那棵妻树摘槐花,掉下来摔死了。儿子把父亲的死赖给这棵树,就把它两万块钱卖给一个陕西人。那些人当着夫树的面,把妻树的大小枝干都锯了,剩下一个秃秃的树鼓墩,用挖掘机连根刨出来拉走。留下的夫树变成独木,活得也不似以前旺势。可能挖一棵伤了另一棵的根。可能这棵看着身边少了陪伴千年的那棵,伤心了,不想好好活。
关河村的这棵大槐也险些被锯了。几年前有两人在树干上拉开大锯,想伐了它卖钱,锯进去一米深,锯口不住地往外流血,而且,锯开的口子一会儿就原长住,这把伐树的人吓坏了,连忙跪下给树磕几个头跑了。
〔26〕我在大槐树下走了几圈,没看见那个锯开又长住的口子,树把人对它的伤害长进年轮里了。我仔细地看这棵大槐的每个枝干,它们有的东斜,有的西歪,有的枝好端端的,突然中途一拐,改变了方向。我知道它为啥长成这样。我会看树。一枝一杈地看上去,它所受的风雨寒暑、生老蹉跎,都长在树上,历历在目。
关河村大槐有六个主枝,绕主干四周。其中三个主枝朝上,一个向东南,一个向西南,另一枝往北,构成树的大形。大槐的南面设有祭祀台,供人焚香祭拜。南面向阳,是树的正面,所有叶子阳面朝南,绿光闪闪。树和人一样是站立生物,有脸面,有前后左右。
〔27〕大槐朝天的三个主枝交错向上,把树的高度拔向云端。这是树的朝天枝,占得树头,独领阳光风雨,也容易遭受雷电袭击。我在西北常看到断头树,都是风摧雪压所致。树高天砍头。对于树木来说,长太高并非好事。西北干旱,遇到一个雨水多的年成,树木会无节制地生长,往高蹿,生出繁枝茂叶,树身难承其重,一旦遭风摇雪压,断头折干便再自然不过。树的朝天枝受惠于天,也最受天罚。据说崇信关河村大槐从未遭过雷击,原因是四周的山峰替它避了雷电。我想,树的节制生长也是原因。大槐的朝天枝看上去并不招摇,没有过分长高,给树惹麻烦。
〔28〕整个槐树高二十六米,十层楼房的高度,但南北宽三十八米,宽度胜过了高度,使它在山间一洼台地上,只显大,却不显高。这是树的聪明,它能活到天寿之龄,肯定是每个枝都活明白了,知道该怎么长。
大槐向东南的主枝,是树的迎日枝,由一个主枝生发为三,两枝朝上追高,一枝斜逸向东,脱离树冠数丈,像树伸出的长长左臂,其枝干所指,必是每日的日出之地。住在村里的人会知道,每天早晨的太阳,从他家柴垛后面升起。迎日枝在漫长的黑夜里也不会长歪,它的枝准确地迎向日出。那是只属于这棵树的太阳,第一缕曙光,被伸到最远的树叶接住,迎到树上,迎到大槐下的关河村。
〔29〕每年春天,树东边的枝头先绿,先长出叶子。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其实每一棵树,都单独地迎接太阳,长成了自己的模样。
长在大槐西南的送日枝,到下午才会被太阳完全照亮。这时候,东边迎日枝的一半,已陷入阴影。关河村的夕照短,它西边是高山,使树和住在这里的人,都只有半个下午的阳光。大槐的送日枝,也顺了太阳的走势,枝干西斜朝上,指向的正是每天日落的山脊。我在大槐树下正赶上关山落日,眼看夕阳独自走远,自己伫立树下,忽有种两相远别的孤独。但头顶壮大的送日枝,又让我感到落日不孤。
〔30〕我沿那棵倾身向日的树枝望去,就要落入山后的夕阳,正好卡在远山的一处缺口里,不舍地多照了大槐树一会儿。这每天多照的一会儿,在三千多年里,已经积累成年。我也在这依依不舍的夕照里,看着大槐朝西的叶子,一层层地黑向树梢,直到送日枝端指的山口,剩下黯淡霞光,树身才全黑下来。
大槐最长的一个主枝,长在北边,是树的背阴枝,常年在树冠的阴影里。背阴枝因为前后左右都被别的枝遮挡,它只有往远处长,一直把枝干伸到树冠外的阳光里。所以,背阴枝也长得最长。这也使关河村大槐树东西窄,南北长,树冠呈扁圆形。
〔31〕让大槐树长扁的还有风。崇信所属的平凉地区秋冬季为西北风,春夏季多为东南风或东风,一年中风多从东西两面吹,树自然被风吹扁,形成南北宽,东西窄。我在西北看到的大树,也多是扁的。整个秋冬季漫长寒冷的西北风,把树迎风面的皮,吹得光滑坚硬。那些风一年年地吹进树干,吹扁树的一圈圈年轮。把树吹成扁模样。西北多独木,有叫“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这样的地名,不会多过三棵。独长的树多是扁的,有迎风面。这样的树木,因为木质不均匀,容易走形,也属无用之才。
〔32〕用木料的人,能从木头截面,看出是不是迎风独木,木匠做活,都选用林中树,树在林中,相互遮挡风雨阳光,也就不像独长的树有迎风背风面,它的木质也便均匀。讲究的木匠也是不伐用独木的。独木命硬,人消受不起。
一棵树独自长大,并不是其它树被砍了,剩下一棵。是因为这方水土,只够长一棵树,多一棵都活不了。像关河村大槐,方圆几公里,独独一棵。这样的大槐,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竟然活了三千多岁,更是让人难以相信。崇信塬高土厚,属半干旱地区,还算不薄的降雨量,勉强维系庄稼和草木生长。
〔33〕土豆麦子包谷,降几场透雨,就有收成了。草比庄稼耐活,再旱的天,根不死,种子留着,一场雨又活过来。树不一样。小树靠天,大树靠地。类似果树这样的小树木,因为根系浅,靠天上的雨水便能活下去。但关河村这棵大槐树,是不能指望雨水活命的,它茂密的树叶和枝干,足以把一场大雨在半空里接住,落不到根部。那它靠什么活命呢。
我一路上多次看到施工破开的土塬断面,从断面上露出的树根草根,能清楚地看见树木在土里的生活。土塬上层一两米到三四米,是雨水蓄积的地表湿土层,几乎所有植物的根,都扎在这层。草根浅,树根深。
〔34〕草有一点降雨便能活,树却需要更多水分才能长大。在湿土层下面,是厚厚的干土层,所有草木的根须伸到这里停住。这一层的土是生土,也叫死土,缺少植物所需的养分。干土层再往下,是和地下水层接上的湿土层或湿沙石层。在雨水充沛的地方,地上湿土层一直连接地下水层,植物的根可以扎得深远,每一棵小苗都有可能长成大树。而在干旱西北,干土层厚达数十米上百米,地上的那点雨水,永远不可能润透它,那是植物无法逾越的绝地。这也是西北许多地方不适合大面积植树的原因。那些人为栽植的树木,永远无法自活,要靠人去引水养活。树越大,耗水越多,直到人养不起。
〔35〕关河村大槐树长在半山腰的台地上,我看它的枝干,便知道它地下根须的走向,那些深扎土中的根,也基本上长成树冠的样子,这条朝东的粗壮横枝下面,对应着同样粗壮的一条大根,那是它地下的影子,根往哪伸,枝往哪展,树根在地下的暗处,给看似明处的树枝指引着方向。我知道这些向下伸去的大树根,一定穿过了其它树木无法扎透的厚土,在更深处哗哗的水声里,让一棵槐树活出了三千年的茂盛繁荣。那是要靠一条地下河流才能养活的大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