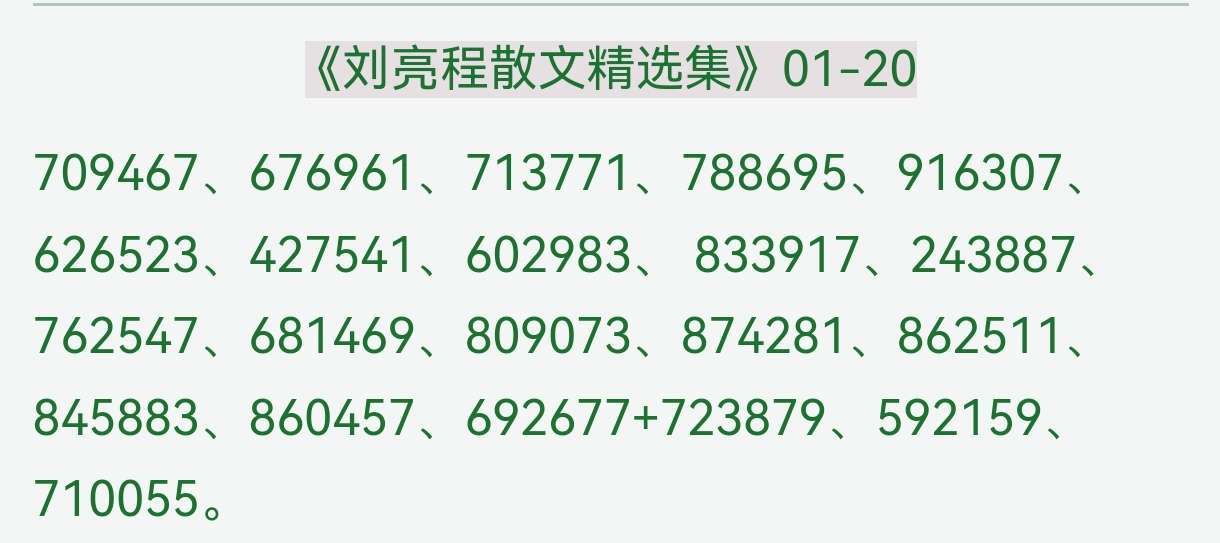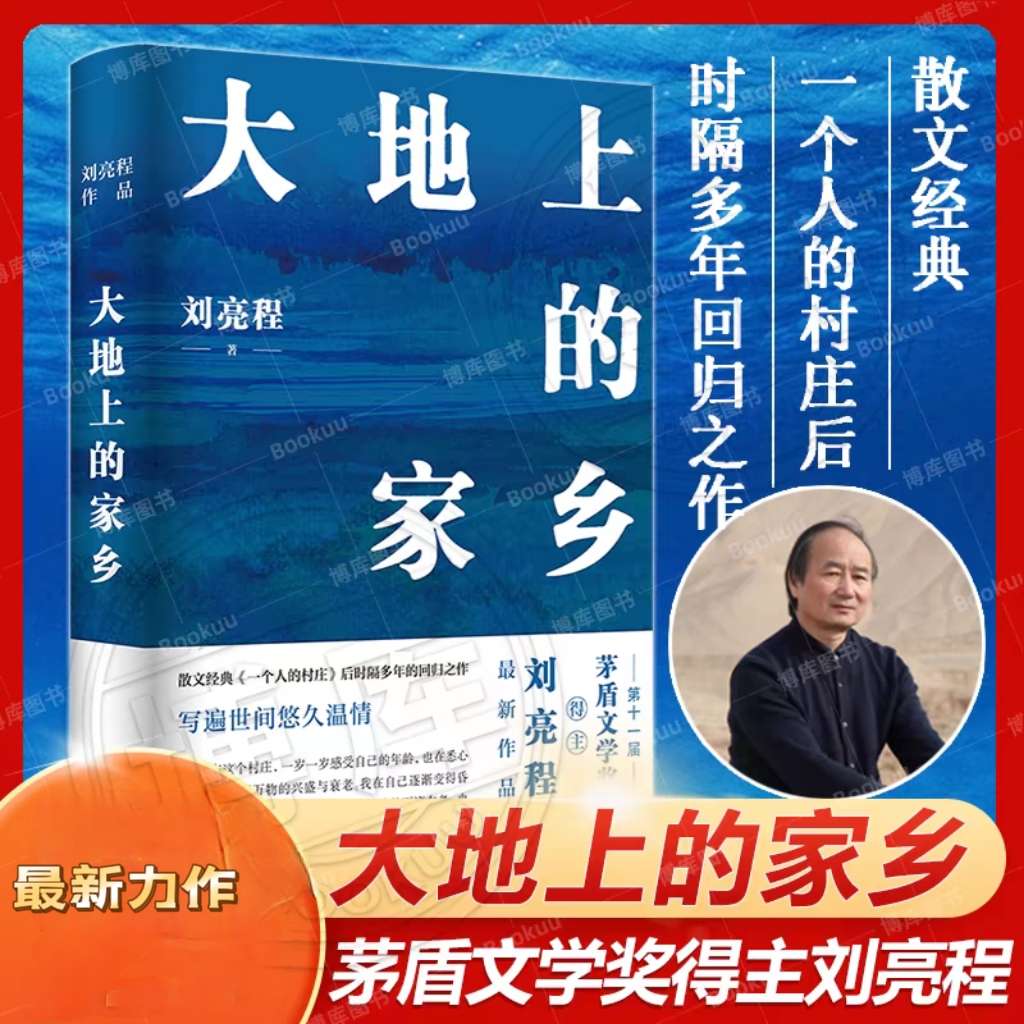
那个从天坑往外背土豆的人
一
〔1〕下天坑的栈道口站着一位卖拐老人,粗矮身体,一身蓝衣裳,戴蓝帽子,像是上世纪里的人。他用树藤做的拐棍沿崖壁立了一排,高矮粗细的都有,手艺糙了点,但不贵,二十元一根。
我拿着他的拐左右端详,想买一根合手的,试了几根又放回原处。我没拿定主意要下到天坑去。带我们来的人说,下去上来要大半天工夫,我们时间不够,就在坑沿上看看吧。
其实天坑本身对我没多大吸引力,我在准噶尔盆地长大,那也是一个大坑,只是太广大了,看不见它的深。
〔2〕栈道口窄窄的,游人排成一溜往坑里走,少有人停下来买拐棍。这个时间都是下坑的人,人下坑时或许想不到买根拐棍。
我给老人说,你若在坑底下卖拐,一定好卖。那时候人要上坑,抬头是万丈峭壁,人往上走时自然会想有根拐棍。
老人摇摇头,说,我这个年龄了,下去上来费劲。
问老人高寿。说八十岁了。
他说出自己年龄时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笑,像很无奈又像不好意思。我被他说出的年龄吓了一跳,仿佛站在一个自己眼看也要走到的八十岁的深渊上。突然地理解了老人脸上的表情。
〔3〕老人说他年轻时经常下坑去,下面有个小村子,住着几户人家,现在都搬出来了。
我问,住在下面咋生活。
老人说,下面的台地上能种庄稼,包谷水稻都能长熟。
他给我讲了村子里的一家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坑里的村子“包产到户”,那家人在分到的地里种土豆,男人把土豆背出坑外,到镇子上卖,成了当时有名的万元户。
把土豆背出天坑去卖?这得费多大的劲呀。
我小时候家里也种土豆,土豆是口粮,我也背过土豆,半麻袋土豆压在背上,那些圆鼓鼓的土豆硌在皮肉上,能把脊背磨烂。
〔4〕那个男人是怎样把一袋袋的土豆背出天坑,又背到镇子上卖掉,成了万元户。那个年代,一斤土豆几分钱或一两毛钱,几十万斤的土豆,才能卖到一万元。那个男人每次背一百斤,得背上万次。那时没修栈道,也几乎没有路,多少年来这个小村子的人,就没打算踩一条路出来,他们担心外人会沿着它下去。他们最初是为了躲战乱藏到坑里,养成不让人知道的习惯。那个男人是怎样背着一麻袋土豆,上万次地爬上坑来。
老人讲的故事,使我有了下一趟天坑的冲动。仿佛那里有一麻袋土豆,等着我去从坑底背上来。
二
〔5〕奉节县小寨天坑据说是世界上最大最深的坑,坑口直径六百二十米,深六百六十六米,从坑底往上攀,相当于爬三百层高楼。坑里隐藏着一个小村庄,从坑沿口往下看不见房屋,也看不见炊烟,从坑底升起来的云气,把炊烟裹藏起来。在很长的年月里,小村庄人过着不为外界所知的生活。坑底有条河,水大而湍急,只是短短的,自坑底冒出来一截,又遁入底下,人称地下河。天坑便是地下河开的一方天窗。河在黑暗地下不知道自己流到了哪里,便开一个窗洞看看路。
〔6〕河边台地上有几块田,种的粮食或刚够几户人吃。
整个白天坑底是阴的,只有半腰处的峭壁上有一带阳光。风或许吹不到坑底,所有的树是静止的,看不见光阴移动,人也没有影子,草木朝着坑口的那片天光长,一万年也不会把头伸进阳光。人爬到半腰处,才能看一眼太阳。人喊一声,四周有许多个声音回响起来,都是自己的。坑里人或都不大声说话。只有露头的地下河哗啦啦流,从黑暗流向黑暗。坑里的天应该只亮一会儿,就黄昏了。
〔7〕去过坑里的人说,从坑地看,天是圆圆的一坨。看不见朝霞和晚霞。晚上夜空低垂,星星和月亮,都挂在坑沿上。看不见北斗星,也看不见启明星。风从坑口上头刮过去,外面刮多大的风,坑里的树都不摇。坑壁上有洞,往外冒云气,地下河也往上冒云气,半腰处云雾袅绕。
明明是地陷下去,为何不叫地坑而叫天坑呢。后来,沿栈道一级级下去,下到天坑半腰处,我才领悟,人在坑半腰,天也在半腰。生活在坑里的人,日夜看见的,是坑里的天。人在坑沿往下看见的,也是天。地深陷得找不见了,天塌进了坑里。
三
〔8〕步道沿坑壁折返下行,台阶陡峭,人需手扶栏杆,才能一步步下去。坑壁长满了树,让人觉不出自己在绝壁深渊的边缘,树遮蔽了危险。
下行到坑壁侧面,树少了些,看见正午的阳光,照在坑底北侧一方台地上。我想,那个男人的土豆应该种在那块台地上。天坑里雨水充足,露出的地下河会自己造出云来,坑太深云飘不出去,又下成雨。他的土豆一定有个好收成。
天坑底下原有一个发电站,我在半腰处听不见发电机的声音。据说早年外面有事通知坑里的人,嫌下去费劲,喊也听不见,便用石块绑上写了字的布条扔下去。很久,听不到石块落地的声音。坑里的鸡鸣狗吠不会传上来,人声不会传上来,几户人家的炊烟,散在雾气里,也不会被看见。
〔9〕每下几个台阶,气候会凉一些,也更潮湿。
越往下走觉得坑越深,有点心里没底。
这么深的坑,都没有陷住那个背土豆的男人。他一次次地负重爬出天坑,把土豆卖了又下去。
我忘了问这个男人现在的生活,他早已经迁出坑外,那个在坑里的村子只剩下两间破房子。
我想他早就佝偻身子了,腿脚也已经走坏。算算那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背土豆卖成万元户的男人,现在也有七八十岁,跟坑口卖拐杖的老人一般年纪。或许他就是我路过小镇时看见的坐在街边的某个老人。
〔10〕到这个岁数,应该啥也背不动,身体本身变成了负担,剩下的力气将一天天地挪不动自己。这时候回头,看见自己在一个八十岁的深坑里。人往高龄长寿里活,命却是在下沉。
这样想时,我又朝坑底看,半腰处一个山洞,正往外冒着白色的虚无缥缈的雾气,那地下河的水声也仿佛在耳朵里,又像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我这个年龄,腿脚还有力气,真应该下一趟坑底。但行至半腰处,往上看,坑口已经吃进天空里,带我们来的人在上面喊。我们没有下去的时间了。
〔11〕往上攀爬时,突然感觉到了沉重。我背负着五十多岁的自己,步履艰难,大口地喘着气。那老人的拐杖助了力,使我多出一条腿来。走到快上去那一段,步梯出奇地陡,不敢回看,腿在颤抖,身体愈加沉重,仿佛三十多年前那个男人的一麻袋土豆,不知不觉地压在我身上。仿佛四十多年前我曾经背过的那半麻袋土豆,也压在了背上。似乎一生背负的所有重担都没有卸去,它在这一刻回到身上。
还有,那个从天坑往外背土豆的男人,他的一麻袋土豆,也会压在知道这个故事的所有人的背上。
从北疆到南海
〔12〕从新疆北疆飞到南海,行程万里。沙漠戈壁与茫茫大海之间,是辽阔而拥挤的中国。人们都说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我说,不到南海不知道中国之辽阔。新疆虽大,但我在新疆却感觉她不大,因为不管往哪走,走着走着就到了边界。一道铁丝网拦在眼前,所有通向远方的路到此中断,或拐弯。我在北疆塔城,沿着中哈漫长的边界线行走过,界碑和铁丝网在左,国土在右,突然就有了触摸到国家边缘的感觉,国就是铁丝网里面的这块地方,说大也大,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家就是其中只有自己能走回去能找见的那个小小的窝。
〔13〕北疆“中哈”边境大多是牧区,中国这边,牧草被牛羊啃得光秃秃只剩下草根。铁丝网那边,草木茂盛葱郁,草原辽阔无际。就有羊把头伸过铁丝网孔,脖子长长地啃哈国那边的草,把挨近铁丝网的一溜子草啃得精光。据说哈方为此还与中方交涉过,说我方的羊越境吃草。中方说,羊只把头伸过去啃了几口草,不能算越境。哈方说,我们哈萨克族数羊都按头算,一个头代表一只羊,头过去就等于羊也过去了。中方说,我们汉语把羊叫只,一只羊,“只”是一个口加两点,口代表羊的头和身体,两点代表蹄子。按我们汉语的理解,一个羊的头、身子、蹄子都过去了才叫越境。最后交涉的结果是哈方宰了一头羊,中方拿了几瓶子酒,一起把事端摆平了。
〔14〕看着这些在铁丝网旁边放牧的羊群,突然就感觉到中国太小,小到我们国家的一只羊,需要把头探出边界,啃几口别国的草才能填饱肚子。
而铁丝网那边的无边草原,也曾经是中国的土地。清末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去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力虽然增强了,但邓小平曾经针对历史遗留的西北边界问题说过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边界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可是,西北边界问题没有留给后代。
〔15〕我曾去过夏尓西里,那是中哈两国经过艰难的边界谈判,于二〇〇三年收回的一小块土地。原争议土地三百二十八平方公里,中国获得二百二十平方公里。单从数字看,中国占了便宜。但是,这一小块土地的回归,也标志着中国所有原属土地的永远失去。
中国在西北曾经大过,国土曾经辽阔到天边,现在不大了。
而南海依旧是大的。从海口到永兴岛,我们乘坐三沙一号航行了一整夜。黑夜的大海上,只有漫天寂寥星辰,海面没有一丝灯火,夜漆黑到海深处,那样的航行,仿佛没有希望会到达什么地方。
〔16〕完全不似我在新疆大地上的夜行,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去南疆,也是黄昏出发,过天山时日落,暗夜使荒冷天山显得郁郁葱葱,一路总有相隔遥远的灯火相伴。南疆塔里木盆地的夜凹进土地深处,沙漠戈壁和小块的绿洲村舍浑然一体,趴在窗口,看见黑夜里不远的一点亮光,那是一个村庄留到深夜的一点亮,像在等谁回家。可是一火车的人没有谁到达,那个彻夜亮着灯的家不属于我们,但又仿佛温暖了每个看见她的人。海上的夜行不经过谁的家,一样的波浪从岸边荡漾到远海,我在船上睡一觉醒来,爬舷窗望一眼,依旧是海天混沌,汪洋一片。这使我心生茫然与豪迈,在我们海洋辽阔的国度,我们把一场一场的梦做完,船还在自己的海域,海依然辽阔无边。
〔17〕三沙市所在地永兴岛虽然是一个只有几十平方公里的小岛,两个小时即可环岛散步一周,但它在南海中已经是大岛了。岛上布满地方和军队的各种建筑,可谓寸土寸金。夜晚住在宾馆,我的耳朵里轰鸣着战机起起落落的声音。岛上有军用机场。中国海军在南海的大规模军演就在近日。菲律宾关于黄岩岛的国际海洋法庭裁定也是近日。中国作家赴南海采风团也赶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采访范围是西沙诸岛。相对于整个南海,西沙算是最安静的内海了,但也并不安宁。据说我们乘坐三沙一号从海口驶向永兴岛那夜,美国一艘航母就在距我们二百海里的海域游弋。这个距离在陆上应该是不远的,三个多小时车程。
〔18〕采风团乘坐的海监船可能一直被监视。我们登船前拉起红布标举行的采风启动仪式,也可能在他们的卫星监控里。美国海军会对一群赴南海采风的作家感兴趣吗?有这个可能。我在《新疆文学》(后来改为《西部》)杂志做编辑时,得知美国一家图书馆长期订阅我们杂志。据说还有专门机构的专家,通过文学作品研究边疆民众的心中愿望。美国人相信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未来走向取决于人民心中的愿望,他们通过文学了解中国人,尤其是边疆地区人们的心中所想。关于中国人的心,他们还得在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中寻找。我们这群前来书写南海的作家,很有可能会被他们关注。
〔19〕西沙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闷热,海洋那么大,却不通风透气,我们采风的几日都是晴天,天和海都光秃秃的,中间没有一层叫云的东西,我在海上似乎没有看见云,黄昏坐在小岛上,海天一色,不像在旷野中,一堆堆的云蹲在地平线上,围一圈,人坐中间,有一种踏实的存在感。在海上人、船、岛都像在漂着,无所依靠。
我们登临的甘泉岛就像是漂在汪洋中的一片荒野,岛上长满一人多高的灌木,有两户渔民居住生活,简单的工程板搭造的房子隐在树林里,岛上暴热难耐,我们走几步都炝热得喘不过气,可想渔民住在这里会有多难过。
〔20〕有一口据说是宋代的水井,还在饮用。渔民带我们在半人高的灌木中找到一处建筑遗址,只剩下依稀可见的四方形房基,这座古代房屋,是用更远古的海生物化石建造的。小岛中心是一片洼地,在这里看不见海,听不见海的声音,仿佛站在炙热的戈壁荒野中。岛中间的植物也跟戈壁上的一样,都萎缩地低头生长。前者要抵抗暴风雨,后者则是保存水分,以低垂的树冠给躯体遮阴纳凉。小岛之外是荒凉的海。遥想古时候,对于汪洋中漂泊数月的航行者,这块有淡水井的小岛,该是多么地难得。那时候过往商船在岛上留宿补给,想来也比现在热闹。
〔21〕回到渔民家时浑身已被汗浸透,在渔家朝海的小径上,我突然感觉到一股凉风,是从海上吹来的,两旁的灌木丛把风聚拢在一起。我看见渔家的餐桌、摇椅都摆放在朝海的小径尽头,在南海无边的燥热里,竟然有这样一些凉快处,让海上人家借以纳凉度日。
甘泉岛是中越海战的引发地,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南越海军“李常杰”号军舰首先入侵,对我国正在甘泉岛附近生产作业的两艘渔轮方向开炮威胁,又瞄准甘泉岛上的我国国旗轰击。次日,4号“陈庆瑜”号军舰也赶来与之会合。一月十七日上午,南越军队在西沙永乐群岛的金银岛登陆,下午又派兵强占了甘泉岛。
〔22〕当时的甘泉岛四周应该是船帆遍海,捕鱼繁忙,岛上应有不少渔民居住。现在的岛上只一两户渔民,海上根本见不到渔船。
当地领导介绍说,西沙常有越南渔船非法进入捕鱼,我海监船只是柔性驱离,全不似外国海警对待中国渔民渔船的粗暴。如今越南在南沙的渔船是中国的十倍。而在十几年前或更早,这里是中国渔船的天下,中国海军顾及不到的海域,皆是那些打鱼船在守护,这片海域有他们的生计,是祖传的渔场。渔民们冒着被外国海警扣留,没收船只甚至丧失生命的危险打鱼,护卫海疆。而现在,靠打鱼为生的中国人越来越少。
〔23〕几艘海监船巡游在西沙,固然是重要,但怎比千条打鱼船拉网作业。当年中俄边界的许多争议区,便是中国牧民赶着羊群占住的,是边境农民开田种地守住的。
从海监船上下来,乘小快艇去鸭公岛,一个巴掌大的小岛,有一户渔民住在岛上打鱼,岛上一小片树林,渔民的板材房子隐在林中。鸭公岛的午餐,吃的全是没见过的海鲜。有一种石头鱼,长着鳄鱼一样厚实的皮,渔家烤熟端上来,我们在厚厚的皮下面找到鲜美无比的肉。岛四周全是堆积的海洋生物化石,证明着海洋数千万年以来生命的层层叠加和演化。
〔24〕一艘军舰停泊在鸭公岛海域,远看像漂在海上的高房子。我们返回时起风了,海面沟壑起伏,快艇在浪中跌宕前行,船体碰在浪峰的强烈撞击感,让我第一次觉到海水的坚硬。给我们开快艇的是这片海域的管委会书记,复员军人,单身,无驾照,或许中午在鸭公岛一起喝了酒壮胆,他在惊涛骇浪中竟然把快艇开得飞快而有把握。
赵述岛要大一些,岛上一块地方覆盖着从陆地运来的黄土。我们在黄土上种了椰子树,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种子,从一只大椰子里发出胳膊粗的芽,这个芽三五年就会长成水桶粗的椰子树。栽树的坑是挖掘机挖好的,我们只需把椰子苗放进去,用铁锹把从岛外运来的土壤填满。
〔25〕在岛上,土壤是最缺的。刚上岛时,看见日军占领时的炮楼,炮楼边的牌子上介绍说日军从岛上盗运走多少吨鸟粪,有点不理解。现在清楚了,土壤和肥料是岛上生存多么珍贵的资源。还从资料看到当年中国民兵收复赵述岛时,岛上越南兵只胡乱放了几枪,然后就抱头鼠窜,躲藏在灌木丛中。岛中心果然有一块不小的灌木林,长得密不透风。中午在岛上午餐,渔家饭菜,样样鲜美,吃着便忘了热,觉得闷热比寒冷好受一些。我在新疆受过隆冬的寒冷。南海之热在我们行程的后几天,渐渐觉得不算什么了。
〔26〕回返海南的那夜我住在海警执法船上二副的房间,因为海上军演在即,采风团临时调整行程,提前返回。执法船给我们腾出了十几个单间。二副的房间干净整洁,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容纳了单人床、书桌、储藏柜、卫生间,却不显拥挤。半夜醒来,趴在舷窗望外面的大海,灰蒙蒙一片,跟我在夜晚经历的所有荒无人烟的地方一样。我不想用荒凉来描述海。我想到的是新疆,一个有无垠戈壁沙漠和绿洲的家乡。南海只闷热,不荒凉。我在新疆经常会走到边界,伸手触摸到国家的边。在南海西沙我们没有航行到国家的边沿,她还远着呢。我们的祖先曾经把海域扩至天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诗意的境界,也是古人留给我们引以为豪的海洋观。
云间白帝城
〔27〕十二三岁时听后父说《三国演义》,知道了白帝城这个名字。后父不识字,不知他说的“三国”从哪听来的。跟我后来读的不太一样。后父讲“三国”前总要说一句“提起三国乱如麻”,乱如麻的“三国”,在民间说书人那里,应该也有无数个头绪万千、理不清也说不尽的别样版本,如蓬勃野草,早已经长出了原作的边界,长得野趣横生。后父只是这些乡间说书人中最普通的一个,却也是最早让我听到文学故事的人。他说书,却不认得书里的字,或也从没见过《三国演义》这本书,所以他说的也不是书,是经过多少张嘴,把书说成的话,传到他耳朵里,他又说给我们。那些书其实已经变成了他的话,带着老新疆方言的味道。
〔28〕后父早年在村里赶马车,去过县城、省城,经常在那些远路上的车马店里留宿。他说的《三国演义》,或许就是路上听来的。我不知道后父是否听全过一部浩瀚“三国”。我也从未听他说全过。他只是一回一回地说,也不按故事顺序,想起哪段讲哪段,经常把故事说颠倒。但我现在记住的,却是被后父说乱的那个“三国”。他只是说他记得的片段,他能记清楚的,便反复说,每次说的也都不一样。
白帝城托孤,是后父最爱说的一回。他讲刘备临死前,把诸葛亮招来,安顿后事,仿佛就是讲我们村里一个快死的人,他就要撒手去了,但是儿子还小,家里一摊子的事,牛呀羊呀鸡呀地里的庄稼呀,都没了人照料,他把自己最信任的人找来,交代后事,也把孤儿寡母托付给人。
〔29〕这样的事在村里时有发生,后父或也帮人家操办过托付孤儿寡母的事,其中细节自然熟悉不过。所以,他能把白帝城托孤这一回,说得声情并茂,他说的时候心里有底,我们听这一回时,心里也有底,那底便是不久前村里死去男人那一家的经历,那家孤儿寡母的哭声似也回荡在后父说的故事里,便有人听着哀叹起来,有人抹着眼泪。一个千年前发生在白帝城的故事,和我们村的一桩近事,叠合在一起。
只是,后父再怎么把那个故事与我们的生活拉近,我都无法将白帝城,想象得像我们村子一样。白帝城这三个字,我初次听到时,便确信它不是一处人间的地方。
〔30〕多少年后,我在夔门左岸山顶的天台,看深渊里的大江,在万山间任意穿行,我站在一块石头上,感受着杜甫《登高》里“滚滚来”的长江,有人指给我看江边湾流里的一座孤岛,说那就是白帝城。
仿佛我遗忘多年的一个名字被叫醒。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是后父话说“三国”里的白帝城。它没有我想象得那样高,但又是我心中的模样。它孤悬于江边小岛之上,俨然与俗世隔开了一条大江的距离。
我们下山来乘船到白帝城下,当我一步步地拾级而上,仰脸看它小而陡峭的城门,“白帝城”三个字牢实地守在门头上,里面街道也窄窄的,那个我少年时从说书人嘴里听到的白帝城,就这样现身在一个中午。
〔31〕陪同的人说,三峡大坝修成后,这里的水位涨了七十多米。也就是说,我现在看见的白帝城,比刘备托孤时的白帝城,比李白杜甫所看见的白帝城,都已经矮了七十多米。想想那个得了赦令而兴奋不已的李白,是从七十米深的水下,乘轻舟穿过了万重山,那两岸猿声,也已淹在水里了。还有杜甫,他写给白帝城的那些诗,也仿佛淹在了水里。“清秋燕子故飞飞”的天空,如今已成“信宿人家还泛泛”的水面。后来我乘坐游轮经过夔门时,特意低头朝水里看,仿佛那里有老年杜甫自水深处看上来的目光。
〔32〕杜甫晚年曾寄居夔州,白帝城自是其常去之地,我在诗中看到他对白帝城的独爱,这座仙都帝城,每每被诗人捧向高处。杜甫在夔州写诗四百三十首,很多诗句写到白帝城。在夔州不到两年的时光,是其诗歌的硕果之秋,亦是人生暮年。这暮气写在他的《登高》里。我年轻时喜欢他的“无边落木”和“不尽长江”,老来读出的全是“萧萧下”。杜甫写《登高》时,五十五岁,离他五十八岁去世,还有三年的活头。他或许已经预感自己到了阳寿的高处,人世的万里悲秋已然到来,多病之身,也一步步地登到高处。《登高》及同期创作的《秋兴八首》,也像是诗人对颠簸一生的“托孤”与交代。只是,他不知交代给谁,只孤独一人对天语。
〔33〕在白帝庙旁的托孤堂,我看见了少年时后父说给我们的那个托孤场面,半卧床榻的刘备,满眼的遗憾与不舍,他望着坐在床头边的诸葛亮,当着众大臣的面,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这位老臣。这是一个将死之人,给生者交代后事。那场面,仿佛就是后父所说,但又完全不同。不同在哪里,我竟说不清楚,只觉得后父当年说给我的,是另一个刘备,和另一个诸葛亮,甚至在另一个白帝城。
那个白帝城在我少年时的无知仰望里,它遥悬“彩云间”,“高为三峡镇”,“城中云出门”,它既在杜甫万里悲秋的萧萧落木里,也在我后父用新疆土话说的“乱如麻”的三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