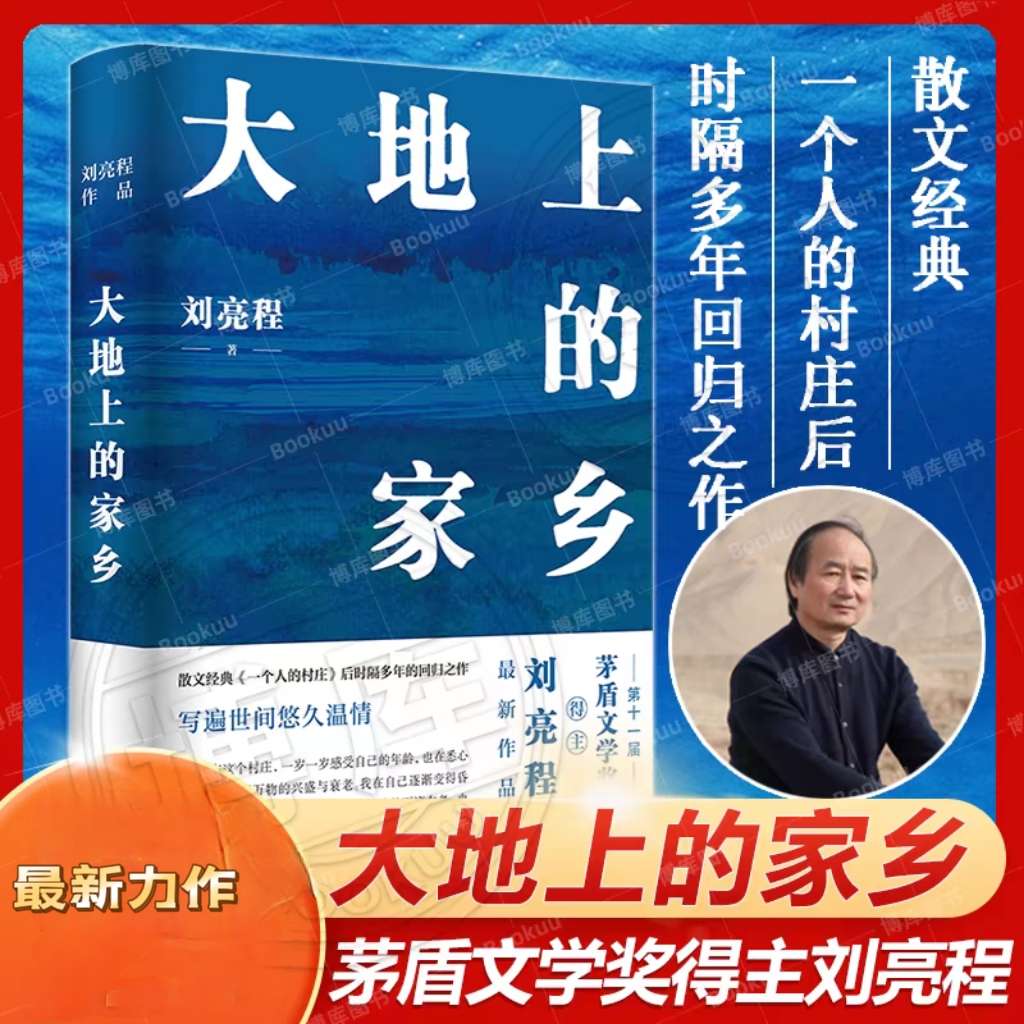
在南京听虫鸣
〔1〕朱赢椿的书衣坊坐落在南师大校园的树林中,细竹竿围起的小院,与外面隔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围栏上看不见门,朱赢椿从里面拉开一小片围栏,我们进去后门又回到围栏上,成为它的一部分。
小院里放着些木制旧物件,湿漉漉的,像是刚下过雨。靠围栏种植了爬藤植物。志宙说这是朱老师给虫子种的。来之前志宙介绍说,给我的书做设计的朱老师,是一位跟虫子打交道的人,你们可以聊聊虫子。
〔2〕书衣坊是一个旧厂房改造,原有空间中加了两层,楼梯陡而窄,每个空间里都是朱赢椿的虫子作品。在他设计的一本书的封面上,活灵活现爬着一只黑蚂蚁,我明知道是印上去的,却还是忍不住拿手指想按住它。在屋里能听见外面树林草丛的虫鸣,有几声或是他种的那几棵爬藤上的虫子发出的。还有几声,像是被他制作成夸张雕塑的虫子发出的。
朱赢椿出版过一本很好玩的书叫《虫子旁》,是给我们这些人字旁看的。虫子旁的字爬在字典中,爬在诗和散文小说中,爬在某些人的名字中。某些人,或许是虫子转世,来教我们和虫子认识的。
〔3〕我最感兴趣的是朱赢椿发现的虫文。虫子在树皮下,在树叶上啃咬爬行的痕迹,被他收集起来,做成唯有虫子能看懂的虫文书。或许虫子也不能看懂。它太短暂的一生来不及回头看。但这个叫朱赢椿的人有充足的时间看虫子走过的痕迹,并把它做成文字。我看那些虫文,虽然不认识,但一点不陌生,它们出现在我从小到大见过的草叶和树皮上,还有泥土地面上。无处不在的虫子,一直在我们身边写字,用它们的嘴、爪子和整个身体。一个笔画不多的虫文,或许就是一只虫子的一生,有的虫子从早晨活到中午,一辈子就过完了。有的会活几天几个月。它们在那么短促的生命中,一声紧接一声的鸣叫,像是有多么紧要的事情。
〔4〕我建议朱先生把他收集整理的虫文解读出来,每个字标出不同的虫鸣声来,做一本《虫人词典》,便于我们和虫子交流。在自然界,都是虫叫虫应。人若知道了虫在叫什么,能与虫呼应,该是一件多美妙的事情。
不过,若真安置一堆设备去录制计算虫鸣,变成科学研究,又没意思了。我们和虫子之间,有一条古老直接的心灵通道,虫鸣入耳时人已然听懂,心有感应。人心中亦有万千虫子鸣叫呼应。我早年曾写过水草丰茂的年成里“一尺厚的虫声”,也写过干旱少雨季节“虫声薄得像一页纸”。南京水系密布,植被丰茂,是虫子繁殖生息的好地方。
〔5〕夜晚我在宾馆高层,竟听见了从街市升起的阵阵虫鸣声,这座古都被四野的虫鸣包裹,人声有三十层楼高,虫鸣便有七十层楼高,被虫鸣托举的人的梦,则高入云天。
书衣坊的最上一层只有屋脊处高出人头,斜屋顶缓缓低下来,做成书架的山墙有半人高,过去拿书要弓腰低头。这个低矮的环境却并不压抑,有回到童年某个小小角落的孤独感觉。屋脊是旧的人字梁木结构,或是从哪个旧建筑上拆下来的,有年月了,木头上有虫洞,抑或有虫子生活其中。这个琢磨虫子的人在木梁下走动时,木头中的虫子一定能感觉到。人缓慢下来时,身体的动作会变成像虫子一样的蠕动。
〔6〕朱赢椿打开隐藏在书柜上的暗门,带我们进到一个小房间,四壁都是书,抬手可触到斜面屋顶。他又推开一扇暗门,躬身进到一个更小房间,里面人只能坐着,像虫子一样蜷曲其中。这该是他静修的和体会虫子生活的地方。
我们在有虫洞的木梁下谈论虫子。我建议朱先生在我的《本巴》和《一个人的村庄》书名设计中用虫文书体设计,想必这样一定很有意思,因为“一个人的村庄”也是一只虫的村庄,或是一条狗、一只鸡、两窝蚂蚁的村庄。不知道他最终是否采纳了我的建议。他只是对我报以诡异一笑。他笑起来时脸部表情像是虫子的。这个痴迷于虫子的人,是否会越来越像虫子呢。
〔7〕三年前,我在南京师大附中讲过一堂大课,讲到我们书院的虫子。每年暑假都有孩子来书院学习,书院虫子多,都不咬人。我教孩子们接受这些小虫子,你喜欢听虫鸣,就得接受虫子在身边爬,偶尔爬过你的手臂,它只是在过路,让它过去便可。我们和虫子都在往秋天走,是形影相伴的同路,我们并不比虫子走得更远。
那堂课,我把遥远地方的风声和虫鸣带给了孩子们。在后来的对话部分中,一位学生说他读了我的所有作品,并提了很有见地的问题。我被一个中学生知己感动。我和学生的对话部分后来整理出来,发表在《语文学习》上。
〔8〕我在长篇小说《捎话》中,写了一位通晓数十种语言的翻译家,最终听懂了驴叫。但他无法把驴叫翻译成人的语言说出来。他只能在最后时刻发出“昂叽昂叽”的驴叫声。
朱赢椿会不会听懂虫子的叫声呢。他把那些虫子的生命轨迹,当一种符号去研究时,他和虫子间便建立起一种个人联系。江南水乡的无尽虫声,给了他一颗难得的虫心。这颗心或许会被虫子感知。或许虫子永远不会知道有一个人在想着做着虫子的事情。千千万万的虫子在地上爬,总有一些虫子爬到人心里,被养起来。
〔9〕“我在三十年前虫子爬过的路上,听见你走来的消息。”
这是我以《江格尔》史诗为背景写作的新小说《本巴》中的句子。
我们都在虫子千百年来走过的路上。我们和虫子一样往时间深处走,没有谁走得更快更慢,也没有谁走得更长或更短。我从遥远新疆,落脚就能踩到蚂蚁的木垒书院,飞到烟花三月的瘦西湖边,依然看见遍地蚂蚁在跑。我跑了一万里,还是没有跑出虫子的世界。
〔10〕在虫子的缓慢蠕动里,所有的快都没有意义。一只细小蠕动的虫子,会拖住整个世界的后腿,以免它跑丢掉。
那日在秦淮河边饮酒,我听见岸边各种各样的虫声,一层一层,密密麻麻,下层的虫声显然老得嗓子嘶哑,依然顽强地叫。上层的虫声和着桨声水声,往夜深处传。在我们耗尽长夜的推杯换盏中,虫子已经老掉了一层又一层。
从西北到江南,每一寸土地上都有虫子在爬。虫鸣连接起的山陵大地,和熙攘人声连接起的城市村庄,是同一个世界。
〔11〕写这些文字时,我已回到新疆木垒书院的虫鸣中,我书案的踏脚是一根两米多长的松树干,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虫文。当年我选用这根松木干,正是因为虫子给它刺绣了好看的花纹,树皮扒开,虫子留下的纹路雕刻般清晰。虫子先我走过了一棵树。我脚踩它写作好多年,偶尔低头看见虫文,再抬头写我的小说散文时,或许已经不一样。
我把木干上的虫文拍照发给朱赢椿看,他说精致极了。
我说,虫迹看久了都像是神迹。
在金佛山遇见自己
一
〔12〕在金佛山景区入口处,他们指着对面一道山脊说,那是佛头,那是佛身。我看了看,只是山,并没有他们所说的佛。可能我佛缘浅,不能看啥都是佛。也可能眼前的山并没造化出我想象的佛相来。
其实我是不屑看那些像佛的山的。人心中有佛,佛一定生着人心的样子。那些有鼻子有眼的山形,只是像人而已。山若成佛,也未必躺成人的模样,它或立或卧,或高耸云天或逶迤千里,都再自然不过。一座像人的山却不自然了。
但我却在金佛山看见一座像我的山。
〔13〕我们沿密林中的木栈道前行,金佛山似有无尽的生长力,草木长得茂盛拥挤,让人感觉透不过气来,却个个活得翠绿旺势。行到山顶风口处,眼前豁然开朗,刚才被树木遮挡的云海显露出来。风刮得正紧。是西风。我们一行人背对风,站在悬崖边上,衣服被吹得飘起来。眼前的云也正被风掀动。从这个山口吹去的每一阵风,都造出不一般的茫茫云景来。
一座铁黑色的山峰耸在无边云海中。云把其它的山都抹去了,这座孤峰露出头来。我知道在它四周,看不见的群山正积聚在云层下方。
〔14〕从我们刚才经过的山谷,能看见那些云层下的山,它们勾肩搭背连为一体。山与山之间有一条万物生长的路,让草色和花色延绵不绝,也让村舍阡陌相连。更高的山峰耸入云中,像是要把天顶破。我们登到山顶才知道,那些看上去高耸入云的山峰,都淹没在云中找不见了。只有这一座山峰,探身到云外。它穿透了天地间的无限空虚,已在云上端坐了。
陪同者说,那是金龟山。
〔15〕此时云雾正随风翻腾,山峰时隐时现,我并没看出山的龟形来,倒是看见那峰顶酷似一个人的阔大额头,连鼻子和嘴都清晰可见。我拿手机拍了两张,拍好后看照片,竟觉得那瞬间抓拍的山形有点像我。赶紧让同伴给我拍张合影,只片刻工夫,那人形已经不在,云雾很快地修改了山峰,没被云遮住的部分,已经不再像一个人的额头。它确实像一块龟背,龟头朝北向下,像是要一跃跳下去。
山与雾,在万千变化的瞬间,雾遮去多余的部分,露出一个人的相貌来,开阔的额头,高耸的鼻子,黑铁的神情。
〔16〕其实我在看见它的瞬间便心中一怔,那不是我吗?那一瞬我似乎去了山那里,早已成为一块石头,被幻化的雾再现于另一个时空。它坐南面北,头朝后倾斜,像是靠在什么地方,但后面全是雾,它靠着空空白雾,或许只有空可以让它的头靠过去,只有虚空,盛得下那颗头颅。
离开龟背石,我们沿悬空的栈道去了趟云雾深处,栈道在云层之上,头顶既是山顶,行走其上,半个身体在浮云里,轻轻飘飘,另半个身体紧依山壁,不敢丝毫脱开和山壁的联系。金佛山栈道长十几公里,一步一景,沿着峭壁可以绕过整座山。
〔17〕我们没有走完全程,回返时带队的女士不断朝后喊,都回来了吧。后面只有回音。人之间全是雾。说出的话也雾蒙蒙的。我们都疑惑地回望,栈道淹没在云中,刚刚穿云走去的一行人,又穿云回来。总觉得有一个人没有回来。又觉得那没有回来的人像是自己。
再次经过写有龟背石的地方,再朝浮云中的龟背石望,云雾还在不住地升腾翻滚,那山峰也不断地随雾造型。但刚刚过去的那一瞬不会再现。我在这里观看一天,或一年,龟背石都不会再幻化出一个像我的人形来。那个瞬间的我已经永远消失了。剩下的时间里,山还是山,露出云海的山脊还是像龟背,它俯身朝下,在往深渊里驮载深渊。
〔18〕回来后反复看那张照片,那座云雾中的山,越加地像我了。
那该是活成一座山的我。
我在人群中每一次的仰头,每一回的挺直胸脯,每一刻的孤傲清高,我都活成了我的山峰。它陡峭,奇崛,独对云天。
我把这样的我藏在深山。
更多时候我匍匐在地,为草木低头,对尘埃俯首,向陪伴自己到老的岁月弯腰。
一个活成人形的我,已经平常得连衰老都跟别人一模一样了。
但我仍然会看山。每一回抬眼看山时,我的脊背都像山一样挺起来。
二
〔19〕一定还有活成一棵树形的我,在这山里长了百年千年,反反复复的死去活来。某一刻我坐在树下乘凉,并不知道我正坐在自己的阴凉里。树在它的年轮中等来我。而我并没有认出它。
我靠在树干上打盹时,我的瞌睡中有它的醒。它一棵树一棵树地醒过来,去年前年,更早年月的树,都醒过来。一棵树在时间的山野里长成自己的森林。我在人世活成无数个自己。我的每一个梦每一个瞬间的想法,都分叉成另一个我。我被自己的人群淹没,又在其中恍惚地认出那个独一的自己。
〔20〕多少年后,我在秋风落叶中再次经过这棵树,我不会去它身旁乘凉,天气已经很凉了,但我的目光会被一地金黄的落叶吸引。一棵树在山里落尽我一世的繁华。我又在别处虚度了谁的一生。
尽管我依旧不知道,在我成为树的时光里,一个季节已然远去。树和我,将再次错过。我回去过一个人的冬天。我的寒冷不会冻坏树的一个枝条。它在山里过树的漫长日子。它再不是我。我也不再是它。
但我的衰老里一定会有一棵树的年轮。
我朝远处的叫喊中也曾有过一棵风中大树的连天呼啸。它疯狂摇动。我拼命奔跑,喊叫。
〔21〕待我走不动路,我会取它的一根树枝做拐杖。
我会躺在一棵大树里,成为自己的木头。我在人们不知道的春天里发芽。那时我的影子不再是黑色的,它不被看见地流淌成一条回忆之河,曲曲折折穿过生长着同一棵树木的辽阔山野。我在那时看见自己的人群,每一刻,每一年,每一个梦中和醒来的我,聚齐在一生的荒野。
我没说出那棵树的名字,我想在此山中隐藏一棵树。它不被人唤出名字。我的名字越被人所知,它便越无名。
〔22〕带我来的女子说,“这棵树年年结小红果,好吃极了,但我从未吃到过一颗。”
“为什么呢?”我望着她好看的眼睛问。
“这些鸟儿,盯着树上的每颗果子,红熟一颗吃掉一颗,半颗都不会留给人。”
“你明年来,它会留给你一颗。”
“那你明年再来,我还陪你上山。这些鸟儿,或许真的会吃剩下一颗呢。”
“树会多结出一颗红果,留给你。”我替那棵树做了许诺,但这个许诺分明又是我的。
我每时每刻说的话,都长成了它的繁茂枝叶,它的“沙沙”声响在所有的季节里。
我每年每月的沉默,都深埋成它的根系。
而我在秋天里红透果实等待的那个人,或许只是另一个我。
他已经来过。
三
〔23〕还有活成一棵草药的我吧。
金佛山被当成草药库,每行一步都可与一样草药相遇。随行女士给我介绍沿途那些草药的名字,许多名字熟悉却从未见过。我小时候家里有繁体竖排版的中医书,先父留下的,我记住许多草药的名字和药性,也早早地知道了人要得的所有的病。我曾有机会去学中药,悬壶济世。但最终当了一个胡思乱想的写书人。草药的名字却一直没敢忘记,总觉得它们是一生中迟早要遇见的贵人,为我以后要得的一样病而生。我一年年的终会走到一株草身旁,它是我有毒身体的解药,我的命在它手里。
〔24〕每一株茂盛生长的草药,都等候着世上的某个人。他出生,长大,生活,生病。老中医给他开的方子里,有一味药长在金佛山的阳坡,有两味生在金佛山的阴洼,另有一味只在绝壁上长,不肯被人采来熬煎。
那孤冷的药草,不屑医生老病死的俗病。
它只医人间的清高,但清高不是病。
生老病死也不是病,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我的书架上有民国版的《中华药典》,有《中国中医秘方大全》《男女科5000金方》,几乎所有的草药和对症的病,都写在医书中,我迟早要得的病也在其中。
〔25〕偶尔翻看,像是在找自己的病,又给病找自己的药。那么多千奇百怪的方子。同一种病,有完全不同的药方,又有几十上百种的草药可以调剂使用。似乎只需得一样病,便可尝尽世间百草。
这是一剂给周岁小儿的处方:
鸡内金5克/神曲5克/麦芽5克/山楂5克/薏仁5克/白术7.5克/山药5克/桔梗3克/茯苓5克/苍术5克/川朴3克/枳壳3克/干草5克。
功能:消食导滞,健脾止泻。主治小儿下利不爽,大便腐臭,暖吐酸腐等症。
每日一剂,每剂熬至150毫升,分4次服完。
若伴呕吐加半夏/藿香。阵啼加砂仁/元胡。小便黄少加车前子/木通。
〔26〕十几种草药,在一起煎熬。十几种味道,熬到最后剩下一味苦。
都说良药苦口。苦口,或是草药最真实的药用,熬给人尝世间滋味的。
尝过这味苦,便没什么不甘甜了。
那苦药汤一遍遍地,经过孩子、大人和老人的口舌胃肠。
草药也是陪伴。你安好时,它长在山里,是一株草。开药味的花,结苦籽。待到体弱多病,山里山外的草都找来了,你不知道哪棵草对症你的病。医生也不知道。否则他不会抓一堆草药给你。
〔27〕一堆草里有一种是你的药。但它须和其它的草熬在一起。一样草携带几十样草,来陪伴你的病。一样草太孤单,一味汤太苦寒。必须是十味百味杂陈。苦熬着苦,酸甜辣也熬在苦里。这样的滋味应是人生的悲欣交集了。
一碗药汤送走的人,带着满口苦味,转世在草药里,开苦花,结不忍给鸟儿啄食的苦涩果实,把最苦的根茎深埋。
还是被人刨出来。
女士指着坡地一棵独秆植物说,这是鬼独摇草。
早年我读到过这个名字,但想象不出它的样子。如今见到了,竟和医书中描述的一样:此草独茎而叶攒其端,无风自动,故曰鬼独摇草。
〔28〕那棵草似乎听到有人叫,微微动了下身子。它知道自己在人世有一个名字,人唤着名字到山里找它,去治胆怯害怕的病。
鬼独摇草学名天麻。
它就长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本想采一株回去,熬汤服了。只是动了心念。我被自己的念头吓住。仿佛内心里有一个跟随多年的我不知道的惧怕,突然在一棵疗治惧怕的药草边,显现出来。
我小时候怕鬼,晚上睡觉都拿被子蒙着头。后来有一天突然不怕了,开始四处找鬼。想知道那个让自己害怕的鬼长什么样子。
〔29〕再后来,我知道鬼活在我的念头里。
人的每个念头里都住着一个鬼。那些鬼迟早会出来。
我用一个个无鬼的念头把有鬼的念头压住。或把鬼念头带到远处扔掉,自己脱身回来。但那个把鬼扔掉的远处也在自己心里。对于念头来说,多远都是一念间的事。
此时一株鬼独摇草,又让我看见自己曾经的害怕。
或是我曾经的恐惧早已投生为一株鬼独摇草,孤独的秆儿,末端举一簇花叶,摇摇欲坠,生着担惊受怕的样子,人却要拿它治惊恐病。不知道它会不会被人的惊恐吓住。
〔30〕千千万万的草药长在山中,我是它们中的谁呢。
在我孤苦伶仃的前世,我一定是此山里孤傲不群的独活,不长多余的枝,不跟别的草合伙,生着不让人喜欢的味,探向高处的白色花簇,只在风中自言自语。
我在今生里忘记多少人和事,才能让那永远不会忘记的人说一句“勿忘我”。
曾经有女子说我是她的毒药。说完后她静悄悄地走了。她去找时间的解药。遗忘也是药。回想也是。我菜地的一角种有茴香,我在什么都想不起来的下午,摘一枝闻闻。它特别的香味里都是往事。
〔31〕我会在世间所有的味道中,唯一尝出你的香味。我会为此忧伤。
而医治我旷世忧伤的长生草,长在金佛山云雾缠绕的峭壁上。它在雾里开花,雾里结籽。我比山高的忧伤,只有看不见的遥远星光可以疗治。
但星光不是药,它是人最需要的仰望。
就像所有的药都医治不了人的死亡。
死亡不是病,它是安息。
当我积蓄够人世的苦,就去做山洼里的黄连。我尝过黄连的叶子和根茎。在我少年时生活的河湾洼地,隐秘而孤独地生长着一丛黄连。只有少数的人知道。更多的不知苦甜地活着的人,最苦的黄连不让他们尝见。
〔32〕我曾因病去看过老中医,他干枯的手指,按在我年轻有力的手腕上。他摸过的脉大多已经平息,我的脉还在堂堂跳动。他摸出我有很长的命,有的是时光去得许多的病。他留给我一册发黄的繁体字的手抄秘方,说我要得的病都在里面,方子也在里面。多少年来我一直给自己号脉,左手按住右腕,又右手按左腕。都说医者不自医。但我有无数个我。一个我生病时,无数个我在对面,他们长成山中草药,长成树,长成一座座山。
我的命在他们那里。
夏花与秋叶
〔33〕二〇〇九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印度访问,参观了泰戈尔故居。那是一栋红色的二层小楼,屋外有一个不大的花园。刚下过雨,花园的树木、石板小路、屋墙都湿漉漉的。当我移步到泰戈尔生前的居室时,突然有了一种干燥的感觉。
泰戈尔故居的房间都很小,一间挨一间,许多的门,总觉得其中有一扇门会通到他的诗歌世界里。
卧室比其它房间大,一张双人床,靠着南墙。白色床单盖在被褥上。床头墙壁上挂着诗人临终前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泰戈尔,正躺在这张床上,大睁的眼睛里满是无助和恐惧。
我被他的眼神吓住了。
〔34〕泰戈尔是诗人也是哲学家,曾创作出版过六十六部诗集,还有数量众多的中短篇长篇小说和剧本散文,一九一三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思想深受佛教、印度教及早期婆罗门教的影响。哲学和宗教,曾给他内心注入过那么丰富的关于死亡的超脱与思考。但是,我从这张照片上,看到他临终前的表情与普通人无异。我在他眼睛中看见所有人面对死亡时的无助和恐惧,这样的表情,是属于人类,我们都在这样离开,有信仰的人和无信仰的人,有思想和无思想的人,死亡将人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勇敢者、懦夫、领袖、平民、有钱人、穷人,在死亡面前归为一样。
〔35〕这时我回想诗人那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泰戈尔写下这两句美丽诗句时,死亡离他尚远。他正享受着生之绚烂。“夏花”之后,自是秋风落叶。他遥想自己的“死如秋叶之静美”。可是,人生的秋日何其漫长,尤其对于活了八十多岁的泰戈尔来说,他的生命在六十岁便已入秋了,从那时起到他临终前,那枚叫泰戈尔的秋叶,落了二十年,终于要落到地上了。生命剩下最后的时刻。他有过八十年的漫长生命,可是,剩下的时光却已经短得抓不住。
〔36〕这时候,已经过去的那漫长的八十年,和仅剩的几个月,或更短的几个小时,甚至临终前的几分钟,哪个更长。
我们活掉的漫长岁月让生命变得如此短促,一生中的每一分一秒,每一年,都在把自己往最后的时刻递送。
当生命到达,活掉的一生算谁的呢。如果活过的生命才是自己的,那么,越到生命的终点,人生应该越长。但是,这个长人得有时间回头去看。都说人生是一次性的,没有回头路。但每一次的回忆,每一刻的回望,都让人生有了第二次,第三次。
〔37〕写了无数不朽诗篇的泰戈尔,他最后的临近死亡的眼神,却不会被自己提前写出来。此时属于自己的夏花与秋叶,在一个人巨大的生命之上,汇合成无声的绚烂与静美。那是一个伟大诗人的,也是普通人的。
同样是印度哲人奥修,我年轻时几乎读过他所有的书。他谈哲学,谈宗教,谈中国古诗词中的禅意,尤其他对佛教生死轮回的解读,让我有了开阔的生命观和永生意识。他曾超度过自己的父亲,说他父亲的意识已经加入浩大的宇宙意识流中。他提示人们有意识地死去,或在临死前有人引领,让其意识不至于散失尘间。死亡有其永生的意识,也有其坠入尘土的无意识。他说经他引领,他父亲的魂已经在永生中了。
〔38〕可是,我最后看见了他的死。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他临死前哭喊得像一个孩子,他对死亡的说教都是给别人的,因为他的死亡未到跟前。他想象着人类灵魂的永恒,内心经过修炼的灵魂和意识,在死后加入运行在宇宙的大意识中,不生不灭。
不知道他最后看见了什么。或者没看见什么。
他没有像自己教导别人的那样安静地死去。或许他看见了自己的死亡,却没有看见来接迎自己的宇宙的意识流。
〔39〕他用最后的时光和气力,哭出了声音,流出了眼泪。
这哭声和眼泪,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哲思。
他以往对死亡与轮回的文字中,超然得没有一滴眼泪,他临终时把它补上了。
这是在死亡面前最真实的奥修。
但我依然相信他追求永生的超然思想。那些来自印度教、佛教又被一个智者重新感悟和建构的生命观,依然会吸引我和更多的读者。
奥修最后的哭啼是身体的本能,他的精神早已远遁。
——《大地上的家乡》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