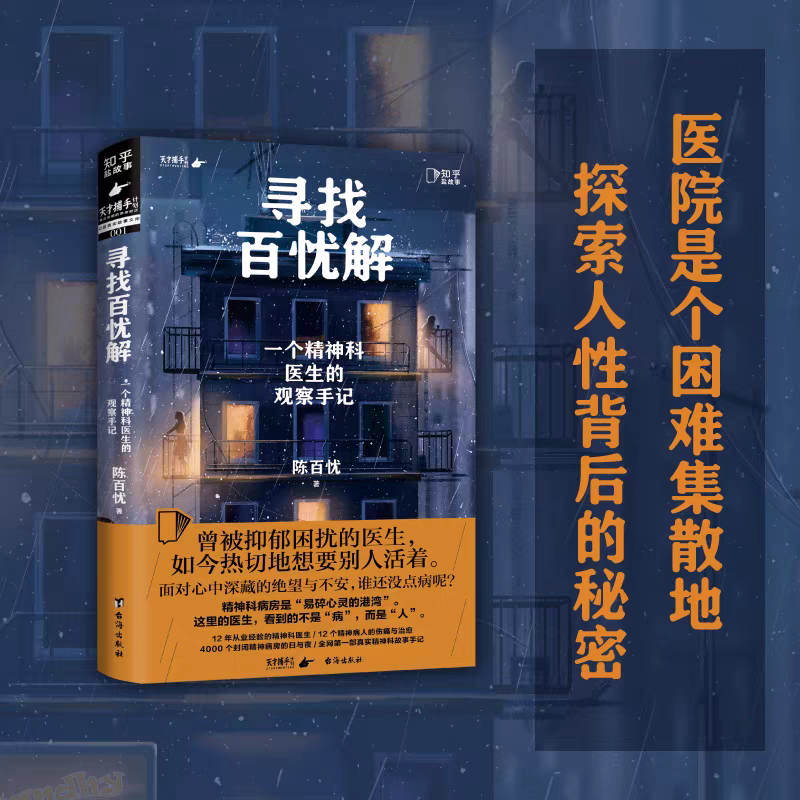
〔1〕从我们精神科建立之初就住进来的段慧来,15年来一天都没离开过。她把自己活成了“院霸”。2010年7月,我刚毕业,被分到远离市区的山脚下的精神科封闭病房,就被这个“院霸”给“盯上”了。
01
那天下午我走进女病房活动室,三四个患者正在里面看电视。她们都隔着至少一个位置坐着,不扎堆。精神病人大部分都性格孤僻,平常也很少两个人挨着坐。我也找了个靠门的位置坐下,想说点啥,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就跟着她们一起看电视。我喜欢观察,也记得老师的话,应该多和精神病人待在一起。也就几分钟后,一个女患者突然主动换到我旁边的座位,挨着我,问:“你是新分来的研究生吗?是正式的吗?医大毕业的?”病房里好几个女患者都长得差不多,我刚来,还不太能分清她们谁是谁,但见有人主动来跟我说话,我还挺高兴的,赶紧回答:“对啊,刚毕业的。”
〔2〕后来我总回忆,单从这段对话看,完全是朋友间拉家常,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但接下来就不一样了,这个女病人听了我的回答,突然变得激动,乐得跳了起来,还拍着手,大声说:“太好了!”这反应明显“过度”,我心里直犯嘀咕,但想起之前同门师姐跟我说的要多观察,从患者身上能学到从书上学不到的东西,于是就顺着说:“还行吧。”紧接着,毫无征兆地,这个女患者竟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起整个精神科里之前各种鲜为人知的“八卦”:“当年有个姓李的男大夫偷偷给楼上戒酒的患者带酒,被主任抓住了就给开除了,那个人是个临时工。”“还有护理员谁谁谁,她让我干活我才不给她干呢,她也是个临时工。”
…………
〔3〕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久,她讲的“本院八卦史”时间跨度长,涉及人物众多,细节鲜活丰富,条理清晰,还有点评——虽然很多评论如刚见面评论我一样,是围绕“身份”二字的——没想到,我在精神病科上的第一课,老师竟然是个女病人。听着听着,我对面前这个女人的困惑越来越多了:这么正常的一个人为什么在精神病科里呢?或者说,她是一个精神病人吗?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跟我聊了一下午天的女人就是本院“院霸”。
第二天一早,我刚迈进病房,一个女人热情的大嗓门就喊起来,就像老店里的店小二——“陈大夫来啦!”之后的好几天,这个女精神病人没事就站在那个门口,只要我一经过就大声地跟我打招呼,那声音在病房与走道久久回荡,异常突兀。每次查房,她还拼命地向我眨眼睛,就好像我和她之间有什么秘密似的。——她是病房里最热情却最孤独,病情最轻却住了最久的人。
02
〔4〕“一定是段慧来!”师姐听说我这两天碰上个异常热情的女患者,非常笃定地得出结论,“病房里就没有她不知道的事,护理员们都叫她‘院霸’呢。”
“为啥叫‘院霸’?”
“你慢慢观察吧。”师姐故意不回答。精神病人大多情感淡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能聊天的很少,我有点庆幸难得遇上这么一个“热情”的病人。
但我还是太年轻了,当时没理解师姐的话背后的深意,就觉得这个女人挺有趣,那天下午不忙时就去病房找她了,这一找,没想到“戏”越来越多。
段慧来继续热情高涨,她不断地拿出她的零食“存货”让我吃,我不吃,她就说,陈大夫不爱吃薯片啊,那吃糖吗?她又拿出一袋糖。我实在让不过,就拿了颗大白兔奶糖放在嘴里。
〔5〕我们医院远离市区,买不着东西,钱在院里是花不出去的,日常用品都需要家属探视的时候带来,所以吃的用的在患者那里都很珍贵。之前有病人家属给病人带了一只烤鸭,病人去水房洗手,回来就发现烤鸭被其他病人偷吃了。除了“偷吃”的,还经常有“偷烟”的。患者手上有没有水果、零食,就体现了患者家属来的次数和对患者的重视程度。这个段慧来算是病房里的“富婆”了。她的箱子、柜子上放着挺多吃的。我心想,家里人把她照顾得挺好啊,怪不得性格这么好。她见我吃了大白兔奶糖,终于满意了,又开始兴奋地拍手。她一高兴就会乐得拍手,一拍手我就感觉有点夸张做作,想到这儿我又提醒自己,这里是精神病科。
〔6〕“陈大夫,我儿子比你大3岁,特别优秀,也是研究生毕业,现在在一个重点学校当老师。”段慧来贴着我坐在床边,献宝似的跟我说,一脸骄傲。接着,她甚至来抓我的手,要给我看手相。我并不排斥与女患者的肢体接触,患者喜欢你才会跟你亲近,特别是精神病患者。只是这个“院霸”段慧来的语气让我摸不准她想做什么——而且她什么时候打听到我的年龄的?她仔细打量着我手指头上“簸箕”的数,说陈大夫你的命挺好。然后她突然抬手拨弄起我的头发,说,陈大夫的头发好黑啊。
那天下午,她真是拐弯抹角、处心积虑地跟我聊了很久,最后我有点明白她的意思了——“院霸”是想让我给她儿子当女朋友!
03
〔7〕“原来你不光被段慧来‘盯上’,还被‘看上’了。”师姐的玩笑、段慧来的纠缠把我弄得开始尴尬了。尴尬是尴尬,不过关于这个女人的一切我都很好奇:她状况稳定,没有过激行为,“零食”也充裕,那么在家人的看护下完全可以回家,怎么就把自己混成了住得最久的“院霸”?
我很快就见识到了“院霸”的厉害。我以为,段慧来让我做儿媳妇的事只是说说,只要我不回应,慢慢也就过去了,所以那之后我渐渐减少了去病房找段慧来的次数。谁知道她真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有天查房的时候,一个新来的患者突然问我:你是不是段慧来儿子的女朋友?我说谁说的,她说她听其他患者说的。
〔8〕这怎么还传上谣了?我知道事态严重了。了解了一圈,很快知道了“院霸”经常会在一段时间内“盯上”某个人。有时候是新来的患者,有时候是轮转的大夫,比如,刚毕业的我。被她盯上的人都会陷入这样的怪圈:一开始会被她的热情感染,和她亲近,但渐渐就会对她“敬而远之”。
有个女患者缺了四颗上牙,笑的时候总是会用手捂住嘴巴,怕被人笑话。可段慧来偏偏最喜欢在新来的患者面前指着那个女患者大声宣布——“她没有门牙!”然后还要让人家展示,说:“谁谁谁,你笑一个,让大家看看你是不是没有牙。”人家不干,下意识地捂住嘴,段慧来就蹿上去硬要把人家挡住嘴的手拽下来,俩女人差点打起来。
〔9〕她还会毫不留情地告发自己藏药的“同胞”。精神病患者大多需要经年累月地吃药,日复一日,没个头,藏药的人很多。但我们这儿是重症病房,里面的患者大都曾给家里惹过麻烦。曾有一个男患者在幻觉的支配下把他嫂子杀了,放进衣柜里。
警察有时也会来我们这儿确认谁谁谁某段时间是不是在这儿住院,一般都是本地发生了严重的暴力案件,怀疑是精神病人所为。所以吃药在我们精神病院病房是头等大事。每天晚上八点,我们准时发药,跟患者的“斗智斗勇”也开始了:医生、护士、护工三个人一起去,患者排着队一个一个吃完药之后把嘴张开给我们检查。我们曾怀疑一个女患者藏药,可是一直抓不到。后来,就是这个“院霸”段慧来举报,对方有个巨大的龋齿,每次吃药的时候都会用舌头把药推到龋洞里去,回到病房再用牙签挑出来。我们据此一举抓获了“藏药现场”。
〔10〕碰上有患者家属来探视,段慧来就更来劲了。不论是哪个患者欺负人,还是谁家的患者被人欺负了,不管是不是她亲眼看见的,她都要上去跟家属告状。有时候明明是我们已经解决了,双方也都取得原谅的问题,对方家属一来她还是要再翻出来添油加醋说一通。我渐渐萌生了一种感觉:这女人即使没有生病,也是个不招人待见的人吧。哪有人会较真、认死理、反复纠缠一件事,甚至没事找事到她这样让人尴尬、难堪的地步呢?
“她儿子确实挺优秀的,要不你考虑考虑?”我至今还记得师姐的调侃。
04
〔11〕我的担心很快就在自己身上应验了。有天赶上我发药,段慧来一见是我,又提儿媳妇那茬——“我不想吃药了,你给我儿子当女朋友我就吃。”
“我见都没见过你儿子,怎么答应?”我耐下心思好好回答。见我不答应,段慧来坚决不肯吃药,她一犯倔我就拿她没办法了。后来,这种情况越发严重,她经常用“给我儿子做女朋友”这个理由抗拒吃药。
一起发药的护士比较有经验,警告她:“你不吃药就让主任收拾你!”谁知段慧来突然破口大骂,一改刚才的任性风格,扯着嗓子喊主任的名字,让全楼道的人都听得见:“李××!我才不怕他呢!”主任真出马了,他说你再这样我就给你儿子打电话了。段慧来竟然立马消停了。段慧来在我们这儿基本软硬不吃,但只要一说打电话找她儿子告状,她的气焰就会软下来。
原来叱咤风云的“院霸”的软肋是儿子。
〔12〕可我上班很久了,这个让段慧来时刻惦记的优秀儿子从没露过面。每月来看段慧来的只有一个女人,她姐姐。姐姐比她大3岁,姐妹俩长得挺像,都身材高挑、苗条,眉眼也很像,只是姐姐看起来更柔和。但姐妹俩其实并不亲。姐姐说,段慧来从小就能歌善舞,跳舞都是最前面领舞的,合唱也总是领唱,学习也好,样样都拔尖。大家都觉得这个孩子长大了会有出息。而她自己是不怎么起眼的那个,先结了婚,嫁了个“成分”不怎么好的人,婚后好几年都没生孩子,妹妹段慧来因此还说过她是“不会下蛋的母鸡”。亲妹妹说自己的闲话,姐姐心里当然不怎么好受,所以姐妹俩只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去父母家见面,私下不来往。
“怪就怪她太要强,认死理这个性格害了她。”姐姐没明着说,但段慧来的表现和她过往的经历让我慢慢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这个女人之后的日子很可能还会继续在精神病院里度过。就因为她追求的“要强”与“正常”,在别人眼里都过了火。
05
〔13〕段慧来那个时代上大学还靠推荐,虽然她拼命表现,但还是没有被推荐上。后来恢复高考后她又报名考了一次,也没有考上。段慧来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家待了几个月,不洗头不洗澡,每天门都不出。
那个时候她父亲身体不太好,就提前退休让段慧来去接了铁路上的班。但因为不符合当时的条件,段慧来只能先当“临时工”,这对骄傲要强的段慧来而言“委屈”了。
听到这里,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第一次见面她就问我是不是有正式编制的,曾经那个年月正式工有编制,又是铁路系统,是多大的荣耀与人生保证啊!估计不亚于现在别人问你在北上广“有没有房”。
〔14〕好在因为能歌善舞,段慧来被安排到工会搞各种文艺活动。工会有个领导挺喜欢这个能说会道的小姑娘,想给她介绍个对象。但因为男方希望找一个带编制的,最后跟一个“处处不如段慧来”,可就是有编制的女孩在一起了——她又被卡在了编制上。那个女孩本来和段慧来关系也不错,但和男孩结婚以后,段慧来开始故意跟那个女孩吵架,两个人再也不说话了。
段慧来继续逮着机会就“表现”,经常被评为先进,后来还入了党。因为表现突出,段慧来终于有了编制,成了正式的工人。
〔15〕我想起段慧来和护工吵架的时候经常骂人家“临时工”。她从1989年开始就住在我们院里的精神病科,价值观也停在了那个年代,可见她依然咽不下当年那口气。时代的局限很强地折射到这个女人的身上了。每次看到她,我总觉得她不像个精神病人,但她又好像只能生活在精神病院里。
有了编制的段慧来像多年媳妇熬成婆了似的开启了“反转人生”,她开始专门指指点点那些临时工,在单位的人缘也越来越差了。婚姻方面,错过了之前的那个男孩,段慧来挺仓促就结了婚,婚后不久就生了孩子。本来以为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一个意外彻底改变了段慧来的人生。
〔16〕1989年刚过年不久,段慧来正在铁道上走着,一列原本停着的火车突然向她开去。慌乱中,她倒在了铁轨中间。她在两根铁轨的夹缝中眼睁睁看着火车从她身上呼啸而过。火车并没有轧着她,但铁轨之下的段慧来吓得浑身瘫软,一动不能动,是铁路上的同事把她抬回去的。段慧来在床上躺了好多天,不敢闭眼睛,一闭上就能看到火车头向她开过来。
从精神科专业来说,这是标准的PTSD,就是有名的“战后创伤综合征”。在这种疾病的影响下,人的警觉性会增高,脾气会变得暴躁,睡不着觉,很多人酗酒甚至吸毒只为了麻痹自己、缓解痛苦。比如,很多经历过战争的人后来听到鞭炮声都会立刻卧倒。段慧来直到意外过后的好几个月,一听到火车鸣笛还会抖得迈不开腿,这其实不难理解,也可以应对。
我总是想,如果当时有人有这方面的知识,多给她一些陪伴和开导,也许认死理的段慧来就不会走到下一步了。
06
〔17〕段慧来搬进了院里的一间空病房,因为儿子。
我们科的小楼建造年代久远,经常需要修缮。那间病房因为暖气漏水,修了几次都没弄好,比别的屋子冷很多,一直没人住。她跟谁也没说,自己半夜就搬进去了。护理员发现了让她搬回去,她又拿“护理员是临时工,没资格管她”㨃了回去。
段慧来这次受刺激的直接原因是儿子。儿子是小学老师,一年通常只来医院看她两次,寒假一次,暑假一次。这次儿子要出去学习,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来了。盼不来儿子的段慧来“犯病”了,开始来回倒腾她箱子里的东西。段慧来住院的时间长,东西也比别人多,她以前单位分的房子动迁了,段慧来没有了可以回的地方,即使暂时用不上的东西也没有地方可以放。所以别的患者只有一个箱子,她有好几个。
〔18〕于是,一个有点怪异的场景出现了——一个女人在那间阴冷、漏水的空房间里,一边翻腾着箱子,一边哼唱着歌,像个快活得即将远行的人。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那个一片高粱,十里哟荷塘,十里果香……”
她的歌声真的很美,我完全被打动了,站在门口,不忍进去打扰她。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理我,把东西堆得满床都是,忙得不亦乐乎。
铁路是国营单位,福利待遇都不错,段慧来住院期间的费用由单位会计来医院定期结算。长期病假工资虽然少,但也一直给她发着。她的工资卡由姐姐拿着,也够给她儿子交学费。她用那笔动迁款给儿子的新房付了首付。
〔19〕所以从实际情况来说,段慧来虽然长期住在精神病院,但对自己儿子也算尽到了抚养的义务。反观这个儿子,快过年了,我也上班好几个月了,他和母亲就在同一个城市,有什么要紧的差走之前连半天来看妈妈的时间都没有?我有点难过,也无法理解。
直到一年后的一天,我远远看见一对“母子”从远处往病房这边走,儿子的手上拎了好多东西。走近了我才发现,是段慧来的姐姐,她后面跟着个瘦高的小伙,应该是段慧来的儿子。想起段慧来曾经撮合我和她儿子,我有点尴尬,明明什么都没有,却还是觉得不自在。
〔20〕段慧来终于等来了儿子,她的目光一刻也不愿意从儿子身上挪开,有点想去拉儿子的手,但看着儿子挺严肃的,就把手又缩回来了。她非常高兴,嘴角抑制不住地往上扬。“北京学习怎么样?都瘦了,要多吃点,工作不要太辛苦。”段慧来一个问题接着一个,他儿子淡淡地答了几句,就跟着我出了病房。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我问他。“就记得她和我爸打架,总是打。电视都砸了。”当时电视可是家里一个大件,“砸电视”这事给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
“那你恨她吗?”我确实想知道答案。
07
〔21〕“火车意外”过了两个月,段慧来终于缓过来一些了,但她觉得这件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这是事故,自己差点死了,必须有人为此负责。段慧来去找段长要说法,让段长开除当天那个开火车的司机。段长却打圆场说那个司机也不是故意的,已经批评过了,还写了检讨,罚了款。“咱就算了吧,今年的奖给你。”
段慧来不干。她成天跟着段长,他走一步她跟一步。大家都认为段慧来在无理取闹。一方面她并没有受伤,也没啥损失,还有补偿;另一方面如果要处理司机,就得上报,这种安全事故一上报,全段的“先进评优”都会被取消,受损失的是大家。段长没办法,找来段慧来的老公让他回家劝劝自己老婆。
〔22〕造成事故的司机也提着东西去找段慧来的老公,请他喝酒。可段慧来依然不依不饶,坚持要个说法。老公搞不定自己老婆,又在同一个单位,这么小个地方属实觉得没面子。时间一长,老公怨气也来了:“你毛都没伤着一根!”没有一个人支持段慧来,老公不支持,父母也不支持。父亲说当初为了让她转正,段长是帮了忙的。加上她平时人缘就不好,好多人因为这事在看她笑话。
因为段里“不管”,段慧来最终闹到了局里。第一次见局长,局长还算客气,听她说完情况之后说一定会严肃处理,让她回去等消息。因为段慧来闹得凶,全段没有一个人得“先进”,大家的话越说越难听,段里说她长期不上班,严重违纪,要把她调去打扫卫生。
〔23〕老公也被单位领导约谈,说段慧来如果再继续闹,就把他的工作也停了。老公心情郁闷,出去喝酒,喝了酒话就更难听了,两个人频繁吵架,动不动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砸得稀巴烂,甚至把新买的电视都砸了,有一次他还对段慧来动了手。后来老公干脆不回家了,段慧来就说老公在外面有人了,但也没有证据。俩人在1991年离了婚。当时儿子已经10岁了,段慧来抢着要了儿子。没过多久,段慧来老公就又结婚并且生了孩子,两人再也没有了联系。
段慧来父亲的病也越发严重了。段慧来众叛亲离,在单位只能做打扫卫生的工作。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糟糕,她不在单位食堂吃饭,说饭菜里有毒,有人要害死她,她老公也和那些人是一伙的。
〔24〕后来发展成说单位的人早就商量好要开车轧死她;渐渐地,她走在大街上遇到陌生人,就说人家骂她不正经;电视里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她也说人家是在提醒她要当心……
一向重视外貌的段慧来再也没有心思收拾自己,成天披头散发,不成人样。大家都觉得她“疯了”。
一语成谶。1989年快入冬的时候,距离意外发生大半年了,一天局长在回家的时候,段慧来不知道从哪儿蹿出来,拿着菜刀就向局长砍去。半年过去了,那个司机还是没有被处理,她觉得局长骗了她,于是跟踪局长,想要同归于尽。好在局长躲开了,她只砍碎了旁边的一棵白菜。段慧来很快被周围的人制服,真的被精神病院的车拉走了。
〔25〕其实,我慢慢有点理解段慧来了,她固执甚至偏执地要砍领导以便要个“说法”,一方面是面子问题,我这个能歌善舞,各方面都优秀的姑娘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下出这样吓人、难堪的事故?另一方面,也许她除了怕火车,更是怕有人——特别是她骂过的临时工们——加害自己。她的光荣竟然都是靠这点正式工有编制的身份支撑起来的,现在看来有点可笑,可在当时,编制本身就是铁饭碗,一劳永逸,命运迥异,没有人不在意。只是段慧来的在意重了点,也久了点。
每个精神病人做的事都有自己的道理,每个选择也都有因有果。我时常觉得,听她们各异的故事,循着“果”去探寻“因”,就会发现那些症结的“因”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情绪:压力、执念、失落、不甘,只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出于心理和生理上的原因,没能很好地调节,才走向了极端。
〔26〕从1993年开始,段慧来开始长期住精神病院。除了病情更严重以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段慧来的父母在1993年前后都去世了,再也没有人能照顾她了。因为和人合不来,她先后换过好几家医院。2000年3月我们医院成立了精神科病房,和铁路上有合作,段慧来是最早进来的十几个患者之一。段慧来把自己混成了“院霸”,她在这里肆无忌惮地炫耀自己正式工的身份,讽刺“临时工”,再也没人能制止或加害她了。她安全了。
08
〔27〕儿子走后,段慧来还是很兴奋,晚上发药的时候又跟我使眼色,问我:“我儿子是不是很帅?”我笑着说:“确实很帅。”段慧来露出一个满意的表情。
“如果你不配合,我就给你儿子打电话。”我开玩笑威胁她。“你跟李主任学坏了。”段慧来头脑清楚,心情很好,也跟我开起玩笑,像个大姐。她倚在办公室和病房之间的那道门上,看见谁都打招呼,打听着别人的一切。新来的家属有时候会给她带点吃的,让她帮忙照顾自己的亲人,我终于知道了她的零食就是这么“攒”出来的。
病房里的患者来来回回的,但从没有人来接段慧来,并非她的病情比别人严重,而是她没有地方可以回。
〔28〕就这样过了两三年。一天下午,段慧来的儿子突然来了,还牵着一个女孩。“她叫小刘,是单位同事,我们下个月办婚礼。”段慧来的儿子开门见山地介绍,女孩也挺大方地叫了“妈”。
儿子走后,段慧来又开始来回倒腾她的那些箱子,不过我总觉得这一次她不是犯病了。她仔细地翻着她的那些衣服,不断地试穿着,还专门跑去水房里照镜子。我突然明白了,她是准备参加儿子的婚礼吧!
没想到段慧来的希望却引来了一场新的战争。
听说段慧来儿子要结婚了,“院霸”的“仇人”孙艳玲打心眼里不痛快。看段慧来天天一件接一件地试穿衣服,孙艳玲就更看不下去了。她们两个同一天住进来,朝夕相处,就好像照镜子似的,深知彼此的一切,又互相看不起。
〔29〕之前她们几乎每天都会吵架,起因可以是任何小事,一吵就是一天,一吵就相互揭短。比如如果段慧来去上厕所,看见孙艳玲在里面,那她就不上了。发药的时候,排队也必须一个排头一个排尾,不然她们就会吵。
孙艳玲比“院霸”多一个症状,幻听。幻听又叫凭空闻语,明明没有人说话,但是她就是能听到声音,并且对这个声音毫不怀疑。这是精神病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孙艳玲总是能听到段慧来骂她。“儿子”是这两个妈妈“互殴”的最大焦点。孙艳玲也有一个儿子,但由她老公抚养。老公在她犯病的时候和她离了婚,也是再没有来往。十多年,她儿子一次都没来看过她。以前段慧来经常刺激孙艳玲,说,“你儿子多大了?”“你儿子啥时候来看你啊?”
〔30〕没想到这一次让孙艳玲逮着机会了,我想她所有的心思都在段慧来会不会被邀请参加婚礼上,当然段慧来肯定会更加焦急地等待。
下个月很快便到,最终,只有姐姐来看段慧来,并给科里送了喜糖。儿子的婚礼没有邀请段慧来,儿子也没再露面。吃到喜糖的那天,“仇人”孙艳玲故意问段慧来:“你咋不换衣服了呢?”段慧来没有说话,第一次没有骂回去。我猜想段慧来不是不说,是憋在了心里。
有一天晚上吃完晚饭,段慧来说饭盒太油了,想去打点热水刷饭盒。开水桶在外面,平时都是护理员用水壶接了水放了温水再拎进去,但段慧来一直挺稳定的,护理员没有多想就给她开了门。她用饭盒接了一饭盒开水,就径直往孙艳玲的病房走去。
〔31〕孙艳玲正躺在病床上,段慧来把一饭盒热水全泼到了孙艳玲的脸和脖子上,瞬间起了好多大水泡。孙艳玲疼得大叫,段慧来在一边气势汹汹地骂道:“你还胡说八道不?”看着段慧来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我一下想到了段慧来当年用菜刀砍局长时的画面。让人有点不寒而栗。她这次是真的被戳到痛处了。
第二天,主任找到段慧来,还是用老手段威胁她,要给她儿子打电话。“打就打呗。”这回她满不在乎。这是第一次用儿子“威胁”段慧来无效。主任还是叫来了段慧来的儿子,让她儿子赔偿孙艳玲,并且要求段慧来出院。没想到这下换孙艳玲跑来求情了:“我错了,我不该胡说八道。”然后她又对主任说:“我已经原谅段慧来了。”因为孙艳玲的坚持,段慧来没有被撵出院。两个人之后还是时不时吵架,但关于儿子和家庭,她们都“很给对方面子”地不再提了。
09
〔32〕对于自己的生命,段慧来似乎就留在火车驶过,以及领导不认错、不给说法的时候,再也没有向前。而她延续的希望,应该都来自自己的儿子。
我想起段慧来姐姐之前叹着气说:“大人没什么,孩子可怜啊。”段慧来的姐姐只有个女儿,比段慧来的儿子小好几岁,一家人早就把段慧来的儿子当自己儿子养。孩子很感激,也很努力。身边的每个人似乎都从这场意外中脱身往前走了,只有段慧来还留在原地。我想起第一次见段慧来儿子时问的那个问题,你恨她吗?段慧来的儿子回答:“我同学都以为大姨就是我妈妈。”他几乎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妈妈是个精神病人。他的世界里仿佛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叫“段慧来”的人,又或者他很不想承认一个这样的母亲的存在。
〔33〕段慧来被所有人抛弃了,彻底成了精神病院里的“院霸”。只是我也说不好,在她的生命里,“成为精神病患”和“被抛弃”到底哪个在先。
在我印象里,段慧来只有过一个朋友,那是一个刚刚生完孩子没多久有孕产期精神障碍的患者,叫李雪。因为别的房间住满了,李雪一来就住进了段慧来那个漏雨的单间。没想到她们两个竟然一见如故,一天到晚有说不完的话,天天手拉着手坐在活动室里看电视,互相编辫子——精神科病房的生活很单调,互相编辫子是女患者之间最常见的表达友谊的方式。
〔34〕有一天,李雪老公来看她,不知道为什么李雪突然犯病,上去就给了她老公一个耳光。一旁的段慧来立刻跳到凳子上,一上一下地举起手来喊:“大家说打得好不好?”底下有病人跟着起哄:“打得好!”段慧来又喊:“要不要再来一个!”众人喊,“要!”于是李雪又打了她老公一个耳光。我们赶紧把李雪的老公带出了病房,李雪还在屋里大骂:“你才是精神病!大夫你也给他做检查,把他也关进来,让他也住院!”
李雪的老公挨打的时候没有躲,挨骂的时候也没有回嘴,一直有风度地退让着。他临走的时候还跟我们说,你们这个工作真是不容易。
〔35〕一个情绪稳定、行为成熟的家人,比医术高超的精神科医生更能治愈患者。李雪的病情恢复得特别好,她没过多久就出院了,出院后还专门回来看过段慧来,这是我知道的段慧来唯一的朋友。
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段慧来在遇上事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包容、理智的家人陪在身边,也许段慧来不会到今天这一步。她住了多少年精神病院,就紧追了并不放那列火车、那场改变命运的“错误”多少年,直追到把身边人都远远甩在身后,直追到只剩自己孤身一人,要一个说法。或许在李雪的身上,“院霸”看到了自己不断被驱离的那个“家”本来的样子。
10
〔36〕2015年10月,精神科要搬回市里,不再保留封闭病房了。所有的患者都要被送到其他地方。当时有几个医院备选,大部分患者都是家属替他们选,段慧来自己给自己选了安宁医院。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孙艳玲选了另外一家医院。她们终于分开了。
我去病房看段慧来,她正在来回倒腾她的那几只箱子,把一件东西放进A箱子,想了想,又拿出来装进B箱子,一会儿又觉得不妥,拿出来放进C箱子。她姐姐在一旁站着等她。
像是时光倒流,我一下又回到那天被她的歌声吸引,站在她的门口看着她穿着挺厚的棉衣在那间比别的屋子都冷的屋子里,一边精心挑选着箱子里的衣服,一边哼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
〔37〕“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那个一片高粱,十里哟荷塘,十里果香……”段慧来的姐姐说得没错,她唱歌是好听的。欢快的歌声仿佛把我带到了童年的故乡,看到了在田野里奔跑着放风筝的自己。一瞬间我竟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我们看来她是犯病了,可说不定她正自娱自乐地享受呢,享受在她定义的“正常”的世界里。
好一会儿,段慧来才打包好,跟我们说再见。望着安宁医院的面包车开出大门,我想,她这一辈子大概都会在精神病院里度过吧,虽然她病得不重。
〔38〕我时常会想起段慧来,但回忆里她“院霸”的气息似乎慢慢消退。其实我从认识她开始就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她究竟是不是一个“精神病人”?我承认我想得挺苦恼的。
在我看来,段慧来的人生在那次火车事故之后其实就停止了,后来的希望只在回忆与儿子身上延续,但最终,前夫与儿子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没有认可、接纳以及帮助她。
段慧来转走后,我有时候开会碰到安宁医院的医生,他们总会跟我抱怨说,你们医院来的那个段慧来也太能折腾了,怎么总惹事啊。段慧来揪着不放的那些事,说到底其实都没错,但可能只有在精神病院里,一个人才能被允许这么“认死理”,这么向往“正常”。而我们要做的,或许是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点理解,接纳每一种生命绽放的姿态。想起段慧来之前倚在门口大声跟我打招呼的样子,我有点想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