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限戏鲸习读专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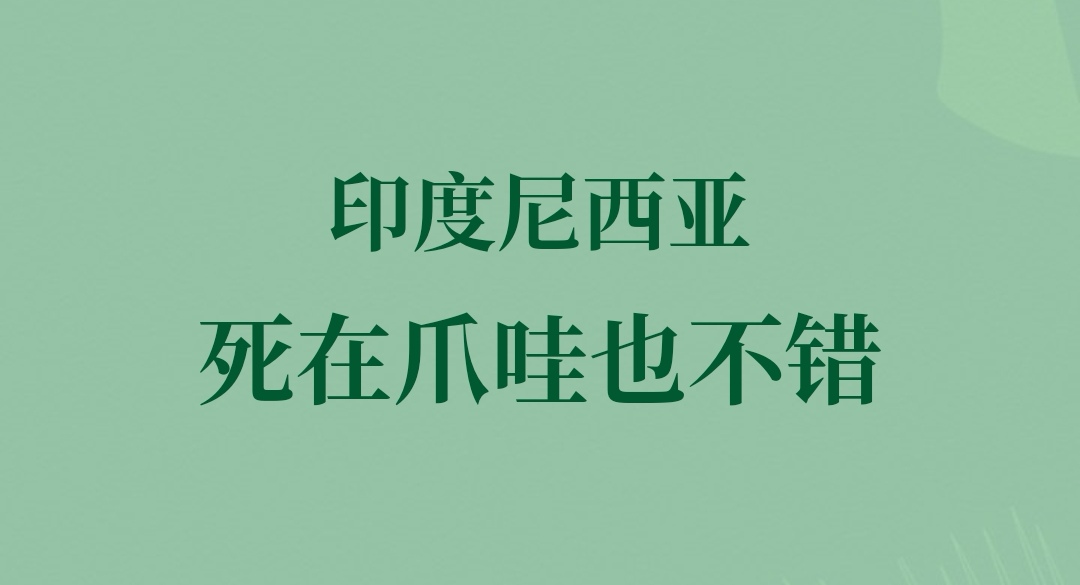 中
中
1.
从雅加达前往日惹,是在穆斯林斋月的第一天。
前晚,我刚在“天吧”喝过酒,清早就在《雅加达邮报》英文版上看到政府发出的警告。上面写着,有些极端分子专挑斋月开始时袭击外国人光顾的酒吧——看上去并不是开玩笑,因为近几年雅加达和巴厘岛都发生过针对使馆和涉外酒店的恐怖袭击案,搞得高档酒店全都如临大敌,除了围上防冲撞的铁栏,进入车辆也得接受全面防爆检查。
我就是在这样的日子赶往日惹,坐的是早上出发的特快列车。因为担心斋月期间吃不上饭,我特意买好水和面包,准备在火车上见机行事。
2.
雅加达到日惹五百六十多公里,要开八个小时。所幸座位够宽敞,也没有吵闹的小孩。我一上车就戴上耳机,一边优哉游哉地听音乐,一边看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亚的小说。窗外是一晃而过的清真寺,稻田像华北平原上的一样辽阔,笼罩着一层薄雾状的火山灰。勉强算得上问题的,一是窗户打不开,二是空调开到了冷冻室的温度。一些有备而来的印尼人甚至裹上毛毯,穿上皮衣——对热带人民来说,这温度确实够受的。
虽然是斋月首日,吃饭并没有想象的困难。中午一到饭点,列车员就主动推来餐车,有鸡腿、炒饭、泡面。几桌头戴纱巾的穆斯林也毫不在乎地大吃起来。比起中东和马来西亚,印尼的穆斯林算是相对温和的,不过在斋月第一天就这么公然地吃吃喝喝,会不会也有点“顶风作案”的意思呢?
3.
进入中爪哇,风景为之一变。之前一望无际的平原,忽然被植被葱郁茂盛的山峦代替。天空压着极低的云,铅灰色的溪水,流过黑色的火山岩。雨水很快落下,像泪水流过车窗,也摇荡着路边的芭蕉树。
我想起在雅加达参观伊斯蒂赫拉尔大清真寺时也在下雨。这座清真寺建成于1978年,能同时容纳二十多万名信众。当时正是中午,阿拉伯文的唱经声透过宣礼塔响彻天空。一瞬间,整个雅加达都显得驯服而安静。我光着脚走进清真寺,在阿訇的带领下,静静地观看。那些虔诚的祈祷者面对麦加的方向跪拜,然而阿拉伯世界的真主,真的能听到他们的祈祷吗?
4.
早在7世纪,穆斯林商人就从阿拉伯半岛源源不断地来到印尼,但是直到12世纪末,并没有多少印尼人皈依伊斯兰教。或许在17世纪之前,伊斯兰教都不是印尼的主要宗教。13世纪,苏门答腊北部港口国巴塞的国王改信伊斯兰教,成为第一批皈依该教的印尼统治者。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伊斯兰教沿着海上贸易通道加速传播,其他国家也开始皈依该教。15世纪末,在爪哇北部海岸线上,伊斯兰教王国淡目国建立,杜班、锦石等地都皈依伊斯兰教。在西爪哇,井里汶苏丹国也独立出来。第一批皈依伊斯兰教的统治者,是由于与外界的穆斯林群体发生接触,其他邦国改变信仰则是被征服的缘故。到17世纪,伊斯兰教开始渗入内地,并扩张到爪哇和苏门答腊内地的大部分地区。自那以后,它便持续向整个印度尼西亚扩散。
5.
如今,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却并非伊斯兰国家。被很多人视为一种妥协的潘查希拉[插图]是这个国家的哲学纲领。苏加诺曾将它阐述为“西方民主、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和国内乡土传统的结合体”,并写入宪法。在苏哈托时期,它更被上升为祷文的高度。虽然一些伊斯兰政党曾试图让遵守伊斯兰教法成为宪法义务,但国会于2002年拒绝了这一提议。苏哈托也曾经明确宣布伊斯兰教法不具备法律效力——尽管该教法的某些元素,仍为部分城市和地区所奉行。
潘查希拉倡导一种包容的哲学和天下一家的思想。这或许解释了伊斯蒂赫拉尔大清真寺的设计者为什么是一位天主教建筑师。当我走出大清真寺,发现仅仅一街之隔的马路对面,就是建于1901年的雅加达天主教大教堂哥特式的双尖顶。
6.
然而,不管拥抱哪种文明——我不乏偏见地认为——印尼人都是在进入别人的世界,而与他们自己的世界渐行渐远。
在伊斯兰教来到之前,印度教和佛教控制着印度尼西亚的各个主要地区。位于苏门答腊南部的室利佛逝国信仰佛教,它在公元7世纪开始出现在唐朝的典籍中。据说,它是一个统一但时常迁都的王国,国中的水手可以在苏门答腊岛和爪哇海周围各港口搜集胡椒、象牙、树脂、羽毛、龟壳、珍珠,然后把它们带到中国,再从中国带回丝绸、陶瓷和铁器。
7.
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一书里,唐朝高僧义净记述了在室利佛逝国学习梵语的情形。显然,他对那里印象颇佳,于是告诉其他“留学僧”,若去印度求法,先到室利佛逝学一两年预科是不错的选择。
印度文明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宗教。当时的统治者也接受了印度的王权观念以及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对于统治者来说,印度文明无疑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他们之所以愿意接受,是因为领会到其中的功利价值。他们邀请婆罗门祭司进入宫廷,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建造辉煌的宗教建筑,因为宗教也能大大提高他们自身的权威。这也正是婆罗浮屠被建造起来的本质原因。
8.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婆罗浮屠都是爪哇岛上最著名的旅行地——它离日惹只有四十公里,然而到了才发现,游客并不太多,兜售纪念品的小贩也不如想象中凶猛。大概因为是斋月,大家饿着肚子没力气干活,很多商铺都空空荡荡,店主也不见踪影。不过后来去附近的村子,又发现很多年轻人在无所事事地玩鸽子,可见现实是复杂的。
亚洲的佛教遗迹我去过不少,从已经基本损毁的鹿野苑,到保存完好的吴哥窟,可只有婆罗浮屠给我一种完全超然物外的感觉。和当地人聊天,他们对本地旅游业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你来也好,不来也罢,无期待也就无痛苦。不过反过来说,较之很多执着于招揽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婆罗浮屠的姿态更让我受用。毕竟这地方在火山灰下埋了近千年,有种空寂、苍茫感才正常。
9.
在售票处围上表达尊敬的纱笼,喝了免费奉送的咖啡,顺着公园一样的林荫路一直走,便是婆罗浮屠。初看上去,婆罗浮屠似乎比想象中的小,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发出一声赞叹。如果从天空俯瞰,婆罗浮屠的结构是一个三维的曼陀罗,代表佛教万象森列、圆融有序的宇宙。实际看上去,它更像一个外星人留下的神秘遗迹。婆罗浮屠的早期历史依然成谜。人们只知道它是由当时统治中爪哇的夏连特拉王朝,在公元750年至850年间的某个时候建造的。至于因何而建,哪里请来的工匠,费时多久,如今都已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中。
10.
婆罗浮屠建在岩石山上,该山海拔二百六十五米,被已经干透的湖床所环绕。1931年,一位荷兰裔印度教学者提出,建造者起初将婆罗浮屠设想为一朵莲花,正处于当时还有水的湖中。后来,学者们通过对沉积物和花粉的研究,证明婆罗浮屠附近确实存在湖泊,莲花理论因此可能成真。再加上附近有默拉皮火山——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它和河流合力,使“莲花”周围的湖水时有时无。
11.
婆罗浮屠由两百万块石块建成,毫不夸张地说,几乎覆盖整座小山。可以想见,建造这样的东西,要耗费多少人力和物力。然而离奇的是,在婆罗浮屠完工后不久,夏连特拉王朝就被他国攻破。该国王子逃往苏门答腊,入赘室利佛逝国,而夏连特拉的势力被逐出中爪哇。这座伟大的建筑在建成后便遭到历史的遗弃,甚至连它何时被遗弃,其间有过何种盛景,为何被遗弃,都无人得知。
我想象着这里荒草萋萋的景象。只有不远处的默拉皮火山注视着一切。它不时爆发,使婆罗浮屠的地基整体性下沉,最终埋在厚厚的火山灰中,又被四周疯长的热带丛林掩盖。
它被遗忘了近十个世纪,甚少爪哇文献记录过它的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本是一个古代帝国“永不陷落”的标志,但却被证明徒劳无功——一如历史所一再证明的。
12.
直到1815年,英国人托马斯·斯坦福德·来福士爵士(来福士广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也是第一本爪哇历史著作的作者)派遣人手,才重新发现这座沉睡千年的佛塔。之后,荷兰人开始对婆罗浮屠进行修复,但发现支撑建筑的山体早已浸水,巨大的石块群也已陷落。荷兰人离开后,婆罗浮屠的修复暂告停滞,刚刚获得独立的印尼人正忙着建设国家,无暇顾及这片早就被祖先遗弃的土地。到1973年,政府仍然无力修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支付两千五百万美元,耗时十年,才最终将婆罗浮屠修复完成。
13.
婆罗浮屠变成爪哇乃至印度尼西亚的骄傲。我在官方的宣传册子上看到,它与中国的长城、印度的泰姬陵、柬埔寨的吴哥窟,并称为“古代东方的四大奇迹”。然而与前三者不同的是,婆罗浮屠已经无法被它的人民完全理解。人们惊叹于它的工艺,骄傲于先人的智慧,可是工艺之下那个曾经繁盛一时的佛教文明已经在爪哇彻底消失——这里现在是伊斯兰教的世界,而宇宙间只有一个真主——安拉。
14.
1985年1月21日,婆罗浮屠的九座舍利塔被九枚炸弹严重损坏。1991年,一位穆斯林盲人宣教士被指控策划了包括这次袭击在内的一系列爆炸案件,因此遭到终身监禁。我站在婆罗浮屠的顶层,看到佛陀慈悲微笑,眼前是绵延的群山、低垂的天际线和茂密的棕榈林。
日落以后,天空布满星星,昆虫和青蛙的鸣叫不绝于耳。我在婆罗浮屠对面山上的茅草屋里,吃烤羊眼肉,喝葡萄酒,雾霭下的热带丛林美得令人窒息。突然之间,散落在群山间的村子开始晚祷,整个世界几乎同时响起伊斯兰教的唱经声。那个拖着长音的男性咏叹调,通过宣礼塔伸向四方的喇叭,漫山遍野,水一般地弥漫。
15.
祈祷一直持续到深夜。现实的后果是我那晚几乎一夜未眠。斋月就是这样厉害。
第二天傍晚时分,我回到日惹。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湿润得带点木瓜味。马尔巴罗公爵大街上依然人山人海,猫在其中悠然穿梭。卖蛇皮果的小贩似在沉思什么,街头大提琴师即兴弹奏着一首小夜曲,任由你把几枚硬币,扔进敞开的琴盒。
路边是一家接一家、绵延几公里的露天餐厅。人们席地而坐,分享着沙爹肉串和印尼炒饭,不时啜饮扎啤杯里加满冰块的红茶。这似乎是中爪哇地区最流行的用餐方式——露天、席地、手抓。一种随意的气氛在城市街头蔓延。对旅行者来说,也是难得一见的风景。
16.
旅途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在一个全然自足又壁垒森严、态度轻松又个性鲜明的地方停靠片刻——日惹或许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至少和雅加达相比,日惹更像是爪哇的灵魂。这里的爪哇语最地道,文化传统最鲜明,老规矩数不胜数。它完全独立,甚至拥有自己的海关,皇室仍然住在皇宫最深处,由穿着传统服饰的老家臣服侍。它是苏丹统治的特区——或许也是爪哇最后一个城邦。
我参观了苏丹的皇宫。这个独特的区域犹如一座带有城墙的城市,里面生活着大约两万五千人,有自己的市场、商店、蜡染、银器作坊、学校和清真寺。大约有一千名当地居民被苏丹雇用。皇宫分前后院,前院是旧时苏丹上朝处,有殿阁和庭院,后院是嫔妃们的住所。后院的大门旁立有两尊石雕,右边是巴劳巴达,代表善良,左边是金卡拉巴拉,代表邪恶。
17.
大殿内,加麦兰编钟乐队正在弹奏“叮叮咚咚”的古乐。中国式的凉亭里,宫廷诗人依然日复一日地唱诵史诗。那本史诗是如此厚重,以至必须放在一张茶几一样的小桌子上。年迈的诗人盘腿坐在桌前,打开台灯,偌大的凉亭里只有他孤单的身影。他开始唱诵,声音抑扬顿挫,歌颂着皇室和神明——那是伊斯兰教来到之前的声音。我很快发现,他完全无视那些窥探、凝视,甚至快要趴在地上按快门的游客。他的注意力从不移开,脸上有一种高贵的漠然——一种在皇宫内待久了的人才会有的骄傲。
18.
我在皇宫里随意步行,看到腰间别着格利斯短剑的侍卫,身着传统的“巴迪克”蜡染服,裹着纱笼。他们一定已经在宫里干了大半辈子,如今都垂垂老矣,盘腿坐在走廊前的蒲团上,有的发呆,有的闭目养神,像村委会门口一群晒太阳的老大爷。我望着他们,想象他们在皇宫里的漫长一生。他们护卫着国王,年轻时一定还护卫过国王的父亲。这个国家的思考方式或许被现代化的浪潮不断席卷,可在这里,在这些老侍卫身上,我看到一种恒常之物——这正是日惹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19.
这座宫殿由哈孟古·布沃诺(意为“宇宙位于我的膝上”)一世修造,现在住在里面的是哈孟古·布沃诺十世。唯一让人迷惑甚至会心一笑的,只有挂在走廊前的木牌,上面用英语写着:禁止与侍卫合影……
此时,我看到四名宫女托着银盘进入后厨。这是国王的午餐,依然按照古老的传统,由试菜师验证无毒后,才能呈进。侍女们大概五十岁开外,穿着朴素,长相也很难称得上端庄,不过这不是拍摄电视剧的外景,而是现实。虽然每月只从苏丹那里领到微薄的津贴,但她们认为,到宫里服务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一些当地农民在农闲时也常来宫里谋差事,还有很多人自愿来宫里服务。在日惹人眼中,只要能在皇宫里干活,哪怕是临时工,也是一件体面的事。
20.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感同身受。一群马来西亚华人就表现得不屑一顾,认为那不过是“封建势力复辟”。连国王最喜欢的斑鸠鸟,他们也避之不及——“那声音可不吉利!”
在爪哇,并非每次发现都是快乐的。因为风景过于斑驳,现象错综复杂。如果你试图找到一种思考框架,使所见的一切如星座般各安其位,那结果多半是让头脑变得更加混乱。
从伊斯兰教的角度理解一切,或许会容易很多,可惜它到达这里的时间还不足以形成文明。在雅加达国家博物馆里,我甚至无法找到与伊斯兰教相关的任何内容——馆里展出的只是土著文化和各个时期留下的佛像。
21.
我乘巴士前往普兰巴南,这里是印度教的遗迹,位于日惹东北十八公里。和婆罗浮屠的命运一样,普兰巴南建成后不久就被遗弃,然后在历次火山爆发、地震和偷盗中,化为悲剧性的废墟。
寺庙群紧挨着公路主干道,即使站在路边远眺,大湿婆神庙的尖顶也甚为壮观。实际走进去,发现仍有大片倒塌的石块,被听之任之地散落、堆积在原地。大量断手断脚、无法修复的佛像立在草地上,像屠杀过后的现场。
环绕大湿婆神庙的走廊内壁上,雕刻着《罗摩衍那》中的场景,讲述的是罗摩王子的妻子悉多如何被诱拐,以及猴神哈奴曼如何找到并解救她的故事。这个故事仍然作为爪哇传统戏剧的一部分,在普兰巴南村的露天剧场上演。然而普兰巴南村已是一个标准的伊斯兰教村落。
22.
有一则传闻说,1965年苏哈托军事政变后不久,要求每个国民申报自己的宗教信仰,普兰巴南的村民一度感到十分踌躇。他们是穆斯林,然而又感到自己不能这么申报——因为违背了太多伊斯兰教戒律。他们了解到自己的祖先建造了伟大的普兰巴南寺庙群,尽管其背后的文明已无从知晓,但他们知道这和印度教有关。他们也知道,平时喜欢看的哇扬戏,很多情节也来自印度史诗。于是有村民提出一个设想:他们应该申报自己信仰印度教。
可是问题也接踵而来。最主要的一条是,他们不清楚信仰印度教应该做什么,对印度教的历史或仪轨都一无所知。于是他们请来巴厘岛的印度教祭师,教授他们印度教的常识,可最终发现过去已无法重建,文明一旦丢弃,就不可能再轻易地捡起。于是,他们只好申报自己信仰伊斯兰教。
23.
从博物馆的旧照里,我看到1885年荷兰人发现这里时的情景。当时,这里是一片更加荒凉的废墟,到处长满荒草,野象横行,而那些荷兰人迷茫地坐在石头上。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迷茫我能够感同身受。一个如此宏大的建筑被轻易地遗弃,一种压倒性的文明彻底消失,无论谁也难以理解。即使是拥有现代化机械的今天,想完全修复普兰巴南也困难重重,更何况在古代?那需要多么大的信心、恒心和毅力?
我深深地感到,这里展示的不是文明,而是文明的丧失,是一种被时间遗弃的力量。那些已然倒塌的是现实,而那些被好意修复的,与其说是保存现实,不如说像镜子一样映照出现实的残酷。
24.
对我来说,同样残酷的现实是,在苦等一个多小时后,被告知开往梭罗的商务列车坏了,不得不换乘无空调亦无座位的普通列车。我蜷缩在行李箱上,看着对面一个表情忧郁的中年人:牛仔裤、黑色T恤、冒牌Hugo Boss夹克衫。稻田依然无休无止,可车门无论如何无法关闭。也许应该庆幸才对,因为风顺着门缝涌进闷热的车厢,如同上天的恩赐。
——这才是爪哇,我心想,一个在现实性中运转的国度。那天晚上,我无所事事地去梭罗剧场看戏。买的VIP票,合人民币两元。当我捏着软软的票根走进去时,发现剧场已经坐了一大半人。有些人在睡觉,有些人在接吻,一个戴着头巾的漂亮女子在左顾右盼。我坐到她身边,可她很快就起身离去。
25.
戏是爪哇传统戏,散发着印度史诗的诙谐与荒诞。散场出来已是10点多,可剧场外依然热闹非凡:一群下国际象棋的光脚男子,一支演奏流行歌曲的业余乐队,几个练习英语发音的大学生,各种各样的沉思者。透过头顶的树叶,新月洒下它的光辉,可兴致勃勃的人们毫无散去的迹象。回酒店的路上,经过城市的主干道。我惊奇地发现,大街两侧停满摩托车,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坐在、躺在、靠在马路牙子上。
我的第一反应是“肯定出什么事了”,但是很快发现,每个人的表情都那么无辜、闲散、寂寞,还带着一点青春期的迷惘。
我问出租车司机,他们在干什么?
“Just for fun.(只是为了好玩。)”司机耸耸肩告诉我。
26.杀青段
从梭罗再次乘上列车,向东赶往庞越,这回需要九个小时。爪哇只是印度尼西亚的第四大岛,但实际走起来,才真切地感受到——那也是相当遥远的距离。
茶色玻璃外是近乎“永恒”状态的稻田,平平坦坦,却看不到任何现代化机械,全由人力和畜力耕种。手头的《雅加达邮报》上说,美国国会规定2015年前,三分之一的地面战斗将使用机器人,但看看近在眼前的爪哇农民,不由得感到一种违和感。另外,从西到东一路走过来,感觉爪哇就像一座巨大的粮仓(它也确实被荷兰、日本当作粮仓侵略过)。如今虽然天下太平,可这样的身份也不是“国家独立”或“和平崛起”能够轻易改变的。
未完待续 …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