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限戏鲸习读专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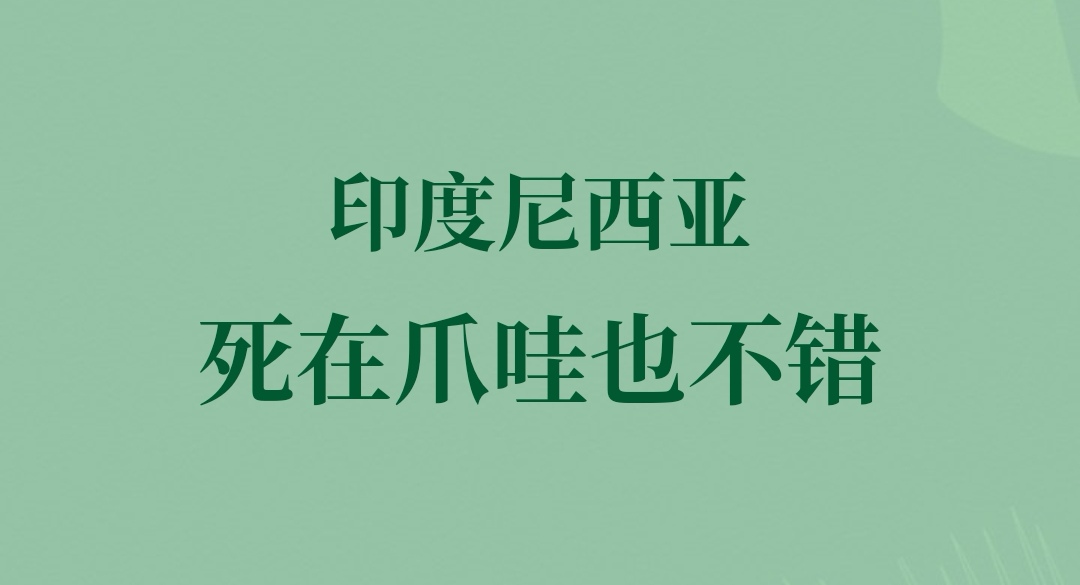 下
下
1.
火车经过泗水,这是东爪哇的首府,从火车上看,仿佛是连绵不断的棚户屋所组成的钢铁集合体。等待开闸的浩荡人群,骑着摩托车,无一例外地面无表情。不时经过污染严重的小溪,有孩子蹲在水边独自玩耍,太阳煌煌地照着。我想起普拉姆迪亚的小说《人世间》就是以泗水为背景:少年明克进入荷兰人开的贵族学校,在爪哇传统与西方文明的撕扯中逐渐成长。此书被称为印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然而一百多年过去,这种撕扯依然存在。
2.
傍晚到达庞越,不幸的是,开往布罗莫火山的巴士已经停运,只好包车前往。不用说,要价高得惊人(合人民币一百八十元),只是也没有可以替代的选项。从庞越到布罗莫火山所在的塞莫拉旺小镇,走山路还要近两个小时。赤道地区天黑早,我怕耽误时间,虽然明知被老板索要了高价,也无可奈何。
司机小哥是一个看起来松松垮垮的年轻人,叼着烟卷,双眼通红,说他刚从赌桌下来,我也一点都不会吃惊。车是印尼产的硬邦邦的吉普,舒适度照例不佳,不过这点自我安慰一下就好。
3.
暮色中,我们穿行在玉米疯长的陌生小镇。伊斯兰教的唱经声在天空回荡,路边烤串的烟气四下弥漫。小哥开得很慢,又不时减速,与碰到的任何人(或牲畜)吹口哨,打招呼,然后告诉我:“My friend.(我的朋友。)”
不到半小时,车就没油了。无奈之下,只好掉头回去。小哥自称“身无分文”,由我垫付油钱,他却从对面的小卖部晃出来,买了包烟,悠然点上。这里明明是加油站,墙上也明明贴着禁烟标志,可无论是谁,全都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加完油出来,天终于黑透。既已黑透,我也懒得再开口,任由司机小哥在漆黑一团的山路上,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左冲右突。车厢里一片死寂,只有风声和不断响起的刹车声。除了祈祷,我也别无他法。有时甚至想,在这个暴力性的、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上,能够平平安安地活到今天,本已近乎奇迹。
4.
小哥突然从裤袋里掏出一个U盘,插入接口,音乐陡然响起,竟是Jessie J的《价码》(“Price Tag”)。
金钱买不到满足和快乐,
我们就不能慢一点,享受当下?
我打包票这样感觉很好!
这无关金钱、金钱、金钱!
我也不需要你的金钱、金钱、金钱!
我只要你跟我舞蹈,忘掉价码……
终于到达塞莫拉旺,它就在腾格尔火山口的边缘,俯瞰着布罗莫。我顾不得挑三拣四,入住一家清教徒般的小旅馆。大概因为海拔原因,水管出水困难,可以勉强刷牙,但没法洗澡。我出去买了一瓶Bintang啤酒,坐在火山小镇自斟自饮。天上没有一颗星,远方是无穷的黑暗。
5.
翌日凌晨4点,我们被塞进一辆小型吉普,前往观测点看日出。所谓的“观测点”,在布罗莫火山旁边,海拔更高的潘南贾坎山上。如果运气够好,可以看到从古老的腾格尔火山口内崛起的布罗莫火山,它西侧的库尔西、巴托克火山,以及爪哇最高峰塞梅鲁火山(三千六百七十六米)在日出时的盛景。
吉普在黑暗中一路颠簸,透过侧面的车窗,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楚,可能感受到整个世界在迅速后退。司机是个壮实的腾格尔汉子,自如地驱使吉普躲过各种坑洼,轮不沾地往前飞驰。我紧紧握着扶手,闭上眼睛,任由脑浆组织大面积重组。那感觉像是参加追捕任务的缉毒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即将走投无路的毒贩。
6.
半小时后我们到达观测点。下面早停了十几辆同样型号的吉普。雨后春笋般的游客,不约而同地会聚到这地球的一隅,穿着防风夹克,走完登顶的最后一段路程。出租和售卖棉衣棉帽的小贩们,跑上跑下地招徕生意——观测台寒气四溢,如果不是穿了抓绒,笃定会被活活冻死(几年前发生过这样的事)。
我站在观景栏杆前静静等待。眼前是火山的谷底,但此刻一片黑暗,远方同样沉浸在更大规模的黑暗中。我想象着在地球某处,太阳已经从地平线喷薄而出,向西驱赶巨大的阴影,它的锋刃离布罗莫越来越近。但是此刻,布罗莫无疑还在沉睡。不知为什么,周围几乎没有人开口,黑暗和寒冷似乎吸走一切生气。天空适时地下起绵绵细雨,打在土上簌簌作响,像小女孩穿了大人的拖鞋乱跑。一些人离开了,但更多人选择留下。
7.
光亮的出现似乎只发生在短短的几秒钟里,却构成两个世界的分野。这时,我终于可以看清眼前的景致:近处的树木,远处的云海。但雾气过于浓重,看不到火山的踪影。普遍性的失望像癌细胞扩散一样,迅速波及每一个人。
“早知道就不来了。”
“这样的天气根本不可能看到日出。”
“当地人可不管这一套。”
“我准备走了,亲爱的,你呢?”
“多等一会儿,我们这辈子来这里的机会可能仅此一次。”人们还是开始陆续离开,规模随着腾格尔司机上来催促达到顶峰。最后整个观测台只剩下我和一个西班牙人。
“走吧。”他终于沮丧地说。
8.
可就在这个瞬间,风突然开始把晨雾驱散。我看到山谷间的云雾迅疾流窜。我们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地盯着眼前瞬息万变的景色。就在风把雾气全部吹开的短短几秒钟里,我们有幸目睹布罗莫火山和远方塞梅鲁火山被朝霞渲染的山顶。
“太美了,简直超越我的想象!”西班牙人激动地宣布。然后,新一轮的雾气便来了,瞬间吞噬眼前的一切。
回到吉普车上,我们返回火山口边缘,然后越过沙海,下探到腾格尔底部。此时天已大亮,我看到布罗莫陡峭的山体,耸立在辽阔的熔岩沙平原上——它像是一片干涸的黑色河床,荒凉而萧瑟。史前时代的地球景致,恐怕不过如此。腾格尔马夫们披着斗篷,牵着马匹,想把游客送到火山脚下,但大多数人选择步行。
9.
布罗莫火山已经近在眼前,它神秘的坑口冒出滚滚浓烟,仿佛一口烧开的大锅。我沿着落满火山灰的台阶,爬上最后几百米,直抵坑口边缘。热气和硫黄气体迎面扑来。我知道,只要顺着洞口下去,就可通向地球遥不可知的最深处。然而,纵使现代科技已经如此发达,这依然毫无可能。
山下的沙海一片苍茫,如同月球表面。一座印度教神庙兀立在沙海中央——它的位置如此突兀,造型如此古怪,以至让我感觉它是被湿婆的大手随意摆在那里。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只是匆匆过客——这里是布罗莫的领地,是神的世界。
10.
布罗莫之所以神圣,并非因为它的景观,光是它的存在就已经足够。长久以来,笃信印度教的腾格尔人就生活在对它的知晓中,并且以它作为生活的尺度。16世纪,当伊斯兰教的洪流颠覆满者伯夷王国,为了躲避灾难,腾格尔人避世于这片荒凉之地。那时,国王没有子女,王后祈求火山之神,帮助他们繁衍子嗣。神灵答应了,赐予他们二十五个孩子,但要求年龄最小且相貌英俊的男孩葬身火海,以示报答。王后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但勇敢的男孩为了整个王国,甘愿牺牲自己。不管怎么说,是火山拯救了腾格尔人。如今,每到一年一度的卡萨达节,腾格尔人依然会来到布罗莫,向火山口内投掷祭品,祈求神灵的眷顾。
11.
从火山回到塞莫拉旺,游客们纷纷乘坐早班汽车离开,有的前往泗水,有的转战巴厘岛,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小镇,顿时显得空空荡荡。只有等到傍晚,新一轮的客人才会陆续到达,然后是新一天的日出、徒步、火山探险……
我在小镇上随意漫步,发现它真的就在火山口边缘,火山的任何一次大规模喷发,都可能是灭顶之灾。然而,肥沃的火山灰上遍植着山葱,苍绿而茂盛,带着爪哇特有的勃勃生机。在爪哇,繁茂与毁灭往往只是一步之遥。
12.
一个卖毛线袜的腾格尔小贩朝我打招呼:“你好!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国人?”他连珠炮似的发问。这之后,语言不通让我们都奇异地沉默下来。我看到他穿着中国产的夹克,骑着日本产的摩托,于是递给他一根美国产的骆驼牌香烟。
气氛相当融洽。直到和我挥手告别,他才终于想起什么似的大声喊道:“要袜子吗?布罗莫纯手工!”
在无人留意的小城文多禾梭,我奇迹般地逗留了两日。也许是因为在这里找到了久违的安逸感,也许仅仅是出于旅行即将结束时的忧郁症——我几乎已经走到爪哇的最东端,在一个闻所未闻的陌生小城。这里棕榈树婆娑摇曳,海风拂面而至,清真寺开始呈现巴厘岛风格,而地里的甘蔗竭力疯长,足有两米多高,在风中簌簌摆动。
13.
旅行至此,我已总结出一种可以称之为“爪哇性”的东西:它是自发的、旺盛的、原始的、热带的、暧昧的、植物性的、永不疲倦的、混乱与秩序纠缠不清的……此刻,在文多禾梭,我感到有必要给这次旅行一个强有力的结尾。
我的目光在地图上游走,马上就锁定了旁边的伊真高原。介绍简单清晰地写道:“这片高山区森林密布,人口稀少,有很多咖啡种植园和几处与世隔绝的定居点。通往高原的道路很不理想,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前往此处的旅行者数量稀少。”
根据我在爪哇的旅行经验,连游客都极少涉足的地方,恐怕是相当“原生态”。我感到一丝隐秘的快乐,暗自做好心理准备,但“爪哇性”事件还是始料未及地发生。
14.
第二天清晨,坐上之前联系好的吉普车,我发现我雇用的司机还带上了他的“情人”。
“A friend.(一个朋友。)”他以无关痛痒的口吻介绍。
女孩说她十九岁,是旅行社新来的实习生,而司机已经四十开外,发际线明显后移。我问司机,他们是不是男女朋友。
“不不不。”他斩钉截铁地否认。
然而在路上,两个人的言行举止却没有那么斩钉截铁的说服力。即便听不懂印尼语,仅仅从他们的肢体语言看,也未免过于亲昵。
“看车!”
“有人!”
我不得不一次次发出警示,确保“爪哇性”不会成为“悲剧性”。
后来,我终于找到机会单独问女孩:“他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男朋友,”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片水蜜桃般的红晕,“是最好的朋友。”
“……”
15.
不管怎样,我们平安进入“无名之地”,连当地卡的手机信号也像断线风筝一样不见踪影。此地果然山高林密,虽然路况并不算太坏,但擦肩而过的车辆、行人都屈指可数。仔细想想,司机带女孩来这里也是用心良苦——这里风景优美,人迹罕至,又没有信号,堪称约会圣地。
吉普在狭窄的林间公路上飞驰,柠檬色的阳光透过树叶,斑斑点点地洒落一地。窗外是漫山遍野的咖啡种植园,咖啡树上结满红色的果实。自从欧洲人把咖啡引入爪哇,这里就成了重要的咖啡产地。文多禾梭那些漂亮的荷兰式房子,都是当年种植园主的私宅。
16.
此地盛产“猫屎咖啡”,是麝香猫偶尔吃下成熟的咖啡果,经消化系统排出体外所得。胃液的发酵作用,使咖啡有一种特殊的风味。不用说,经过这么一番大动干戈,每磅咖啡豆的售价也高得惊人。不过即便在此地,野生麝香猫也已相当罕见,更不要说还能被人恰好捡到它们排出体外的咖啡豆。
如今的“猫屎咖啡”都是人工养殖的麝香猫所产。这些麝香猫被关在笼子里,每天被迫吃下大量咖啡果——虽然猫也有各式各样的猫生,但只靠咖啡果果腹的猫,无论怎么看都相当凄惨。只是有需求就有市场。据说,窗外的咖啡果采摘下来后,会有一部分专门运到麝香猫养殖场,用于生产“猫屎咖啡”。
17.
我们还经过一些不大的镇子,是咖啡工人的聚居地。一致性的建筑,一致性的人生。简单聊了一下才知道,他们的祖辈都是荷兰人从苏门答腊带过来的,几代人如今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在中国似乎只是转瞬之间的事,但在日复一日的咖啡园,却感觉几乎与永远无异。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伊真火山。它是爪哇主要的硫黄采集地,拥有一个绿松石颜色的火山口含硫湖,周围环绕着陡峭的火山壁。这里的旅游并未完全开发,直白点说,几乎不存在配套设施,但是一些旅行者会来这里(似乎法国人居多,因为都在说法语),看壮观的火山湖和采集硫黄的工人。
18.
在很多人眼中,这些硫黄工人的生活堪比“人间地狱”。他们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在毒气四散的火山口采挖硫黄,然后把硫黄矿石卖给山下的制糖厂,用于制糖过程中去除蔗汁杂质的硫熏。他们先要爬三公里的陡坡到达山顶,再爬两百米的峭壁下到火山口,用最原始的方式烧硫黄,然后手拣肩挑,把八十至一百公斤的硫黄用扁担原路扛到山下。如此走完一个来回,需要三到四个小时。他们凌晨2点起床,为的是赶在毒气更加肆虐的正午之前,完成一天的工作。他们每天能挑两趟,赚大约五美元。
在上山的入口处,我看到一个写着“因故关闭”的牌子,和爪哇的大多数牌子一样,只要弯腰过去即可。接下来便是三公里长的山路,山势变化多端,坡度也时急时缓。周围是茂密的丛林,可以近距离看到长臂猿在树丛间跳跃。比起一片荒芜的布罗莫,这里更像是一个国家森林公园。
19.
天上飘着小雨,山路又湿又滑,可没什么值得抱怨的。因为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硫黄工人,扛着沉甸甸的扁担,依然健步如飞。他们没有登山鞋和登山杖,有的甚至只穿着夹脚拖鞋,人看上去也瘦瘦小小,绝不是想象中大力士的模样。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从事着这份可能是世界上最重体力,报酬却极其微薄的工作。
爬到山顶,我看到一望无际的高原。它如同沉睡的巨象,趴伏在蓝色的苍穹下,仿佛随时可以起身,把世界掀翻。通向火山口的小路破碎不堪,硫黄熏枯的植被横躺在路上,好像史前动物的遗骸。我走到火山口边缘“禁止下行”的警告牌前,看到热气蒸腾的绿色火山湖和喷发着硫黄气体的黄色矿床。在这样的高度,一切宛如魔幻电影中的冷酷仙境。
20.
这也是大部分旅行者选择在此止步的原因。如果下到湖边矿床,至少还需半个小时。那是一段艰险的攀爬,一些路段很滑,硫黄气体势不可当。据说几年前,一名法国旅行者失足坠落,就此丧生。
或许是心理作用,我感觉下去的路极为漫长,每一步都迈得十分沉重。那些硫黄工人还要把重达两百斤的硫黄背上去,所付出的辛苦可想而知。越接近火山口,硫黄气体就越猛烈,我不得不戴上在北京防霾用的口罩,才能保证呼吸,而大部分工人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们挑着扁担,挺着胸脯,极为缓慢地走着,好像电影中的慢速播放。我可以听到他们沉重而快速的喘息声和发力时的呻吟。
21.
终于到达热气蒸腾的火山口。湖水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绿松石颜色,而地热通过湖水表面释放出来,变成一片白茫茫的雾霭。在湖畔的硫黄矿上,铺设着几十条陶瓷管道,从火山口喷发出的热气通过管道形成的真空加热,大面积融化着硫黄矿。一种如血的红色液体,沿着陡坡流淌下来。一些工人正在湖边收集冷却成块的硫黄,然后用铁锹砸碎,装进篮子。
周围如此寂静,无论是湖水、矿床还是人,都悄然无声。我只能听到铁锹击打硫黄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单调地在谷底回响。
22.
我站在这场景中,久久不能开口。即便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依然感到语言的无力。我深知任何一个简单的陈述句背后,都是无法想象的艰苦现实。有人说这里是炼狱,可对每天采矿的硫黄工人来说,炼狱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同我们吃饭、散步、朝九晚五地工作一样平常。作为亚洲最大的火山坑,伊真火山的硫黄喷发量为世界之最。这被看作一种幸运。因为在人口日益密集的爪哇,城市和乡村都无法再提供更多供养。对当地人来说,挖硫黄是一份得天独厚的工作,更是一条现实的出路。工人们告诉我,在爪哇,一名普通教师的月收入不过一百美元,而他们可以拿到一百五十美元。
为了不忘记这震撼性的场景,我从地上拾起一块金黄色的硫黄晶体,用塑料袋包好带回中国。这样做并非有什么重大意义,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英雄行为”,只是为了深深铭记——在这样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生活。
23.
突然,火山湖喷发出一阵巨大的烟雾,夹着热气和硫黄气体扑面而来。工人们纷纷扔下工具,四散躲避,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感到眼前一片昏暗,泪水夺眶而出,嘴里产生一股强烈的二氧化硫的酸味。我剧烈地咳嗽着,虽然戴了口罩,也毫无作用,肺叶好像都燃烧起来。
这时,一只手把我拉向旁边的一处背风岩石——是一个硫黄工人,他看到我困在那里,便出手相助。他也在流眼泪,也在大口喘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脸上的皱纹里全是黄色粉尘。我们蹲伏在岩石下面,等待火山平息怒气。然后我鼓足勇气,爬回人间。
24.杀青段
回去的路上,吉普车经过一片林中墓地。小小的墓碑,插在落满树叶的土壤里,没有文字,亦无名无姓。是的,在爪哇,我终究没有发现绝对的事物,也没有发现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
我见识了繁华而凌乱的雅加达,也看到被刻意回避的历史。我参观了雄伟的佛塔,却发现它早在一千年前即被遗弃。我整日听到伊斯兰教的唱经声,但明白那只是一种信仰,与爪哇的文明无涉。我在人群散去的火山小镇游荡,发现它美得近乎忧郁。最终我抵达一个强有力的存在,它用人的故事告诉我,这才是爪哇的灵魂。
就这样,吉普车一路向东。我毫无知觉地睡去,醒来已到海边。
本章(上中下)三本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