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限戏鲸习读专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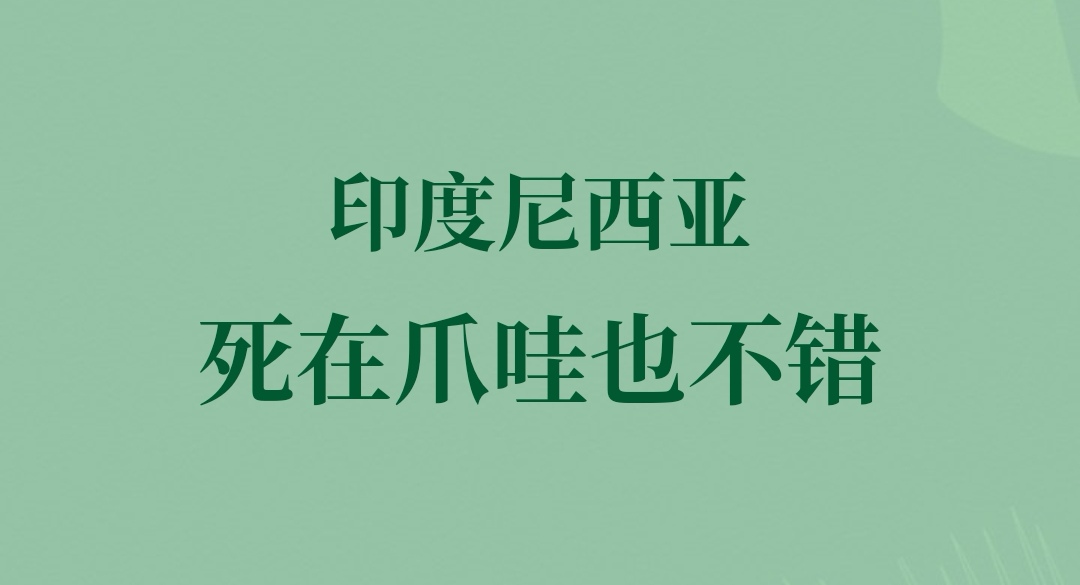 上
上
1.
在伊斯兰斋月前夜,整个雅加达仍然开门卖酒的地方只有这家“天吧”。它坐落于城市的最高处,俯瞰着可能是整个赤道地区最汹涌的夜色。那是一片带着点魔幻气息的巨大虚空,闪耀着大型跨国公司的招牌与车流构成的光带。在来到爪哇之前,我穿越了整个南中国海——然而此刻,我却很难意识到自己飞了这么远。在五十二层楼的高度,在俊男美女身边,雅加达似乎模糊了它的个性,与曼谷、西贡甚至广州达成合谋。不止一次,我狐疑地打量眼前竹笋般从雾霭中升起的高楼,试图分辨这一切和在广州四季酒店顶层的“天吧”看到的有何不同。
2.
然而,我亦深知,俯瞰一座城市是轻松惬意的,能得到的也只是明信片似的印象。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全部实质——它的历史、性格、态度——只能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离。
来到爪哇之前,我就了解到以下事实:这个国家约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雅加达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首都——这里的一天是从响彻天空的唱经声开始的。这个国家由一万七千五百零八座岛屿组成,有一百多个民族,七百多种语言,即便是人口最多的爪哇人,也是少数民族,这意味着雅加达是一盘货真价实的种族、文化、道德和体味的大杂烩。
3.
对旅行者来说,如果纽约是“大苹果”,那么雅加达就是“大榴梿”。它表皮坚硬、带刺,幽幽地散发出腥臭的甜香,让习惯者欲罢不能,却令初来者难以下咽。
这种不适感首先体现在“风”这一自然元素的匮乏上。因为地处赤道附近,风几乎很难造访此地。走在雅加达,你或许可以偶然观察到一股热气流从铁皮屋顶卷起,或在夜晚开窗时,感到一阵空气轻微的抽搐——但仅此而已,那决然算不上风,也没有风理应带给人的舒爽。
“就想想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吧,想想风吧。”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写道。在雅加达的最初几日,我的确为风的缺失愤愤不平,仿佛一项宝贵的天赋人权被无情剥夺。
4.
不适感也体现在雅加达的过分喧闹和混乱上。在这座城市,汽车和摩托车同样多,人比汽车和摩托车相加更多。2006年,爪哇人口就达到一点三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岛,而其面积却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尽管北京并不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交通优越感的地方,但是在雅加达的几日,我一边像迷途的羔羊,被裹挟在肿胀不堪的街道上,一边充满阴险的民族自豪感。这里到处是呛人的尾气和轰鸣的噪音,在热带骄阳下,有一种海市蜃楼般的不真实感。过马路则是真实的灾难,因为信号灯少之又少,斑马线则被熟视无睹。除非冒着生命危险,否则站在原地一小时也动弹不得。当地人说,他们对雅加达的交通也相当恼火,可是恼火归恼火,哪怕恨铁不成钢,也只能抱着不如忘到爪哇国的好心态。
5.
雅加达是赤道地区最强健、最活跃的经济体。在这里,我发现所有人都习惯早起。虔诚的穆斯林早起晨祷,数不清的小吃档口则趁着漫长的闷热降临前,开始一天的生意。他们奇迹般地从街头巷尾冒出,像库尔德山区里神出鬼没的游击队,让人深感没有什么力量——洪水也好,暴政也好,殖民也好——能够将这种热带植物般的生命力消灭。
不适感还体现在爪哇人独特的人情世故上。
“他是巴塔克人。”“他是爪哇人。”——在雅加达,我时常被好心人如此提醒。这并不是价值判断,也并非种族歧视,只是友情提示一个外国佬,这个国家缘何如此运转。
6.
巴塔克人,来自苏门答腊,以性格直率、热情好斗著称,爪哇人则是不同寻常的礼貌和委婉的代言人。巴塔克人和爪哇人喜欢讲同一则笑话来表达彼此的不同:在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人的脚被踩住了。此时,巴塔克人会怒目圆睁,一把推开踩脚者,爪哇人则会彬彬有礼地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冒失,但在不久的将来,我可能会用到这只脚,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您可否把您的脚移开呢?”
爪哇人总是尽量避免与人针锋相对,因此想从他们口中听到明确的判断,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比如在“天吧”,当我拿出相机准备拍照时,穿白衬衫的爪哇侍者出现了。
7.
“对不起,先生,您不能用专业相机拍照。”
“为什么?”
“这里不允许用专业相机拍照……”
“那么,可以用卡片机?”
“如果您本人作为照片前景的话……”
“什么意思?那我用手机拍一张总可以吧?”
“如果您不拍夜景的话……”
“岂有此理,不拍夜景,我拍什么?”
“如果您本人作为照片前景的话……”爪哇侍者依然有礼有节,但不屈不挠,“这是经理的规定。”
“可为什么?”
“因为本酒吧原则上不允许拍照,如果您实在想拍照,我们的建议是……”
我最终放弃了拍照,这让我和爪哇侍者都松了口气。
8.
即使抛开全球化的陈词滥调,雅加达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横亘在每到雨季就洪水泛滥的平原上,绵延数十公里,既没有中心,也很难说有什么边界。它像一件被随手扔在岸边的旧夹克,污渍斑斑,即便是那些炫目的高楼大厦,也并不标榜与之相称的文化深度,更不遮掩背后一片片灰色混凝土郊区组成的丛林。
很难相信,荷兰人曾经在这里统治过三百多年,把这里称作“巴达维亚”,古语“荷兰”之意,因为如今这里已经见不到什么荷兰人留下的痕迹。
9.
这里既没有阿姆斯特丹的从容,也缺乏后殖民学者感兴趣的“异国情调”。满大街的罗马字母,不是荷兰文,也不是英文,而是印尼文,其中一些词的词根来自梵语,暗示着爪哇与古印度文化的缥缈渊源。实际上,“雅加达”即梵语“胜利之城”的意思,尽管胜利对于这座城市来得并不算轻松。
作为印度尼西亚的首都和爪哇岛上最重要的城市,雅加达遍布雕像和革命纪念碑。它们与城市的日常生活毫不相关,建筑风格也大相径庭,可展示的情绪则是相同的:国家独立的自豪感和对宏大叙事的渴望。
10.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无比年轻的国家,其所有领土作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概念,才形成不到一个世纪。“Indonesia”这个词本身也一直鲜为人知,直到20世纪20年代,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人民,才用这个词称呼他们梦想中的独立国家。
日本军队在1942年占领印尼时废除了荷兰文字。他们命令清除所有荷兰语标志,于是荷兰在印尼三百年的统治,一夜之间土崩瓦解。随之消失的还有这个没落帝国最布尔乔亚的一切——海景酒吧、网球俱乐部、戴面纱和白手套的女士、星期日的下午茶。大约有二十万荷兰人、华人和盟军士兵被送进日军集中营,被关押者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
11.
最初,印尼人把日本人视为解放者,因为他们有限度地扶植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包括国父苏加诺在内的一批反荷志士被允许进行政治活动和民族主义演讲。
日本人还建立了印尼乡土防卫义勇军。二战结束后,这支军队的部分将领和士兵重组军事组织,与试图卷土重来的荷兰人进行了四年武装斗争,最终取得独立。也正是这支军队,在独立后的二十年里,帮助苏加诺将企图分裂国家的各种不同力量聚拢到一起。
12.
1956年访问中国后,苏加诺开始围绕更适合印尼的政治体制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想用“乡村讨论达成一致”的传统做法取代西方式民主,然而实际权力却逐步集中到他本人手中。更为辛辣的事实是,他无法带领国家走出经济低谷。
到1965年,印尼的共产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三百万,苏加诺暗中决定武装该党,作为牵制军方的力量。然而陆军战略储备部队司令苏哈托率领的军队最终占据上风。他软禁苏加诺,更以反共清洗为由大肆杀戮[插图]。十万人被捕,一百万印尼“共产党”及其支持者遭到屠杀。这场政变的残酷性前所未有,即便到今天,谈论此事的印尼人依然感到惶恐和不可思议,就像一个成年人远远打量自己青春期时无法理喻的暴力留下的阴影。
13.
苏加诺于1970年病逝。在很多印尼人看来,他是一位风度翩翩、富有魅力的政治家。他也“不负众望”地娶了四个老婆,其中一个还是日本酒吧的女招待,情人则更多。他是印度尼西亚的缔造者,对宏大叙事的爱好几近偏执。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希望把雅加达打造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于是斥资建成十车道的坦林大道(如今依然堵得水泄不通)。他还建起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民族主义建筑,比如被戏称为“苏加诺最后的雄起”的民族独立纪念碑,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伊斯蒂赫拉尔大清真寺。
14.
无论是理性还是铺张,这些建筑都成为今天雅加达的地标。
我参观了民族独立纪念碑,一百三十七米高,矗立在自由广场上。它从1961年开始建造,到1975年正式向公众开放,由政变者苏哈托剪彩。纪念碑用的是意大利大理石,顶部则镀着三十五公斤的金叶。远远看上去,纪念碑像是一根勃起的男性器物。走近才发现,原来可以通过一个前列腺似的地道,进入纪念碑内部——它的地下室已经被改造成国家历史博物馆。
15.
我喜欢历史博物馆,在世界各地旅行时顺便看过不少,但这样连一件(哪怕一件!)“历史实物”也没有的历史博物馆还是第一回见。在这个超现实主义的笨重结构里,陈列着四十八个微缩景观模型,像过家家似的,描述印度尼西亚争取独立和建国的历史。也许是为了彰显建国之路的漫长多艰,每组模型间都刻意隔着很远的距离,而模型本身又很小,实际看上一圈相当费腿且劳神。
我一路看过去,在1955年万隆会议的模型前长久驻足。因为在我所受的历史教育里,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展示出非凡的魅力,无疑是万隆会议的“灵魂人物”和“真正主角”。
16.
可当我带着一点飘然的心情定睛细看时,发现台上慷慨陈词的男主角不是周总理,而是苏加诺。他戴着黑色清真小帽,手臂高举,主席台上聆听的各国元首纷纷露出钦佩的神情。我看了几遍,主席台上没有周总理的身影,倒是前排观众席上有位穿中山装的人颇为神似,只是因为角度不好,加之灯光昏暗,始终不能确定。
我终于醒悟:历史就像一摊泥巴,把泥巴捏成何种形状大有学问。毫无疑问,在印尼人民心里,万隆会议的真正主角是苏加诺——他们亲切地称为“Bung Karno”的“加诺兄”。
可真实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呢?我望着眼前的模型,感到一阵迷茫,仿佛置身的不是历史博物馆,而是历史“薄雾馆”。
17.
我又寻找关于1965年军事政变、反共屠杀,以及苏哈托在之后三十年军事独裁统治的模型。不用说,它们都被刻意回避,仿佛一缕青烟,消散在历史叙事中,而“缺失”成为一种“言说”,一种更有力量的“言说”。
好在这地方印尼人自有妙用。虽然像样的藏品一件都没有,却因为是地下室而兼具昏暗、阴凉两大优点,加之门票便宜(合人民币一块八),着实吸引了不少青年男女。他们找个角落,席地而坐,品味着各自人生的浪漫。什么国家啊、历史啊这类煞有介事的话题,在他们的爱情火苗前全部轰然崩塌。我还看到一家老小铺上席子用餐,享受天伦之乐——也许这才是这家博物馆的正确用途。果不其然,走了一圈,我发现特意付钱跑这里看微缩模型的好事之徒好像仅我一个。
18.
从历史博物馆出来,我决定登上纪念碑的顶部——据说那里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烟雾污染的“盛景”。排队等电梯的队伍颇为浩荡,足有几百人,蛇形延伸到外面又拐了几道弯。我本打算耐心等待,可阳光太毒,队伍又一动不动,只好走到里面一探究竟。
难怪,偌大的纪念碑只有一部载重七人的电梯,上上下下几百号人全都靠它。我渐渐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可看看周围的印尼人,全都安之若素地看着这台老式电梯,看它“咣当”开门,“咣当”关门,悠然地运行……
19.
一直趴在桌子上小憩的工作人员,突然抬起头,朝我招了招手。他见我迟疑片刻,就更加夸张地挥动手臂,脸上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他留着两撇神气上翘的小胡子,只是被烟草熏得枯黄,活像两捆干稻草。
他指了指排队的长龙,伸出两根手指:“Two hours.(两小时。)”
他又伸出六根手指,指了指天:“Six dollars,express.(六美元,快速通道。)”
他的发音如此标准,让我怀疑这门生意已经营颇久。那些像我一样误入歧途的外国佬,想必总会抱着“来都来了”的认倒霉心态掏钱登顶吧。况且,相对于排队两小时,六美元的“后门价格”也算得上公道……
20.
只是突然间,对于爬到纪念碑顶上这件事,我感到一阵兴味索然——漫长的队伍、缓慢的电梯、对外国人的特殊“照顾”、被刻意回避的历史……这一切,已经让我感到不虚此行。
“很长的队,两个小时。”他微笑着望着我。
“苏西洛[插图]总统会派直升机送我上去。”我开了个玩笑,走了。看样子他没怎么相信。
最终,一种怀旧的本能将我引向这个已逝殖民地的核心,位于城区北部港口的哥打——曾经的巴达维亚古城。在残破的街景中,我发现昔日帝国的幽灵仍然在这里徘徊。
21.
在著名的巴达维亚咖啡馆,一群追忆往事的荷兰人,正端着曼特宁咖啡,坐在二楼高高的天花板下,吊扇有节奏地搅动着午后略显沉闷的空气。窗外是鹅卵石铺就的法塔西拉广场,耸立着建于1912年的老巴达维亚博物馆。如今,落满灰尘的陈列柜上,摆满各种各样的哇扬木偶,注视着人来人往和时光变迁。
巴达维亚的兴建者扬·彼得松·库恩的纪念碑就在楼下的庭院里。1619年5月,正是他率领荷兰军队夷平雅加达人的城镇,建起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让巴达维亚成为荷兰统治爪哇乃至整个东印度群岛的基地。
22.
在这里,荷兰人建造高高的房子,在瘴雾弥漫的运河上建起荷兰式吊桥。自始至终,他们心目中的蓝图是把雅加达建成一个热带的阿姆斯特丹。因为从未想过离去,总督范·伊姆霍夫将自己的宅邸修建得格外宏伟。红色的砖墙,宽大的窗棂,只有最尊贵的殖民地官员和他们的家眷,才有资格透过那些窗户眺望满是帆船的港口和椰子树。
市政厅早就被改建为雅加达市立博物馆,陈列着一些荷兰殖民时期的家具。门口的青铜大炮,是荷兰人攻克马六甲的战利品,尽管风吹日晒,仿佛仍可随时点火。我看到一对雅加达情侣正倚在大炮上拍摄婚纱照,女孩穿着白色长裙,男孩穿着爪哇贵族的制服,面露羞涩。
23.
他们并不感到孤立。因为法塔西拉广场如今已经成为年轻人、艺术家、流浪汉和小贩的乐园。头戴纱巾的女孩们在这里骑车,穿着夹克和套头衫的男孩们三五成群地聊天、弹吉他,刺青艺术家展示着他所发明的图腾,流浪艺人牵着猴子当众表演,发福的女人们则向游客推销着gado-gado和bakso——前者是花生酱拌什锦蔬菜,后者是在印尼度过童年的奥巴马最怀念的牛肉丸。
这一切的背景,是那些内部已经荒废或濒临荒废的殖民地建筑。洞开的大门里躺着几个酣睡的当地人,对旅行者的窥探早已司空见惯——他们接管了荷兰人的房子,接管了巴达维亚,顺便也接管了过去,让那些帝国的幽灵们无家可归,只好永远凄凉地徘徊。
24.
出于一种考古的冲动,我沿着腥臭的运河,向更北面的咖留巴港走去。当地人曾经雄心勃勃地计划重建整个咖留巴地区,在摇摇欲坠的建筑上兴建新的博物馆,然而这些计划最终搁浅。我看到的是一个被遗弃的世界:露天垃圾场、裁缝铺、修鞋匠、卖鞋垫的,私人宾馆破败不堪,停车场里停着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汽车,一群70年代长相的当地人(可能是印尼华人)正在汽车的阴凉下打牌。太阳毒辣无情,仿佛要点燃一切。
东印度公司的货仓被华人老板收购后改建成一家咖啡馆兼文化机构,这是附近唯一像样的地方,有着绿草茂盛的庭院和廊柱支撑的走廊。然而店员李世强对我说,这里每年雨季都会进水,水没过膝盖——因为河道堵塞的原因。
“你会发现,雅加达的富人盖房,都会把地基提高一尺。”他比画着说。
25.
李世强是雅加达出生的华人,祖籍广东梅县,说一口带爪哇腔的汉语。他的父母在民国时期来到这里,一家人再没有回过中国。他向我打听国内的情况,也传播他所知道的内幕消息。
我向他了解当地华人的状况。他说,不容乐观,隔阂一直存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经济曾一落千丈,统治国家三十多年的苏哈托被迫下台。雅加达爆发大规模的骚乱和排华事件[插图]。
“华人像是220V的电流,而整个印尼只能接受110V电流,作为电压转换器的政府一旦出现问题,华人就会遭殃。”李世强说,“这就是为什么每次社会动荡,华人总是首当其冲。”
26.杀青段
在通往港口的路上,我不时想着和李世强的对话,感到雅加达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只是在循环往复中运行。就如同眼前的港口,虽然历经几个世纪,却依然维持着当年的样子。褐色的水面上,漂着树叶和浮沫,两侧泊满古老的望加锡帆船,黝黑的搬运工依然用手推车装卸货物,太阳则依旧照耀这片破败、颓废却又异常美丽的土地。
一个蹲在码头上的老人向我招手。他说,只要三美元,就划船带我去入海口兜一圈。他的脸上布满皱纹,目光中带着早期白内障的白雾。我给了他钱,跳上一只小舢板,看着他把瘦小的身躯随意搁在船头,不再说话。
除了那只摇橹的小臂,老人的身体几乎保持不动,脸也像枯叶一样丢失了表情。在烈日下,他带我驶出港口,向着更宽阔的海面驶去。
未完待续 中…
